《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
後記
羅布·蘇沃爾
由於泰德·格蘭特的《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結束在1950年,讀者顯然想知道從那時起發生了什麼。鑒於其範圍,就這樣一個主題寫一篇後記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然而,一項嚴肅的任務,即使不是幾本書,也至少需要再寫一本書。這是我們所不能承受的,但我們將來會再談這個問題。不過,我將試圖至少簡要地概述一下後來的發展情況。儘管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空白和遺漏,但我希望這將有助於確定我們當前工作的背景,並使其具有一定的連續性。
1950年,在被希利開除出「俱樂部」後,格蘭特試圖重整旗鼓,盡可能地收拾英革共的殘局。必須說——後來泰德也承認——事後看來,他沒有支持公開工作是個巨大錯誤。他仍然希望挽救黨的領導團隊,尤其是哈斯頓。這是一場沒有回報的賭博。如果成功了,至少英革共的基本核心會基本保持不變。在1956年英國共產黨遭遇危機的時候,他們會更有效地進行干預。然而,隨著希利-坎農-巴布洛-曼德爾密謀著對英革共的破壞,這個機會也就失去了。
到了1950年秋天,格蘭特的支持者只有約30人左右,主要在倫敦和利物浦。鑒於客觀環境的困難和組織的薄弱,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在工黨內部開展工作,為未來形勢必然變化做準備。以這樣的微小力量,在五十年代的條件下——就像穿越一片荒蕪的沙漠——考慮在工黨之外建立一個獨立的政黨,那是瘋狂的。換句話說,工黨內部的工作並不是基於事先制定的戰略或戰術,而只是迫不得已。
就在被開除後,泰德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致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的公開信》,試圖澄清他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政治立場。在沒有任何全職人員或組織的情況下,同志們努力維持著一切。他們的會議記錄記錄了他們尋找聯繫人的嘗試。雖然組織對倫敦和利物浦以外的其他地區的接觸並不頻繁,但格蘭特設法四處旅行,以接洽一些聯繫人。其他的決定是建立一個30英鎊的「發展基金」,並作為建立一個組織機構的第一步,以12鎊又10先令的價格購買一台複寫機。這無疑是趨勢組織的「狗日子」。
1951年5月,第一次全國會議在倫敦舉行。據報導,倫敦有20名成員,利物浦有11名成員,全國各地也有零星的聯絡人。泰德發表了一份題為《戰後時期的史達林主義》的文件,文中全面地充實了新時期的特點和史達林主義的前景。
「對馬克思主義來說,無論是悲觀主義還是虛假的樂觀主義,都不能在事件的分析中起到決定性作用。首先必須理解匯聚成當今世界情勢的各個歷史力量的意義。」
「在史達林主義所控制的地區,推翻史達林主義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誠然,史達林主義仍然是一個長期危機的政權。在它裡面,在國家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與波拿巴主義的國家機器和它為之服務的特權階層的利益永遠處於矛盾之中。因此,俄國的史達林主義政權本身與帝國衰敗時期的古羅馬的凱撒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甚至比資本主義的波拿巴主義還要相似。在這一點上,它與法西斯主義有著高度相似之處。從長遠來看,波拿巴專制主義的政權與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經濟基礎是不相容的。這就是克林姆林宮中貪得無厭的蛀蟲長期抽搐、無休止地撤換官員的根源。史達林主義的勝利只能是為它的滅亡做準備。但這只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如此。無疑,史達林主義暫時得到了加強」[1]。
這一分析為我們組織提供了一個更加一致的視角,並被用作組織招聘新同志的基礎。會議一致通過了該文件,並在次月作為一份公開的小冊子複印本印發。會議還決定每兩個月發行一本理論雜誌。吉米·迪恩和他的兄弟亞瑟·迪恩、布萊恩·迪恩、里亞赫、李維等人,幫助籌集資金,創辦新刊物。1952年2月,由泰德擔任編輯的新雜誌《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出了第一期。然而,由於資源缺乏,經濟拮据,雜誌只在1952年2月至1954年4月間斷斷續續地出版。
希利的機會主義
對格蘭特的趨勢組織來說,關鍵問題是如何在工黨內工作。希利派——正如泰德所預言的那樣——「在錯誤的時間加入工黨,也將不可避免地在錯誤的時間離開工黨。」在工黨內部,希利集團根本不知道如何工作,只是在推行一種機會主義政策。他們在追逐一個並不存在的幻影左翼,同時掩飾自己的「托洛茨基主義」,給自己穿上左派改良主義的衣服。
更糟糕的是,他們與一層左派改良派結盟,有「建立起左派」的錯誤想法。希利在1948年成立了社會主義協會,然後與貝西·布洛克(Bessie Braddock)和她的丈夫傑克·布洛克(Jack Braddock)市議員等「左派」名流一起推出了一份名為《社會主義展望報》(Socialist Outlook)的報紙。這些極度右傾的人物用官僚機器統治了利物浦工黨。
希利集團實行的是深度打入主義政策。他們混進了工黨,但完全放棄了自己的理念。《社會主義展望報》按照巴布洛的路線,具有明顯的左派改良主義和親史達林主義的特點。它與工黨左派的報紙《論壇報》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例如,它在1952年9月19日的一期上,就有這樣的標語標題:爭取貝文在1952年工黨大會上勝選!(奈·貝文是改良左派的領袖之一)。他們報紙的1953年11月27日的頭條則是「保守黨必須下台——讓我們發動連署把他們趕出去!」諸如此類的改良主義話語。
即便如此,這種溫吞的左派改良主義對於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來說還是太過火了,他們在1954年禁止了《社會主義展望報》。由於害怕被開除,希利的支持者立即關閉了該報。當工黨高層同樣禁止了社會主義協會時,《展望報》發表了一份聲明:「作為工黨的忠實黨員,我們從來沒有任何獨立於工黨之外的利益,也有義務接受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決定。」[2]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吱聲就投降了。
在「協會」和《展望報》關閉後,希利集團在工黨內加深了它的機會主義路線——這實際上是巴布洛的「新式」打入主義政策。他們開始出售《論壇報》,而不是自己的報紙。事實上,在《展望報》關閉後,他們有兩年時間沒有自己的報紙。正如哈里·拉特納(Harry Ratner)後來承認的那樣,「我們想在工黨和工會中創造一個泛左潮流,這與我們深入工黨的打入主義戰略是一致的。」[3]
被開除後,泰德在給《第四英國部成員的公開信》中分析了《展望報》的作用:
「《社會主義展望報》的政治角色不是由蒼白無力的編輯評論決定的,而是取決於那些英國下院議員等人的社論。而他們的政策顯然是在給右翼的苦藥加些甜度。同時,編輯評論的內容色彩則是不要『得罪』編輯部裡的史達林主義同路人。編輯評論提出的『批判』跟那些臭名昭著的『蘇聯之友』的言詞是如出一徹的。」
他接著引用了《展望報》中的例子:
「(他們文章內充斥著)諸如『領導們希望它能』、『我們遠遠不是說俄國政府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支持進步運動。』、『莫斯科試圖通過確保朝鮮的和平來換取安全理事會上的額外席位,這帶有明顯的強權政治的味道。』等等。這些就是他們聲稱的『嚴肅托洛茨基主義式的批判』的例子!在這樣的言論中——這些言論帶有很獨特的味道——有以下這一項:『俄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對方國家眼中符合蘇聯利益的東西決定的,但正如印度所證明的那樣,這種政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始終與國際工人階級的最大利益相一致。甚至,從長遠來看,這也不符合蘇聯自身的最大利益。』!」
希利派純粹的機會主義和親史達林主義,與眼前的不景氣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觀點並駕齊驅。「經濟上的需要迫使美國向蘇聯和殖民地革命進行武裝決戰」他們1950年的大會綜觀決議這樣寫道:「帝國主義正被迫備戰,然後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著手進行一場世界大戰。但是我們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我們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組織起來,即儘管有巨大的不利條件,但我們可以在戰爭中進行不亞於在和平中向前推進黨的建設」[4]。
每況愈下
如前所述,第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已向鐵托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屈服。這種對史達林主義的適應在巴布洛、曼德爾、弗朗克等人的決議的政治立場中表現得非常明顯。1951年,巴布洛領導層提出了即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觀點。在當時的條件下,巴布洛堅持認為,這種新的現實符合「革命導致戰爭的概念」,因此當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和方向應該建立在這種概念之上。「現在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帝國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採取「深入打入主義」的政策,托洛茨基主義者需要隱藏他們的身份。坎農、希利和他們其他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這一立場。「我們認為這些文件完全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坎農在1952年5月29日寫道。而希利則組織了「工作大隊」從英國前往南斯拉夫支援當地的「社會主義」政府。
順帶一提,現在是回應希利派多年來到處兜售的一個神話的時候了。亨特(Bill Hunter)曾是英革共多數派的支持者,在英革共解散後,他便一心一意地投向希利。作為希利的主要擁護者,他在1954年末被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取締《社會主義展望報》後開除出工黨。他與泰德·格蘭特同屬東伊斯靈頓的選區工黨。當地工黨兩次拒絕認可亨特的開除案。在第三次會議上,這個選區工黨的總管理委員會(General Management Committee,GMC)面臨著明確的選擇,要麼認可開除,要麼被強行解散。在這種情況下,格蘭特雖然抗議亨特的開除,但投了棄權票。此後,為了抹黑泰德,希利派就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指責格蘭特背叛左翼、支持右翼。亨特在自傳中重複了這個神話。後來,這個故事又被聯繫到一個謠言上,即1964年,戰鬥派的支持者們支持以政治理念為由將希利派開除出黨——這都是子虛烏有的。
諷刺的是,格蘭特所採取的正確立場,正是幾年前希利在曼徹斯特所贊同的立場。當1951年5-6月對索爾福德市工黨進行紀律處分的問題時,工黨全國執行委曾威脅要關閉這個選區工黨。「我們是否還應該繼續無視於黨中央的意志,以至於被開除呢?」拉特納寫道:「我們一直與希利和『俱樂部』在倫敦的執行委員(亨特是其成員之一)保持聯繫。他們的指示是,鑒於『俱樂部』的長期打入戰略,我們應該避免被開除。我們已經採取了原則性的立場,每個人都會理解為什麼有必要進行戰術性的撤退,以避免地方選區工黨的解散和鬥士們被開除黨籍」[5]。
泰德在1954年面對當地工黨被解散而投棄權票的立場是絕對正確的。雖然抗議亨特被開除黨籍,但在這樣的問題上讓官僚機構輕易地地關閉整個黨部,清空所有的左翼份子,是瘋狂的。當然,為了誹謗泰德·格蘭特,包括拉特納和亨特在內的希利派利用泰德了的棄權票來污衊他的革命人格。
1953年,第四國際內發生了分裂,希利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一起分裂出去,成立了自己的「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雙方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政治分歧。所有的政治理由都是後來為了證明分裂的合理性而製造出來的。坎農只是不想讓巴布洛干涉他在美國的組織。帕布洛因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以博特·柯克蘭(Bert Cochran)為首的反對派而招致坎農的憤怒。所以坎農決定與巴布洛分道揚鑣,並把歐洲的所有事務都交給「他的人馬」希利身上。這非常適合希利,因為他想成為歐洲的「大老」。所有關於「巴布洛主義」的無稽之談只是一個煙幕彈。事實是,坎農和希利之前都毫無疑義地接受了巴布洛的親史達林主義路線。
希利派的拉特納指出:
「這個(巴布洛的)總體分析得到了1951年8月召開的第四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的贊同。起初,它只是遭到法國支部(國際主義共產黨)內的大多數人反對。當國際指示他們加入法共時,他們拒絕加入。1952年1月,巴布洛利用他作為國際書記的權力,中止了國際主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多數成員的職務。後者因而分裂。幾個月後,以蘭伯特和佈雷特魯為首的大多數人被逐出第四國際。」
「這一行動和國際的總路線得到了普遍的支持,特別是得到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英國希利的團體(俱樂部)的支持。直到一年多以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面對內部派別鬥爭,反對巴布洛支持的反對派,才開始批評『巴布洛主義』為由企圖清算第四國際,向史達林主義投降。在一段時間內,希利集團繼續支持和鼓吹巴布洛的總路線。事實上,當1953年7月巴布洛向國際書記處提交了一份題為《史達林主義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talinism)的草案,作為即將召開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討論的基礎時,希利同意以國際書記處的名義將其分發給各支部,並只對其提出了輕微的批評。」[6]
當這場爭吵爆發時,拉特納承認他們「被嚇了一跳。」所以坎農和希利其實是最初的巴布洛派。希利的主要合作者、《社會主義展望報》的編輯勞倫斯和他的支持者一起,忠實地貫徹了他們的親史達林主義路線。希利後來把他們開除了——不是因為他們傾向史達林主義,而是因為他們支持了巴布洛。勞倫斯在政治上是一致的,他脫離了國際組織,最後加入了英國共產黨。所以,1954年巴布洛和第四國際在英國忽然一無所有。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在隨後兩年內,赫魯雪夫在共青團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揭露了史達林的許多罪行後,各國共產黨內部發展的危機為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可能。這些在蘇聯展開的事件,起到了推動國際社會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性和正確性大大提高的作用。巴布洛急於在英國尋找新的盟友,竟然在左派改良派的《論壇報》上刊登廣告,找人幫忙在英國成立一個新的第四國際支部。
那時與第四國際組織保持聯繫的山姆·伯恩斯坦,敦促巴布洛與格蘭特的團體取得聯繫。經過一番討論後,格蘭特派才與倫敦的其他一些巴布洛的支持者進行了合併,並承認新的團體為官方的英國支部。實際上,格蘭特的原班人馬形成了這個新支部的絕大多數,其他的人基本上不活躍的成員,很快就離開了。儘管如此,它還是起到了重新激活一層老同志的作用,如喬克·米利根(Jock Milligan)、馬里恩·倫特(Marion Lunt)和安·基恩。
然而,第四國際的認可是以承諾提供資源來支付兩名全職工作人員和一本新雜誌的費用來實現的。到了年底,格蘭特和巴布洛的支持者約翰·費爾黑德(John Fairhead)一起成為了全職人員,並創辦了一本新雜誌《工人國際評論》(Workers International Review)。巴布洛希望費爾黑德能夠成為他在英國的盟友,以對抗格蘭特在組織內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影響。然而,費爾黑德並沒有堅持多久,就很快就離開了。他的政治演變最初是從支持希利的《社會主義展望報》,進入英國共產黨,然後再加入革命社會主義聯盟,而後是克里夫集團,然後是波薩達斯派(Posadists),最後打入了工黨。從那以後,他加入了保守黨,並成為右翼保守黨星期一俱樂部的執行委員!「我並不感到驚訝」泰德後來說:「他是一個貴族學校的孩子,而且來自保守黨家庭的背景。」
在英國重新建立組織的嘗試,恰逢正在展開的匈牙利政治革命。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事件震動了世界,並引發了共產黨內部的進一步深層危機。六週內發生了兩次總罷工和兩次起義。駐紮在匈牙利的俄軍投向了革命群眾。最後,他們被撤走了,中亞的軍隊被派來鎮壓起義。他們被告知他們要去柏林鎮壓法西斯政變。起義最終被俄國坦克冷血地鎮壓了。
匈牙利的革命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各國共產黨內部的動蕩。史達林主義領導人譴責起義是一場「反革命」運動。但是,共產黨的大批基層黨員不能忍受這種路線。英國《工人日報》駐匈牙利的通訊員彼得·弗萊爾(Peter Fryer)發回了關於匈牙利革命的在地報導,但被領導層壓制了。它們最終被刊登在《曼徹斯特衛報》上。在英國,一大批共產黨人的情緒相當不滿,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開始持開放態度。在一年之內,這場危機導致共產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黨員。
我們的趨勢組織此時就需要快速地面向共產黨黨內的這些機會。對此,組織內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辯論來釐清如何接近這些潛在的新同志。格蘭特提出了打出公開的旗幟和發起公開的組織的問題,認為這是吸引共產黨黨內持不同意見者的唯一有效手段。這遭到了山姆·李維等同志的抵制,但被多數人所接受。組織遂於1957年初成立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而格蘭特透過《工人國際評論》發表了題為《就匈牙利問題致英國共產黨的公開信》,敦促基層共產黨黨員為真正的列寧主義而戰。
「同志們!新的衝擊還在後面」《公開信》中說:「昨天是蘇聯二十大的轉向,今天是匈牙利的事件,想想看明天… (會發生什麼事呢?)」
「俄國軍隊對匈牙利的干預是為了阻止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俄國邊境建立,因為這將是俄國官僚末日的開始。已經有一些俄軍士兵站到了匈牙利人民一邊。這是未來的預兆!俄國軍隊的干預阻止了群眾在匈牙利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但是將來當俄國群眾起義的時候,有誰會保衛俄國官僚呢?在未來的時期,東方人民反對史達林主義,西方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大事將迫在眉睫。我們能夠是最能夠幫助俄國和東歐的工人,為推翻英國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殊死鬥爭的組織。」
「共產黨的同志們!如果你們對工人階級的問題和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清楚的瞭解,就能最好地説明完成這項任務。我們相信,你們會明白,只有在你們的領導人所拋棄的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綱領上,革命鬥爭才能在英國和國際上取得最後的勝利。」
靈活的戰術
在一份同樣由泰德撰寫的題為《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政治任務》(1957年)的文件中,尖銳地提出了對共產黨內異議人士採取靈活戰術的必要性:
「從這項工作中可以為第四國際贏得大批關鍵和重要的幹部。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任何企圖仿效史達林主義的做法來強加路線都是不可取的。例如,許多最優秀的份子不會立即準備好打入主義的觀點。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在英共黨員之間贏得一批核心人士到第四國際的綱領和旗幟下。在以後的階段,必須討論群眾組織內部的工作問題和未來前景的問題。但是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如果這樣的集團立即加入工黨,就意味著許多優秀的人被淹沒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沼澤中,也意味著其他人對工黨真正工作的可能性完全失去幻想。其實論壇運動(英共黨內的反對派)中最優秀的、最頑強的份子,目前是與打入主義最對立的。」
該文件繼續道:
「當下形勢首先要求採取靈活的策略。決不能把打入作為一種癖好,就像開放工作的概念一樣。我們在特定時間的策略是由我們所面臨的機會和未來前景的可能性所決定的。如果採取形式主義的態度,對獨立旗幟下工作的直接可能性置之不理,那將是更大的瘋狂——《工人國際評論》的些許的成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政治上和在戰爭中一樣,戰術的實質是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在戰場上那個戰鬥狀態最有利於勝利的部門。在公開領域的成功工作可以為今後在工黨內部取得更大的成功做好準備,因為決定性的鬥爭將在那裡進行。」[7]
格蘭特和其他同志與英共內的一批異議人士進行了接觸和討論,但對他們極低的政治水準感到震驚。格蘭特回憶道,「過去的史達林主義者首先會問起你們的綱領。但現在這些人首先會問的問題是:你們有多少人?」經過幾十年史達林主義的誤導,要把這樣的人爭取到一個小組織中來並不容易,效果也不是很出眾。作為史達林主義對工人積極份子的惡性影響的例子,只需舉出下面的例子即可。
史達林主義者通過完全官僚化的手段,包括操縱選票,從上控制了電工工會(ETU)。但在1956年,一系列重要的電工工會領導人脫離了英共,開始了反對派爭取工會內部民主的鬥爭。在與格蘭特討論過的人中,有這個團體的領袖弗蘭克·查佩爾(Frank Chappel),他當時還是左派。他最後沒有加入我們,後來又遠遠地向右移動,成為工會的反動獵巫頭目。
基本上,思想、理論和原則並沒有吸引這些前史達林主義者。他們更多的是被希利的組織所吸引,他們的組織規模更大,資源更多,有自己的印刷機。因此,希利招募到了整整一層人,包括布萊恩·貝漢(Brian Behan,愛爾蘭著名劇作家布倫丹·貝漢(Brendan Behan)的弟弟)、彼得·弗萊爾(前《工人日報》駐匈牙利記者)和布萊恩·皮爾斯(Brian Pearce)。利用希利的資源,弗萊爾成為1957年新創辦的《通訊報》的編輯,也就是「俱樂部」的機關報。
然而,他們不但沒有使這些前史達林主義者認同托洛茨基主義,反而似乎把希利轉變成了「第三時期」史達林主義的再版。幾年之內,希利放棄了他在工黨的極端機會主義路線,於1959年初發起了社會主義工人聯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他們從最懦弱的機會主義立即轉向最瘋狂的極左主義。但蜜月並沒有持續多久。希利派內部以威逼和恐怖為基礎的官僚集權制度,很快就導致貝漢、弗萊爾和其他一大批人被開除。
幾年後,希利的傀儡亨特犬儒地反咬他的導師。他揭露了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希利是一個小氣的暴君,是組織內部的獨裁者。亨特在他的自傳中說:「他在1970年代後期把離席抗議作為一種有意的施壓方法,企圖用意志力、恐懼、行政手段和暴力來解決黨內的歧見…。」[8]
任何對他有些許理解的人都知道希利與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完全沒有關係。無論亨特如何隱瞞,他都無法逃避他曾毫不留情地支持了希利政權——直到1985年希利被開除而垮臺為止。「如果沒有他周圍的一大群其他領導層人士的支持,希利永遠不可能像他那樣行事」拉特納評論道:「像邁克和托尼·班達(Mike and Tony Banda)、亨特、克里夫·斯勞特(Cliff Slaughter)和巴布·肖(Bob Shaw)這樣的人都是他的慫恿者,而像我這樣的人未能發聲」[9]。
如前所述,格蘭特認為,希利在錯誤的時機進入工黨,也會在錯誤的時機離開工黨。事實證明,這一預測是絕對正確的。儘管如此,希利派的曲折在我們組織內部產生了一定的質疑,於是格蘭特利用這一經驗在1959年3月寫了一份內部文件來回答這些疑問並澄清情況。該文件簡要介紹了對於工黨戰術的歷史,並分析了與托洛茨基的打入主義概念和我們在群眾組織內進行的長期工作的不同之處。
顯然,托洛茨基所給出的經典打入條件在當時的英國並不存在。黨內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工作是基於未來群眾左翼的觀點,而左翼將在政治和經濟危機時期發展。在社會危機時期,廣大工人群眾轉向他們的傳統組織,為創造群眾性的左翼改良派甚至中派潮流服務,這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像派別集團試圖宣稱的那樣,馬克思主義者「把自己埋在工黨里。」需要的是把黨的工作與獨立工作結合起來,時刻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政策而奮鬥。絕大多數新的支持者來自工黨之外,但被我們清晰的思想和對群眾組織的定位所贏得。
泰德在文件中解釋說:
「不論情況如何瞬息萬變,任何工作都是不可能在沒有清楚前瞻的情況下進行的。不然我們的工作就會如希利派一樣,採取經驗主義,讓任何短期的事件發展都令我們毫無方向地橫衝直撞。這樣的策略,只會讓我們的趨勢組織完全受制於各個突發事件,只能被時而有利、時而不利的客觀情勢擺動。反之,儘管我們在日常工作當然要將一切突發情況考慮進去,但我們必須向成員們解釋每起事件的意義,並且幫助他們學習如何透過對於整個運動的廣闊前瞻來理解所有事故。希利派由於沒有理解打入主義戰略與其用途,所以才發展了他們的行徑。他們的工作只會以流產告終。」
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的反對派
雖然我們是第四國際的官方支部,但在一系列問題上,我們始終在政治上反對國際的領導。儘管匈牙利事件使我們找到了共同點,但其他事態發展卻產生了尖銳的分歧。例如,在中蘇交惡爆發時,第四國際沒有把它看作是兩個官僚機構之間的民族衝突,而是決定對據稱更「進步」的中國官僚機構給予批評性支持。與此同時,轉入反對派的巴布洛則支持俄國官僚,聲稱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化」運動為官僚的「自我改革」打開了大門。這兩種立場都與托洛茨基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一位以阿根廷為基地的領導人胡安·波薩達斯(Juan Posadas),竟然支持中國官僚機構對美國發動核戰爭的號召!最後,他在拉丁美洲建立了自己的「第四國際」,並在1962年的一次特別會議上宣佈:
「我們正在為一個階段做準備,在這個階段中,在原子戰爭之前,我們將為奪權而鬥爭,在原子戰爭期間,我們也將為奪權而鬥爭,而那時我們也會得到權力(原文如此!)。原子戰爭沒有開始,只有結束,因為原子戰爭是整個世界的同時革命。不是連鎖反應,而是同時的革命。同時性並不是指同一天同一小時。偉大的歷史事件不應該用小時或天來衡量,而應該用時期來衡量。工人階級將維持自己的存在,(並且)將立即不得不尋求自己的凝聚力和集中化。」
「毀滅開始後很短的時間內,甚至在幾個小時內,所有國家的群眾都會揭竿起義。資本主義在原子戰爭中不能自衛,只能把自己關在山洞裡,企圖摧毀一切可以摧毀的東西。而群眾則要出來,必須出來阻止,因為這是他們唯一能打敗敵人的生存之道。資本主義的機器、員警、軍隊,將無法抵抗群眾,當時必須立即組織工人的力量。」[10]
所以,在波薩達斯混沌的腦海中,那些在原子戰爭後存活下來的人,對數百萬人的死亡驚恐萬分,會起來奪取政權!這顯示了這些人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退步到了什麼程度。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而與從瘋人院發出的思想相去不遠。在向史達林主義投降後,波薩達斯成了毛派官僚的喉舌,只是形式更加極端。
斯里蘭卡平等社會黨
一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團隊唯一能擁有的威信,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威信。這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形成時期的領導基礎。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用組織方法把自己的思想強加給國際。只是在列寧死後,在官僚主義墮落時期,季諾維也夫才開始利用組織機構把「莫斯科路線」強加於人——這種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第三國際的毀滅。
在1930年代,儘管困難重重,但托洛茨基巨大的個人威信,使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小股力量團結在一起。他為捍衛和維護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的真正思想和傳統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但其他的第四國際領導人完全沒有相同的等次。像季諾維也夫一樣,坎農和曼德爾等人想像著他們可以要求基層承認權威和服從他們。列寧曾經警告布哈林:「如果你(只要求)服從,就會得到一批聽話的蠢材。」他們毀了托洛茨基留給第四國際的所有政治和道德權威,並企圖用組織方法來彌補自己的缺失——就像英國支部的領導一樣。這必然造成第四國際還沒有建立起嚴重的群眾基礎之前就被粉碎的結果。大部分的支部仍然是小規模的,並且隔絕於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之外。但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外是斯里蘭卡(錫蘭)支部。
錫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實際上是該國勞工運動的創始人。他們甚至發明了僧伽羅語中「社會主義」這個詞,在此之前是不存在的。他們創造了「Sama Samaja」這個詞——字面意思是「平等社會」。這個詞並不特別科學,但這是他們能找到的與「社會主義」最接近的對應。
在其他國家,史達林主義者開除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在錫蘭,情況恰恰相反。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LSSP)是錫蘭工人階級的傳統群眾政黨。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勇敢地站在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平等社會黨獲得了群眾的支持,成為僅次於資產階級的統一國民黨(UNP)的第二大黨。1953年,它曾成功地領導了斯里蘭卡島上的總罷工,並確立了托洛茨基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領導地位。然而,與它的成功相比,第四國際領導人的失敗逐漸削弱了他們在平等社會黨領導人眼中的權威。
第四國際領導人的錯誤立場導致他們一錯再錯。這進一步損害了他們自身的信譽。在一段時期內,這在國際最大的支部——平等社會黨 ——產生了重大影響。與擁有群眾組織的平等社會黨領導相比,第四國際的領袖們不具備一丁點政治和道德威信。格蘭特回憶說,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平等社會黨領導人N.M.佩雷拉(N.M. Pereira)會帶著諷刺的表情坐在那裡。「我認為N.M.佩雷拉從來都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泰德曾說:「但是,任何人總是會尊重地傾聽托洛茨基的想法,而曼德爾、巴布洛和其他人在平等社會黨領導人那裡根本沒有權威。後者大概坐在那裡想:『我們是群眾領袖。這些人代表什麼?他們沒有正確的思想。他們沒有群眾支持。所以他們有什麼用呢?』而事實上,這種想法也不無道理。」
由於在國際上沒有權威性的政治領導層的制衡,斯里蘭卡平等社會黨領導層所受到的機會主義壓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影響。1950年代末,在不利的客觀形勢的壓力下,平等社會黨開始在政治上搖擺不定,對從前執政黨統一國民黨中分裂出來的斯里蘭卡自由黨政府採取了調和的態度。最終,在1964年,平等社會黨投票決定入閣資產階級政府。這終於讓第四國際領導人無法接受。多年來他們為了不得罪平等社會黨領導人而沒有糾正後者的機會主義。現在,他們不得不譴責該黨轉向人民陣線主義的行徑。不用說,巴黎國際中心的譴責被平等社會黨輕蔑地忽視了。後來,當損害已經造成的時候,國際書記處就在斯里蘭卡支部內部製造分裂,使該國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受到了深刻的打擊。
「第四國際領導層在斯里蘭卡發揮了可恥的、破壞性的作用,」泰德強調說:「多年來,曼德爾等人對斯里蘭卡平等社會黨領導人的機會主義政策保持沉默(這是非常明顯的),但這次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組織了以埃德蒙·薩莫拉科迪(Edmund Samorakody)為首的左派分裂。他來到倫敦,我們進行了友好的討論,在討論中,我們試圖勸說他留在平等社會黨內,組織一個左翼反對派,但他拒絕了。他很真誠,但有點極左。最後從黨內分裂出來並沒有帶來任何成果。後來我們聯繫了平等社會黨的左翼,我們從其中贏得了一個相當大部分的人,他們後來成立了新平等黨(NSSP)。可惜的是,新平等黨隨後被黨領導巴胡(Bahu)的冒險主義破壞了。但這是另外一回事。」
困難時期
從1950年代初開始,格蘭特的趨勢組織招收了些許新成員,其中包括後來成為重要據點的南威爾士分會。1950年初在利物浦,吉米·迪恩吸引了一個16歲的年輕人派特·沃爾(Pat Wall)加入組織。派特在當時大選期間加入了工黨,並在兩週內成為加爾斯頓工黨選區黨部的書記。「他非常想瞭解更多關於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而(後來進入上議院)的工黨議員比爾·塞夫頓(Bill Sefton)告訴他,要學這些就要到沃爾頓去向迪恩一家人求教。」他的終身伴侶和同志波琳·沃爾(Pauline Wall)回憶道:「從那之後,他手不釋卷,把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都讀完了。」派特在利物浦工會委員會和工黨(當時兩者屬統一機構)中為我們的趨勢發揮了領導作用,發展和培養了如泰利·哈里森(Terry Harrison)等一批年輕同志。泰利加入工黨後,對他在黨內的經歷感到失望,一度想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然而,他在一次工黨區會議上撿到了一份我們的青年報紙《集結報》(Rally),並決定與之聯繫。派特曾在利物浦和後來在賓利成為工黨議員,經歷與右翼的鬥爭以及工黨全國執行委的調查,後來成為布拉德福德北部的工黨國會議員。在1990年8月不幸去世之前,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在工黨會議和無數次公開會議上的激情演說,以及他真正的平易近人的個性,將為許多人所銘記。他是一個真正的偉人。
在共產黨內的可能性枯竭後,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實驗結束了。該組織發行了一份名為《社會主義鬥爭報》(Socialist Fight)的新刊物,由泰德·格蘭特編輯,從1958年1月到1963年6月不定期出版。編輯部的其他人包括沃爾(利物浦)、大衛·馬修斯(Dave Matthews,斯旺西)和穆裡爾·布朗寧(Muriel Browning,拉內利)。此時,財政狀況特別糟糕。由於資源匱乏,《社會主義鬥爭報》在1960年期間以舊式模板來製作、發行,直到1961年2月中旬才重新複印。
1955年,我們趨勢組織最強的基地是在利物浦的沃爾頓區,格蘭特也一度被提名位當地選區工黨的國會議員候選人,但被得到右翼全國執行委員會全力支持的當地工黨官僚阻撓。「無論如何我終究會被開除黨籍的」,泰德評論道。另一位經歷過工人國際聯盟和英革共時期經驗豐富的同志喬治·麥卡尼(George McCartney),則被推舉在黨內同當時的「論壇派」(也就是後來的極右翼份子)伍德羅·懷特(Woodrow Wyatt)角逐黨的提名。經過工黨全國執行委的一番調查後,喬治終於成功地得到了全黨提名,但在1959年的大選中未能贏得國會席位,那年工黨在全國的選情也受挫。不久之後,前英共黨員艾立克·赫弗(Eric Heffer)成為候選人,並在1964年贏得了該席位。然而,在1991年沃爾頓補選慘敗之前,沃爾頓一直是我們趨勢組織的堡壘。儘管喬治現在年事已高,但他至今仍是《社會主義呼喚報》的支持者。
工黨官僚機構在1955年關閉了工青聯盟(Labour League of Youth),工黨一時之間沒有任何全國性的青年組織。我們正確地預測到工黨在1959年大選的失敗後,青年運動將很快重新被建立起來,因為工黨如果要成功地進行另一次大選,就需要青年。這發生在次年2月,社會主義青年團(Young Socialists,YS,以下簡稱社青團)成立了。這迎合了當時年輕人群眾之間發展的情緒發酵,尤其是1960年的全國學徒罷工和圍繞核子裁軍運動(CND)的群眾反核戰爭運動的發展。
極左主義
1959年,希利派朝著極左主義方向瘋狂突進,成立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一如既往,希利在沒有與「俱樂部」成員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宣佈成立這個新組織。他們申請加入工黨,並迅速地、可預見地(鑒於1946年的會議決定)被工黨官僚機構取締。希利熱衷於促使工黨開除他們的黨籍。他建議拉特納「讓工黨中央開除你,並爭取讓地方黨部拒絕接受開除案,即便這可能會讓他們也被開除」拉特納清楚地意識到:「希利和執行委員會採取了不必要地挑釁工黨,促使開除黨籍的政策」[11]。
儘管希利做出了這些明顯的挑釁,但前希利派人士肖恩·馬特加姆納(Sean Matgamna)在由「工人自由」(Workers’ Liberty)組織製作的一本名為《左翼的苗床》(Seedbed of the Left)的小冊子中,譴責我們的組織如何「向右翼屈服」,並抨擊我們。馬特加姆納說:「格蘭特趨勢對希利趨勢懷有如此毒辣的敵意,以至於它拒絕具體反對工黨中央於1959年2月對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取締」[12]。他接著又重複了泰德在1954年對希利派的開除案投下棄權票的舊帳,這點我們已經在上文解釋過了。
然而,對於我們對取締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態度」,馬特加姆納顯然是在用希利的老辦法來製造對對手的誹謗。畢竟,為什麼要讓事實毀了一篇精彩的故事呢?他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在1959年4月的《社會主義鬥爭報》的頭版上有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文章。我們引用這篇文章的內容,以正視聽:
「工黨全國執行委已經取締社會主義勞工聯盟以及其雜誌《通訊報》,這是對工人運動中民主的打擊。黨內應該為所有支持社會主義政策的人留有餘地。在充分而公平的辯論下,應該由黨員來決定應該採取什麼政策。獵巫和取締異議者,只能損害黨,而不能協助黨的建設。黨內所有相信民主的人都會抗議這個決定。《社會主義鬥爭報》雖然不同意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許多政策,但仍將抗議取締他們的行動。」(我的強調)。
一開始,正如我們所預測的那樣,社青團吸引了大量的年輕人。然而,狂飆極左路線,且剛剛註銷工黨黨籍的希利突然意識到了社青團,再次180度大轉彎,把所有資源都投向了打入社青團。憑藉著希利強大的組織機構,以及他們的青年報紙《向左看齊》(Keep Left),希利派通過各種可疑的手段,在全國範圍內控制了社青團。
當時社青團內最大的團體是克里夫派的團體,又稱「國資派」(state caps)。該團體當時出版由格斯·麥克唐納(Gus Macdonald,現為麥克唐納勳爵,布萊爾政府的內閣部長)編輯的《青年衛士報》。其次是泰德·格蘭特的團體,由幾十名同志組成。社青團會議變得相當激烈,關於「希利派」、「巴布洛派修正主義者」之類的指責漫天飛舞,令參加會議的全國執行委代表們大惑不解。有一年,左派議員伊恩·米卡多(Ian Mikardo)一頭霧水地問他的同仁:「為什麼對大家都在罵巴布洛·畢卡索(著名西班牙畫家)和丹尼士·希利(前工黨大臣,與希利派無關)?」
在利物浦,我們的同志通過沃爾頓社青團分部製作了《集結報》。這份由貝里爾·迪恩(Beryl Deane)編輯的雜誌,不僅面向利物浦的青年,而且在倫敦、泰恩賽德和斯旺西的青年團支部也有發行。同志們對學徒罷工進行了干預,贏得了一些青年工人的支持,特別是在利物浦。
學生中的突破
另一個為我們的發展開闢機會的重要地區是布萊頓。這裏從來都不是特別激進的地方。1960年,我的兄長艾倫·伍茲在我們的家鄉斯旺西加入了社青團。我們的祖父和母親都是英共黨員。我們的祖父——一個鐵皮工人、活躍的工會會員和老黨員——從小就把馬克思主義介紹給我哥哥。艾倫的史達林主義政治背景造成了他與社青團的其他成員發生尖銳爭論,而當時的社青團正是由我們趨勢組織的成員大衛·馬修斯(Dave Matthews)、科林·廷德利(Colin Tindley)、比爾·史密斯(Bill Smith)以及菲爾和艾倫·勞埃德(Phil and Alan Lloyd)所主導的。
艾倫起初不斷在社青團內的政治辯論上敗陣,而講不過托派的艾倫總是會想我們的祖父求助,尋找新的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反駁。在我們的祖父最後完全耗盡了論據後,艾倫最終被格蘭特派說服了。1963年,艾倫去蘇塞克斯大學求學,當時這所大學是一所新的實驗性大學,只有300名學生。其中有一位是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後來成為南非總統。姆貝基當時領導著一個反種族隔離組織,裡面大部分人後來透過艾倫的努力被贏到了托洛茨基主義陣營。
當時,艾倫是整個英格蘭南部唯一的同志。經過在大學和後來在布萊頓內的堅持工作,他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支持者團體,其中包括杜德利·愛德華茲(Dudley Edwards)和瑞依·阿普斯(Ray Apps)等工人。阿普斯是當地的一名公車司機,也是工黨會議的定期代表。杜德利是一名工程工人,在運動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在獨立工黨的革命政策委員會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後來加入了英共,但因對其失望而離開。他也曾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直到希特勒奪政。他常常在會議上談及這段經歷。杜德利經過與艾倫的多次討論後(他後來承認他那時是在試探我們),他最終加入了我們組織。
蘇塞克斯同志的工作是我們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的一個真正突破。其後多年,我們的大部分資金和領導人員都來自蘇塞克斯地區。如果沒有艾倫在蘇塞克斯的工作,我們永遠無法在全國範圍內發展這個趨勢組織。如今,彼得·塔夫(Peter Taaffe)和所謂的「社會黨」(Socialist Party)(戰鬥趨勢多數派的殘部)的領導人試圖貶低艾倫的作用,但我們組織當時的全國編輯委員會於1965年5月報告中的記錄不言自明:「布萊頓在過去一個時期在財政上和政治上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蘇塞克斯大學爭取來的學生通知為我們的趨勢組織打開了全國許多其他地區的大門。同志們甚至贏得了布萊頓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全部積極成員,包括印刷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主席吉姆·布魯克肖(Jim Brookshaw),他至今仍然是我們堅定的成員。通過這項工作,我們在布萊頓肯普敦工黨中確立了重要地位,建築工人同志羅德·菲奇(Rod Fitch)最終成為1983年的國會候選人。
因此,在蘇塞克斯的工作成果是戰鬥趨勢命運的決定性轉捩點。
分分合合
1960年代初,有人提出要把當時存在的兩個第四國際——設在巴黎的「國際書記處」(巴布洛、曼德爾、弗朗克和邁坦)和設在美國的「國際委員會」(韓生、希利和蘭伯特)——重新統一起來。由於最初的分裂缺乏任何原則基礎,只是威望和小集團政治的結果,因此重新統一的問題應該不會造成很大的政治困難。
然而,正如泰德常說的那樣,偽托洛茨基宗派通常「只懂分裂,不懂合併」。如果你不以原則性的方式對待政治,那麼每一次合併組織的嘗試都只會將兩個團體合併成十個。這次也不例外。「合併」被提議後飛快地製造了不只兩個,而是四個或更多的「第四國際」。波薩達斯和南美局(South American Bureau)拒絕接受統一。英國的希利和法國的蘭伯特也是如此。與此同時,在國際書記處內部,巴布洛與曼德爾等人發生了爭吵,曼德爾等人很快就報復性地將前者開除了!
國際領導者們仍然不顧一切地堅持合併,向所有同志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團結起來——無論政治分歧如何。這是必然導致災難後果的。「國際書記委」不明智地指導我們所隸屬的英國支部,企圖與諾丁漢的前英共黨員派特·喬丹(Pat Jordan)和肯·科茨(Ken Coates)重新聯合。後兩者願意成為巴黎「國際書記處」的傀儡,曾創辦過《週刊》雜誌。當時充滿著冒險主義氣息,在晚年成為工黨在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的科茨,過去曾一度是希利集團的成員,但後來被他們開除。
這些人曾在1950年代末加入過格蘭特的集團,喬丹還當過一段時間的組織書記。然而,他們與巴布洛周旋,建立了一個派別。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他們就離開了,成立了自己的國際集團。這個微不足道的團體在組成和觀點上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換句話說,正是曼德爾偏好相處的那種人。這個集團的政治是百分之百的純機會主義。《週刊》的內容完全是改良主義的,邀請了各種左派議員之類的人撰稿。他們被很多人譏笑為「弱者」(英語「Week」(週)和「Weak」(弱)是諧音)。這也許有點不厚道,但完全準確,而這些人也是第四國際組織寄予全部希望的人。
「第四國際」在英國有一個大問題。一年前,他們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談和,但沒有與希利重歸於好,對希利來說,將合併後的國際中心設在巴黎是死亡之吻,因為他將不再像美國黨迄今所允許他的那樣在歐洲稱王稱霸。他立即開始了一場歇斯底里的運動,反對「巴布洛主義」(方便地忘記了他過去與巴布洛的密切關係),反對韓生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背叛」(方便忘記了他與他們不久前的密切關係)。
巴黎方面要求英國官方支部與喬丹和科茨的「國際社」聯合起來打擊希利。這遭到我們趨勢組織大部分成員的強烈抵制,但最終還是被推進了。在國際社的壓力下,1964年9月,在肯特郡七橡樹的一次會議上,發生了一次不堅定的合併。吉米·迪恩——當時的分會書記——錯誤地預示著這是「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向前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他還說:「會議在通過關於合併的聲明時,也展現了它對同志們的不同經驗和對存在次要戰術分歧的成熟態度。」[13]
然而,這句話也是一廂情願的。第四國際組織的領導層一如既往地表現出不誠信,立即開始對英國支部領導層進行惡鬥。這些「次要分歧」很快就發展成尖銳的分歧,幾個月內合併嘗試就分崩離析,喬丹和科茨抵制領導機構,最後走出去建立自己獨立的國際社(後來的國際馬克思主義社,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
這對國際書記處的成員,並對泰德和其他那些拒絕承認他是國際組織的「偉大領袖和導師」的同志懷恨在心的弗朗克是一大打擊。喬丹和科茨立即的出走也使弗朗克失去了與英國領導層周旋的可能工具。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一變故的不滿,責備那些分裂者:「你們太懦弱了,不敢戰鬥。」
我們的趨勢組織已經吸取了關於不可能走捷徑的慘痛教訓。與曼德爾派的合併被證明是一場鬧劇。與克里夫集團合作制定《青年衛士報》期刊的錯誤嘗試也以失敗告終。這兩條路線主要的推動者是吉米·迪恩,他對合併的可能性抱有幻想。這些嘗試失敗後,吉米心灰意冷,不再積極參與運動,儘管他始終忠於思想。如今,他在一次嚴重的中風之後,已經病入膏肓,喪失了行動能力。但這位有著濃重的利物浦口音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個能力極強的人,所有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都深深地緬懷。他不僅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也是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罪行的受害者。
《戰鬥報》的啟航
上述的這些挫敗可能是我們組織命運的最低點。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孤立的團體,沒有報刊,沒有錢,沒有全職人員,沒有中心。在社青團中,我們是最小的團體之一。艾倫·伍茲回憶道:
「我們不僅面臨著來自工黨官僚機構的持續攻擊,而且還面臨著來自宗派和第四國際的攻擊,他們決心要粉碎我們。但我們有比所有這些東西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我們絲毫沒有垂頭喪氣。我們對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充滿信心。泰德在這個時候起到了絕對關鍵的作用。他從來沒有失去他的樂觀主義、他的不可動搖的信心和他著名的幽默感。」
「困難的條件反而有助於培養我們。當時參加活動的年輕同志都習慣於為理念而鬥爭。因此,我們什麼都不怕。它使我們變得堅韌而堅定,也使我們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得到了磨練。」
1964年夏天,我們決定創辦一份新的出版物,經過反覆討論,選定了《戰鬥派》(The Militant)這個名字。由於吉米·迪恩因工作原因遠足海外,於是我們又決定在倫敦中心找一個接替他的人。來自伯肯黑德的年輕新成員彼得·塔夫被選中,來到倫敦全職製作報紙並協助全國性的工作。在《戰鬥派》創刊後的幾個月內,我們組織就從位於國王十字路的獨立工黨黨部租了三間小房間。這標誌著泰德·格蘭特的戰鬥趨勢發展的新篇章。
希利派對社青團的控制不知所措,他們決定脫離工黨,建立自己的獨立青年組織。他們決定用流氓手段挑起工黨的開除。儘管他們的行為令人無法容忍,包括使用肢體暴力來破壞會議,但他們的計劃沒有想像中容易實現。大多數工黨黨員對年輕人都很寬容,並不熱衷於開除他們。
最終,在1965年他們終於有幾個成員被工黨開除後,他們的極左策略使社青團與官僚機構發生了衝突,他們將大部分青年分裂出工黨。結果,官方的社青團被關閉,後來留下來的青年被改組為「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工社青)。希利派的流氓挑釁,使工黨官僚機構有藉口鎮壓青年組織。官僚機構施加了嚴格的限制,如全國委員會由成人黨任命,社青團聯合會被禁止,任何青年會議討論僅能限於青年問題。為了繞過這些官僚主義的限制,同志們用盡了一切辦法,包括有一年提出了一項詼諧的決議,「呼籲工社青全員支持所有25歲以下的越共黨員」!
在希利派脫離工黨時,他們盡可能地散布關於「巴布洛派格蘭特主義者」的謊言,聲稱我們協助工黨右翼開除了他們。事實上,我們雖然完全反對在工運中任何地方的流氓手段和暴力,但我們堅決反對黨中央對左派的政治迫害、禁止和取締。然而,有一次,我們不得不劃清界限。
旺茲沃思社青團當時的主席是一位名叫馬尼(Mani)的錫蘭人同志。他曾是希利派的成員,後來加入了戰鬥派。他遂成為了希利派組織的一場仇恨運動的目標,在這場運動中,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成員從街頭招募了一些未成年的青年(小太保),並派他們去搗毀一個由馬尼主持的會議。他們被告知那個會議內有個「討厭小太保的黑人」。有一次,馬尼成功地勸說小太保們安靜地離開,但第二次他們引起了騷亂,於是黨的代理人打電話報警。這時,馬尼宣告散會,試圖化解這一局面。隨後,工黨官僚機構提出開除一些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成員的動議,馬尼則提出反對動議,僅限於開除那名親自參與暴力行動的成員。
晚些時候,希利派試圖以此事件來大肆渲染。其實,在工人運動內部是容不下暴力的,那些對工運成員採取暴力的人完全應該被趕出去。這種行為是不能被容許的。當史達林主義者第一次把這些外來的方法引入工人運動的時候,托洛茨基早就解釋過這個問題。事實上,希利的趨勢與史達林主義之間,比他們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有更多的共同點。
希利派對托洛茨基主義在英國和國際上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他們在50多年的時間裡,用即將發生經濟不景氣、世界大戰或法西斯專政的瘋狂觀點,系統地對其成員進行錯誤教育。他們的「第三時期」史達林主義方法論像一台絞肉機,用紙上談兵和即時革命的虛假承諾摧毀了他們的新成員。他們很快就教壞了他們所贏得的所有年輕人,並且在極左瘋狂中脫離了工黨,最終淪為碎片。
《戰鬥報》編輯部在一份題為「關於極左主義的一些申論」(A Contribution on Ultra-Leftism)的聲明中指出:
「近來,自詡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極左派,拋棄了列寧關於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的全部教誨,否定了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
「對他們來說,只要向工人階級、工會、工黨、社青團發出最後通牒就可以了。向工人階級下達行軍命令。而當工人和鬥士不理睬他們時,他們就暴跳如雷 ,譴責所有那些為了以列寧的原則為基礎的一貫的革命綱領和政策而進行實際鬥爭的人,說他們是中派、工賊和『巴布洛派』。」
「從英國支部成員們的經驗看來:今天指著別人大喊著「叛徒」、「賣身求榮」、「假左派」等等的人,恰恰是那些曾經採取深入打入主義的『革命派』。今天的『反巴布洛派』,其實是昨天最歇斯底裡的『巴布洛派』人。過去那些以會『破壞我們同《論壇報》的關係』為理由而拒絕批評奈·貝文的人,就是現在譴責《論壇報》是主要敵人。而這些人的火力沒有集中在資本產階級敵人——保守黨,或者右翼工黨領袖上,而是在『假左分子』,和『巴布洛派』上 。」(《內部公報》,1966年8月)。
最後的決裂
格蘭特趨勢一直反對巴布洛的政治立場和1963年合併後被稱為「聯合書記處」(United Secretariat)的領導層。在中國、中蘇交惡、古巴、遊擊戰主義和殖民地革命等問題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這些在附錄中包含的文件《評第四國際》和泰德的文集《不間斷的傳承》一書中都有概述。英國支部和巴黎中心之間的衝突到1965年底達到高點,當時在國際上發號施令的弗朗克、曼德爾和梅坦決定把我們踢出去,而承認科茨-喬丹集團為正式英國支部,儘管他們代表的只是一小撮人。
在1965年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上,當時的英國支部同志決定把我們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由於對於聯合書記處領導層是否願意散發我們的材料沒有信心,於是決定把泰德寫的關於中蘇爭端和殖民地革命的文件複印出來,送到巴黎去散發。然而,當英國代表到達時,他們發現其他代表根本沒有一個人看過這份文件。泰德諷刺地評論道:「列寧說過,第二國際根本就不是一個國際,而只是一個郵局。但這些人連郵局都不是!」
在國際會議上,泰德總共有七分半鐘的時間(不包括翻譯),來陳述反對聯合書記處立場的理由。自英國支部重新加入第四國際以來,不斷對英國支部進行周旋的弗朗克於1966年1月19日寫了一封簡短的信,通知我們被「降級」。我方也簡單地答覆說,聯合書記處的領導層沒有政治威信,只是在採取組織手段,壓制我們的反對意見:
「第四國際的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對這一問題的不理解。因為從根本上說,國際組織是什麼? 它是一個綱領、政策、方法,最後才是一個執行前三者的組織。我們仍然忠實於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 這時,巴布洛本人已被聯合書記處開除(1964年),最後回到希臘,不再積極參與運動。幾年前,年事已高的他在雅典去世。他臨終前請一些希臘同志向泰德致意,並補充說:「你知道,他確實是(1950年代國際領導層)那些會議上唯一誠實的人」。
在這次經歷之後,有必要對第四國際的歷史做個總結。泰德在一份名為《評第四國際》的文件中做到了這一點。30年的經驗肯定足以讓我們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如果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犯了錯誤,那是一回事。但如果同樣的錯誤不斷重複,而且沒有吸取任何教訓,那麼它就不再是一個錯誤,而是一種有機性的傾向。雖然很痛苦,但大家都很清楚,這個所謂的第四國際已經名存實亡,任何重振它的企圖都是無果的。經過一番討論,大家決定,我們應該永遠拋棄這些人,堅定地走向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
克里夫集團的機會主義
到了1967年,隨著對威爾遜工黨政府的日益不滿,克里夫集團(又名國際社會主義者,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後來成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國際馬克思主義社跟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離開了工黨。他們輕描淡寫地丟掉了以前所說的一切,四散奔逃。他們以一種純粹的機會主義方式,追著參與反越戰抗議的學生跑,並為了迎合學生和小資產階層的偏見調整自己的立場。
克里夫集團雖然堅持他們的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但還是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北越給予了支持。不過,早些時候,他們在朝鮮戰爭時就拒絕支持朝鮮。為什麼有如此的不同?原來,1960年代,支持胡志明在學生中變得非常時髦。後來,他們又可恥地支持阿富汗的伊斯蘭基本教義聖戰組織,認為他們是反對所謂蘇聯帝國主義的「自由戰士」。
1960年代初,克里夫已經放棄了任何形式的托洛茨基主義主張,甚至與列寧主義組織保持距離。羅莎·盧森堡成了反對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人士中的風雲人物——當然,他們喜愛的是她的短處。作為粗暴的機會主義者,克里夫派只是簡單地跟風,隨波逐流。
他們在愛爾蘭問題上的立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69年,戰鬥派反對英國政府向愛爾蘭派兵,我們的支持者在工黨年度會議上把這個問題作為緊急決議提出。雖然決議被壓倒性地否決,但我們明確表示反對英國帝國主義,並重申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在社會主義綱領的基礎上進行聯合鬥爭的必要性。這是解決愛爾蘭問題的唯一辦法。相反,克里夫集團支持英國政府向北愛爾蘭出兵,理由是派他們去「保護天主教徒」。
戰鬥趨勢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解釋道,英國政府之所以出兵是為了維護英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工人階級應該在工會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不分宗教派別的武裝自衛勢力。但克里夫派是「實際」的人,他們最終支持了英國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
克里夫派發行的《社會主義工人報》寫道:
「英軍的介入所提供的喘息空間是短暫的,但卻是至關重要的。那些要求在街壘後面的人能夠自衛之前立即撤軍的人,是在招致一場大屠殺,而這場大屠殺將首先和最嚴重地打擊社會主義者。」[14]他們又說:「因為英軍部隊沒有北愛皇家騎兵隊和「B特部隊」(B Specials)那種對天主教徒根深蒂固的仇恨,所以他們不會採取同樣的惡行,在北愛部署英軍,對皇家騎兵隊和B特部隊的無法無天提供了某種安全阻礙。」[15]後來,這些人完全變了臉,最後支持臨時愛爾蘭共和軍的個人恐怖主義運動。
他們對這些立場感到尷尬,現在試圖否認或將其掃到地毯下。而後,克里夫以他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為基礎,在蘇聯和東歐展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中保持中立。對他來說,這只是一個「側面」的轉變,並無實際意義。[16]
國際馬克思主義社也無條件地支持各地的遊擊鬥爭,同時企圖在大學裡建立「紅色基地」(原文如此!)。他們還支持臨時共和軍在愛爾蘭的每一次恐怖行動,甚至把他們在英國的炸彈襲擊說成是「反帝國主義鬥爭」:「我們國馬社和《紅色週刊》(Red Weekly)無條件地支持愛爾蘭共和運動開展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武裝行動的權利」,他們在1973年8月23日發表的新聞聲明中這樣寫道:「我們不認為這種武裝行動原則上必須局限於愛爾蘭海峽的另一邊」。
實際上,國馬社已經完全放棄了馬克思和康諾利的立場,轉而採用巴枯寧和個人恐怖主義的方法。而戰鬥派則堅持一貫的階級立場。我們當然譴責英帝國主義在愛爾蘭的鎮壓統治,但我們也明確反對臨時愛爾蘭共和軍的策略,因為這種策略完全落入帝國主義的圈套,加劇了北愛的宗教鴻溝。與國馬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立場相反,我們一貫主張用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方法來解決愛爾蘭的問題,就像詹姆斯·康諾利一貫的做法一樣。
這個小小的曼德爾派宗派,一直追求深入人心,現在突然宣佈工黨是資產階級政黨,居然號召工人在1970年的大選中投廢票(並沒有人聽到他們的話)。他們甚至建議人們去打散工黨的會議。不用說,他們自己從來沒有嘗試過這樣做,他們寧願把這種口頭上的蠱惑限制在大學的咖啡吧裡,那是他們「革命行動」的專屬領域。
戰鬥趨勢的起飛
到1970年,工黨中唯一有規模的政治趨勢,就是我們。極左派對我們嬉笑怒罵,但最該被嘲笑的是他們。這些庸俗的經驗主義者沒有任何遠見,只能看到自己鼻子的末端(至今還是如此)。
表面上看,他們似乎是有道理的。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工黨政府的右翼政策導致工人們越來越感到憤怒和失望。芭芭拉·卡塞爾(Barbara Castle)試圖實行反工會立法,導致礦工俱樂部威脅要脫離工黨。
經過希利派的肆虐,工社青一度沈淪在邊緣。我記得在1968年,我是斯旺西青年團支部僅存的成員。運動中的動力下滑了。然而,就工社青而言,在幾年內,工黨領導層作出了讓步,恢復了1965年被剝奪的許多民主權利,包括給予青年發表報紙的權利和工社青代表在工黨全國執行委中的席位。
1970年代是英國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分水嶺。威爾遜政府的敗選和希斯的上臺,使工人階級迎來了一個高度激進化的時期。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被發起,以反對政府的反工會立法,最終導致五名碼頭工人被監禁,並威脅要舉行總罷工。工廠佔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最終政府被1974年的礦工罷工所推翻。統治階級正在撤退,國家的一些部門正在為將來轉向反動做準備,當時基森準將(Brigadier Kitson)和其他軍事人物的觀點就證明瞭這一點。
在斯旺西,通過在學校學生中開展工作,我們成功地贏得了一些年輕同志的支持,其中包括安迪·貝文,他將為我們組織發揮關鍵作用。到1970年,民主選舉的結果使我們的趨勢贏得了工社青全國領導層的多數席位,工社青開始了建立我們自己青年組織的全國運動。工社青主席多耶爾(Peter Doyle)當時被選為工黨全國執行委的青年代表,這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第一次被選上這樣的職位。我們開始在工運中建立起支持點。我們留在工黨的正確性被這些成功證實。
群眾組織不是直線發展的,而是辯證性發展的。它們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工人階級和整個社會的進程。1974-1975年的經濟衰退,結束了1950年以來資本主義普遍上升的時期。這是戰後第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在此之前,上升期的週期性衰退是非常表面化的,工人幾乎沒有注意到,而生活水準卻普遍提高了。1970年代與之前的時期,甚至與隨後的1982-2000年時期的特點完全不同。
在國際上,1974-1975年的不景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前殖民地世界,安哥拉、莫三比克和其他地方發生了革命運動。葡萄牙也發生了革命性的發展,推翻了獨裁統治,希臘推翻了軍政權,西班牙結束了佛朗哥政權。義大利經歷了革命前夕的騷動。與五、六十年代的「民主」幻想時期不同,歐洲資產階級正準備與工人階級進行決定性的決戰。「短劍」陰謀(The Gladio Conspiracy )[17]毫無疑問地證明,統治階級正準備在義大利、西班牙、挪威和比利時實施軍事獨裁。此後發現,「民主」的英國的統治階級和軍方的部分人員甚至在1960年代末曾考慮對威爾遜的工黨政府發動政變。
在這一時期,社會的鐘擺遠遠地向左擺動。在葡萄牙,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法西斯和波拿巴主義統治之後,1974年五一勞動節,100萬人在里斯本街頭示威。由於葡萄牙的總人口只有800萬,這顯示了革命的非凡席捲力。《泰晤士報》發表社論說:「葡萄牙的資本主義已經死了。」群眾又一次轉向他們的傳統組織。不幸的是,是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人的行動——特別是史達林主義者在第一時間的行動——再次挽救了資本主義。
這種激進化也反映在英國工黨內部。左派成功地贏得了全國委員會的些微多數。工黨的官方政策也反映了向左的轉變,它通過了一項包含將25家最大的公司國有化的綱領。戰鬥趨勢果斷地參與了這些事件,並開始發展壯大。
從1966年不到100名同志,到1975年發展到500多名同志。我們有了自己的印刷廠,1972年《戰鬥報》改為每週出版,並在工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地位。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們沒有屈服於極左主義的壓力,而是在其他人離開的時候仍然留在工黨內。這是馬克思主義趨勢後來在英國取得成功的秘訣之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無可比擬的突破。
工人國際委員會
艾倫·伍茲從1960年代初開始就在英國組織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成為了我們趨勢組織的第一個區域性全職人員,長住南威爾士,並很快將當地的工作發展成一個模範。從1969年斯旺西只有我們兩個人開始,我們建立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地區,有許多福特汽車廠的工廠代表,副召集人羅瑟(Albert Rosser)在福特罷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由於我們對1970年和1974年礦工罷工的參與,使我們在礦工中擁有良好的基礎。《戰鬥報》在一些主要礦井中銷售。我們領導了斯旺西的麵包師罷工和大規模的租客罷工。在每次全國性的示威中,南威爾士的隊伍都是最大的隊伍之一。但我們並沒有把自己建立在「活動主義」(Activism)的基礎上。我們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南威爾士夏令營成為全國性的暑期學校。我們還出版了《南威爾士馬克思主義研究公報》(South Wales Bulletin of Marxist Studies)。
1974年,我們和其他國家的極少數同志成立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簡稱工國委)。此時,艾倫在我們的國際工作中被賦予了一項重要的責任——那就是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建立我們趨勢組織的支部。1976年1月,艾倫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和組織活躍成員帕姆做出了很大的個人犧牲,帶著兩個小孩(五歲和兩歲)搬到了馬德里,在西班牙地下非法工作的困難條件下建立起了趨勢組織。幾年內,從最初只有6名同志(3名西班牙人和3名英國人)的小團體開始,西班牙組織發展到350人,並成為工國委內第二大支部。
但西班牙社會黨的官僚吸取了英國的經驗。經過社會黨官僚機構的猛烈追捕——我們的報紙被取締,大部分同志被開除出黨。然而,我們堅持了對群眾組織的方針,包括靈活的戰術,並得以建立起托洛茨基主義的重要基礎。今天,這使我們能夠在西班牙中學學生聯合會(Spanish School Students Union)的旗幟下開展群眾鬥爭。自1987年以來,學生聯合會多次領導了300萬學生的全國性罷課。
艾倫在西班牙待了8年,直到1983年因健康問題不得不返回英國。回到英國後,艾倫在國際組織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協助我們在智利、阿根廷、巴基斯坦、墨西哥和其他國家建立支部。他還成為我們的理論雜誌《戰鬥國際評論》(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擔任編輯,並在工黨開始驅逐戰鬥派的時候被開除工黨黨籍。
我們在英國和西班牙正是在這個時候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在群眾組織中的工作能否成功,一方面是由客觀形勢決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是否有耐心的、長期的準備工作決定的,這就為在條件成熟時接觸大量的左傾工人和青年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主義者從不迷信任何組織形式或策略。真正的金科玉律是在任何時候都要找到一種與工人階級連結的方式,從其中最活躍的階層開始。這就必須利用每個階段出現的每一種可能性,同時牢牢記住總的方向和戰略目標。
工黨第一次獵巫失敗
1974-1979年威爾遜-卡拉漢政府的危機,使我們趨勢與廣大的激進化工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連結。警鐘不僅在工黨的官僚之間,也在統治階級之間開始敲響。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首次成為國家政府必須正視的因素。資本的戰略家們對工黨的急劇左轉感到震驚,他們正確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在推動左派、堅定左派的決心、敦促左派更進一步的方面起著關鍵作用。
當然,這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目的,而是副產品。左派改良派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是矛盾的。在與右翼的鬥爭中,我們客觀上是盟友,但我們也是競爭者和對手,不斷地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贏得陣地。我們在迫使他們走得比他們希望的更遠。此外,眾所周知,一個糊塗的人總是討厭思想明確的人。他們充其量只是不穩定和不可靠的盟友。
1976年,著名專欄作家貝洛夫(Nora Beloff)在週日報紙《觀察家報》上的一篇「爆料」開始了針對我們的迫害運動。貝洛夫利用工黨全國召集人安德希爾(Reg Underhill)收集的材料,試圖將工黨推向一場獵巫行動。這具有預謀挑釁的所有特徵。
然而,不幸的是,對於挑釁的組織者來說,黨內的氣氛並不利於對他們進行迫害。我們的組織因其不懈的工作和在所有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在活動家中贏得了很多尊重。我們從來沒有去做那種極端左翼團體常做的謾駡和歇斯底裡,把他們自己與普通工人階級隔絕開來。泰德始終堅持我們應該堅持用「事實、數字和論據」來捍衛我們的思想,像列寧常說的那樣:「耐心地解釋」。
工黨全國執行委中的「左派」多數拒絕採取行動,到了年底,為我們擔任工社青主席的安迪·貝文同志在面試中表現出色以及一次黨內官僚失誤之後,被選為工黨新的全國青年幹事。在經歷了最初的「紅色恐慌」和工黨官僚組合的騷動之後,安迪最終被送進工黨總部的一間辦公室裡。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機會,使我們能夠充分地利用在工社青中的地位,把我們的想法帶到工運的更廣泛的部分。
在1977年全國消防員罷工之後,英國工會聯盟次年站出來反對政府的工資政策。一個月後,在工黨會議上,我們的同志杜菲(Terry Duffy),一個來自利物浦偉佛特里(Wavertree)選區工黨的代表,成功地提出了一個綜合提案,也反對政府的工資政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低薪工人運動,即所謂的「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1979年,經過一番推諉,總理卡拉漢發動大選,卻被柴契爾領導的保守黨擊敗。
柴契爾政府
工黨的失敗和柴契爾的當選導致了群眾組織的大規模激進化。左傾的轉變反映了人們對工黨親資本主義政策的厭惡,並在工黨內以本恩主義(Bennism)的形式崛起。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取代卡拉漢成為黨魁,1981年參與角逐副黨魁的左派領袖托尼·本恩(Tony Benn)以不到百分之一的差距敗給右派候選人丹尼斯·希利。
這次領導層選舉後,一部分右翼分裂出去,成立了英國社民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SDP)。這一舉動進一步加強了黨內的左傾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戰鬥趨勢發展相當迅速,到1980年,登記在冊的積極支持者達1000人。托洛茨基主義在工黨內的興起使統治階級感到震驚,因為統治階級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工黨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寶貴道具。執政階級絕不可能接受不經過鬥爭就失去對工黨的控制。對我們來說,很明顯,統治階級反撲只是遲早的事。親資媒體對我們的趨勢發起了新的迫害,要求我們被開除出工黨。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1966年末在斯旺西參加了一個夏季的社青團學習營。當時泰德正在講俄國革命,我就加入了這個趨勢組織。我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跟一位同志的廚房裡進行討論時被告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是一種終身的承諾。」當時,我相信我們全國大約有七、八十位同志。到1976年初我成為正式成員,艾倫去西班牙時,我們大約有600名同志。當時,我從威爾士被選入了工社青全國委員會,也被選入了這個趨勢組織的領導機構。1982年初,我成功地為我們趨勢在南威爾士建立了一個強大地位後,我去了工國委工作,但很快就被徵召到我們倫敦總部一個新成立的「反獵巫」部門。
在反對工黨獵巫的鬥爭中,我們在倫敦溫布利會議中心成功地組織了一次有2000名代表參加的工運會議。儘管有反對獵巫的抗議和決議,但最終在媒體宣傳的壓力下,工黨全國執行委內的「軟左派」還是屈服了。媒體每天都在報導我們組織的活動。1983年,工黨全國執行委利用充斥著各種文件、小道消息和所謂「證據」的安德希爾報告(Underhill report),開除了《戰鬥報》編輯委員會的所有黨員。開除事件發生在倫敦南部伯蒙德賽區補選之前,而開除事件發生後,工黨在這個傳統鐵票倉敗給了自由黨。
1983年底,我被任命為戰鬥趨勢的全國召集人,直到1991年底。期間,我領導著戰鬥趨勢的組織部,負責工黨內的工作,反開除、媒體關係、策劃我們國會和市議員同志們的工作、協調全職人員、招聘、組織全國性的集會和會議,以及公開運動,尤其是反人頭稅運動。這是一個龐大的工作。我們在全國各地都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抗議黨中央開除黨籍行為,這反過來又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我們的趨勢組織。這種支持也轉化為戰鬥趨勢在工會中的發展,以及「泛左組織委員會」(Broad Left Organising Committee,BLOC)的發展。
全盛時期
1984年英國礦工罷工之初,BLOC已成為工會中最大的左派力量,並成功召開了由各主要工會2500多名代表參加的大會。我們造就了史上第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約翰·麥克雷迪(John MacCreadie)當選為工會聯盟的總理事會成員。在長達一年的礦工罷工期間,鑒於我們在礦區的地位,我們成功地贏得了500多名礦工加入我們的趨勢組織。1988年,我們在倫敦亞歷山德拉宮聚集了7500名支持者。這是戰鬥趨勢的最高點。
在政治方面,我們的兩位同志特里·菲爾德(Terry Fields)和戴夫·內利斯特(Dave Nellist)於1983年當選為國會議員。隨後在1987年,派特·沃爾也進入國會。派特是一位了不起的同志,與工人和青年的關係非常融洽。從1983年起,利物浦市議會的戰鬥派領導以及其與保守黨政府的鬥爭,也使我們在英國政治版圖上牢牢地佔據了一席之地。雖然我們在利物浦的議員後來處分並被禁止連任,但我們從未在選舉上被擊敗。戰鬥趨勢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我們的人數和影響力也迅速增長。所有那些留在工黨之外,對我們在工黨內的工作嗤之以鼻的宗派,都被晾在一邊,張口結舌地看著我們的成果。
1985年10月,接任邁克爾·富特為工黨黨魁的尼爾·金諾克(Nei Kinnock)在工黨會議上發表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演講,攻擊戰鬥派領導的利物浦市議會。這是一場協調一致的巫師行動,是黨中央與我們趨勢決戰的開始。工黨右派鄧尼斯·希利說:「我認為尼爾的講話具有歷史意義」。然而,利物浦河畔工黨議員鮑勃·帕里(Bob Parry)聲稱:「金諾克今天表明,他是自麥克唐納以來工黨最大的叛徒」。
但是,金諾克的嘗試最後都失敗了。雖然他採取的措施使我們組織的活動非常困難(還能指望什麼?) ,但他們並未得逞。到了1980年代末期,他們只成功地開除了戰鬥趨勢大約8000名支持者中的250名同志。
我們創造了俄國左翼反對派時代以來最強大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我們從身無分文到每年超過100萬英鎊的收入,擁有一整座大辦公中心,一間能印出日報的印刷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有大約250名全職人員——這比工黨本身的全職人員還要多。我們在許多工會和工黨中都有根基,包括大約50名市議員和3名國會議員。令工黨領導層非常氣憤的是,儘管一再嘗試,但他們仍未能將馬克思主義者從工黨中分離出來。
人頭稅
1987年柴契爾第三次大選獲勝後,保守黨政府開始在蘇格蘭推行倒退性的人頭稅,一年後又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推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從事群眾工作、領導反對保守黨政府的好機會。最後,我們的群眾抗稅策略在全國百萬人之間產生共鳴。在最激烈的時候,約有1800萬人拒絕繳納這可恨的稅。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由我們建立並領導的全英反人頭稅聯盟(All-Britain Anti-Poll Tax Union)所帶領。25萬人在倫敦示威,另有5萬人走上了格拉斯哥的街頭。毫無疑問,這場令資本戰略家感到恐懼的群眾運動,促成了1990年人頭稅的廢除和柴契爾的下台。
儘管取得了這些巨大的成功,但我們趨勢組織內部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最嚴重的是,幹部的政治水平正在下降,而領導層卻對此毫無作為。他們被動的原因最後就很明顯了。泰德·格蘭特在編輯部會議上不斷強調,要對進入我們隊伍的新同志進行徹底的教育和培訓。遺憾的是,這些呼籲基本上沒有被理會。艾倫·伍茲試圖通過建立理論期刊來扭轉這一情勢,但這些嘗試被彼得·塔夫周圍的領導集團蓄意破壞,他們此時已經在追求自己的目的。
塔夫集團偏重於行動主義而非理論,他們私下裡對理論嗤之以鼻。由於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加困難,我們組織變得必須快速奔跑才能站住腳。當然,組織的建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行動主義開始越來越壓倒了我們的組織。僅僅強調人數的增長,卻在政治上淡化了我們趨勢的質量,削弱了幹部的力量,並使它受到各種外來的壓力和影響。雖然泰德在領導層中的政治威信很強,並起到了維持大局的作用,但在幕後,戰鬥報的編輯塔夫卻有其他意圖。
事後看來,塔夫顯然開始對戰鬥趨勢的真正影響力和他自己的角色有偏頗的看法。泰德曾不斷強調要有「分寸感和幽默感」。但分寸感恰恰是戰鬥派的領導團隊所缺乏的。他們陶醉於趨勢的成功。這些成果當然都是實實在在的,但我們必須把事情放在適當的背景下。擁有八千人的組織固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沒錯。但與數百萬人參與的英國勞工運動相比,它仍然是非常小的。塔夫和他的支持者們沒有把握住這個事實,正在迅速與現實脫節。用史達林的不朽名言來說,他們「被成功沖昏了頭腦」。
塔夫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人,對實際或潛在的競爭對手有著病態的恐懼,他認為自己的才能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事實上,儘管塔夫在組織方面有一定的天賦,但他從來都不是一個理論家,而且他深深地嫉妒那些他認為比自己水準高的人。他身邊有一群這樣唯命是從的人鼓勵著他的妄想,慫恿他與泰德對抗。但他不能公開地這麼做。反之,他採取幕後手段孤立泰德,散佈關於他性格是多麼「固執」或者甚至更惡劣的謠言。
在塔夫這個人的周圍逐漸地形成了一個小集團。他直接控制了戰鬥趨勢在利物浦和蘇格蘭西部分會,在那裡孜孜不倦地培養著一群跟班並剷除異己。雖然塔夫是一位有才華的演說家和有能力的組織者,但他所有的政治理念都是從泰德那裡得來的。
塔夫只要和泰德一起工作,他的長處就能夠得到足夠的發揮並建立組織。然而,這個時候,塔夫顯然是想通過私下破壞身邊的人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塔夫有計劃地在領導層中孤立泰德。兩年內,泰德被指責成「年事已高」,或者說得不那麼文雅的是「老年癡呆」。他被斥為「另一個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最終成為孟什維克)。而伍茲則被描述為「只不過是一介理論家」。然而,這句話比什麼都能更好地揭示塔夫及其集團的狹隘的組織心態和對理論的蔑視。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我們的趨勢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實基礎上的。一旦這個基礎被移走,整個大廈就不可避免地要倒塌——這也正是後來發生的結果。
實際上,塔夫特別忌諱伍茲。後者的理論水準比前者更高,而且大家都認為伍茲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和作家。由於塔夫總是在尋找該剷除的對手,他(錯誤地)想像伍茲是對自己地位的威脅。因此,他在每一步都千方百計地孤立艾倫,採取不同的手段,阻止他在公開會議上發言,扣留理論雜誌的經費,甚至阻撓他出版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書。艾倫的主要罪狀是,他始終與泰德關係密切,因此絕不會計較任何針對他——或其他任何人——的花招。塔夫知道,如果不與艾倫·伍茲爭鬥,就不可能除掉泰德——他擔心的是後果,尤其是在各國支部間可能造成的後果。因此,他非常謹慎地行事,盡可能地隱瞞自己的陰謀。
隨著反人頭稅運動的結束,趨勢內部的情況已經開始惡化。雖然我們對人頭稅運動的介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於組織領導層推行的「行動主義」政策 ——這有時意味著我們最積極的人在漫無目的地奔波 ——所付出的努力與增長的具體成果之間明顯不相稱。因此,組織內部開始出現沮喪和不耐煩的情緒。
這甚至影響到一些領導同志,特別是在蘇格蘭西部和利物浦。他們一直在進行群眾鬥爭,並被這些抗爭沖昏了頭。他們開始尋找通往成功的捷徑。蘇格蘭的湯米·謝里丹(Tommy Sheridan)尤其熱衷於脫離工黨。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堅實基礎和清晰的觀點,他們受到社會上短暫的情緒和當下的壓力的影響。在實踐中,他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選擇了折衷主義和印象主義。他們顯然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分寸感,完全迷失了方向。
1991年4月,他們說服塔夫在蘇格蘭發起「新的轉向」。他們聲稱這只是地方分會的臨時「彎路」,據說是為了打擊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威脅。不久之後,國際領導層內部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泰德和艾倫指責塔夫組織了一個小集團。這導致了領導層內部關係的急劇惡化。然後在5月,隨著沃爾頓國會議員艾立克·赫弗的過世,當地需要舉辦補選。塔夫周圍的團體提出推派在工黨黨內初選以微弱劣勢失敗的戰鬥派成員萊斯利·馬哈茂德(Leslie Mahmood),與默西塞德郡的官方工黨候選人和首席獵巫者彼得·基爾弗約爾(Peter Kilfoyle)公開競選的想法。他們的企圖被可笑地描述為一個原則性問題,而趨勢組織被煽動性地投入爭取補選。它代表了與我們過去整個方向的根本性決裂。在領導層中,由於艾倫當時人在國外,僅有我自己和泰德表決反對此提議。內利斯特後來私下裡說:「這簡直是牲畜在投票支持屠夫。」
我們投注了所有資源到這場補選選戰上。在全國性的會議上,有人瘋狂地誇大其詞,說勝利就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最後,作為「真正的工黨」候選人的萊斯利以2,613票的微不足道的成績獲得第三名,而基爾弗約爾則以21,317票勝選。這是一場恥辱性的失敗——要知道,戰鬥派最近在該市領導了一場群眾運動,並有效控制了議會。但塔夫和他的支持者不能承認這一點。相反,他們採用了公然的煽動手段。《戰鬥報》的頭條居然是:「2,613人投票支持社會主義!」,試圖掩蓋這種羞辱,並提高普通同志的士氣。
多數派領導人宣佈這一結果為「成功的」,全國其他地區也應效仿!這樣一來,本來是一個很容易糾正的小錯誤,卻被放大成一個巨大的錯誤方向,隨後摧毀了戰鬥派。認為一個小組織可以與工黨競爭的想法是極端荒謬的。正如我們多次解釋過的那樣,歷史已經證明,弱小的革命團體不可能通過直接的途徑接觸到工人階級的群眾。但是到了這個時候,理性的爭論在戰鬥趨勢的領導層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後者一意孤行地要把組織推向如同泰德恰如其分地描述的「走進懸崖的捷徑」。
塔夫身邊的那群人誰也沒興趣聽我們的建言。現在對領導集團唯一重要的是威望和領袖不容置疑的地位。他們得出的結論相當牽強。默西塞德的召集人戴夫·柯特瑞爾(Dave Cotterill)後來寫道:「工黨將會日漸式微」這說明當時這些人的心態中存在著荒唐的妄想。當然,正如我們當時所預言的那樣,塔夫派才是會式微的。
沃爾頓事件只加劇了工黨官僚機構對我們趨勢的迫害。「根據工黨成員在補選中為馬哈茂德競選的照片和其他可核實的證據,全國執行委組織委員會下令暫停147名疑似戰鬥派同情者的黨員權限——這是有史以來對該組織最大的一次打擊」喬治·德洛爾(George Drower)寫道:「開始了開除據稱支持戰鬥份子的工黨議員戴夫·內利斯特和特里·菲爾德的行動。」[18]塔夫領導層實際上把組織送進虎口內。
在領導層內部,泰德、伍茲和我堅決反對這種極左的「轉向」,泰德把這種「轉向」說成是「威脅著四十年來的工作成果。」正如我們在《反對派公報》中所解釋的那樣,「在群眾組織中成功地開展了幾十年的工作,使我們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之後,有人企圖使我們的趨勢開始冒險,這有可能破壞組織整個基礎。」[19]。
始終使我們與偽托洛茨基宗派不同的一點是,我們趨勢組織內部的生活是極為民主和寬容的。開除黨籍的情況極為罕見,不同的意見總是得到公平的聽證。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基於領導層巨大的政治和道德威信,而這又反映了泰德·格蘭特的政治和道德威信,他從不顧忌政治辯論,但即使是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總是心胸公正、寬容和忠誠的。但這些清廉的傳統卻被踐踏在腳下。塔夫和他的支持者並不具備與反對派進行公平競爭所需的政治武器。相反,他們利用組織機器的重量、全職人員、誹謗、流言蜚語和人格暗殺的武器,企圖削弱和壓制我們。
在激烈的派系鬥爭中,泰德和反對派受到了惡劣的對待。我們不是被當作有論點要回答的同志,而是被當作要被粉碎的敵人。他們採取最卑鄙的騷擾手段來打擊我們的士氣。當我們去中心的時候,沒有人願意和我們說話,甚至連一聲早安都沒有。後來,我們的行李要被搜查後才被允許離開大樓,等等。正如泰德對塔夫的評價:「他(塔夫)居然這麼詭計多端。他一定認為這就是政治的全部意義。這意味著他只是個粗淺的政客。」
統治集團在派別鬥爭中的方法是純粹的史達林主義。在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上,這是一次有組織的特別針對我本人的「批鬥大會」 ,泰德發表了他一生中最簡短的講話:「你們做的一切,我以前都看過。這是希利主義、季諾維也夫主義、史達林主義。用這些手段,你們什麼都建立不起來。用這些手段,你們現在有的所有設備、印刷機、辦公室等都會付之一炬。」然後他坐下來,全場一片驚愕。事實是,塔夫派不能容忍反對派。他們發現他們無法打垮我們——就像他們打垮了其他人一樣——因此,在一場鬧劇式的「辯論」之後,我們在1992年1月被毫不客氣地開除了。
反對派被開除後,不可避免地在英國和國際上導致了整個組織的分裂。在英國,反對派得到了幾百名主要是較有經驗的幹部和工會活動家的支持。在國際上,情況要有利得多。在分裂時,反對派在CWI中占多數。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丹麥、塞普勒斯、墨西哥、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的組織都支持我們。希臘支部內塔夫派和反對派各佔一半,但其中所有的工人同志都支持我們。我們在瑞典和德國支部內具有不可小看的少數派。在愛爾蘭、美國和斯里蘭卡支部內沒有舉辦任何關於分裂的辯論,我們也實際上被阻止前往這些支部來申論我們的立場。法國支部已經因塔夫的花招而分裂了,後來我們發現愛爾蘭也是如此,而被開除的同志加入了反對派。如果我們把英國排除在外,這就意味著,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國際組織的大多數同志都站在我們這一邊。
然而,在英國,我們再次淪為一個相對較小的團體,沒有資源。我們的設備只剩下一台破舊的打字機。我們設法籌集了足夠的資金,租了一間小房間,並創辦了一份月刊——《社會主義呼喚報》。然而,雖然人數不多,但我們卻得到了相當大的國際支持。儘管受到了挫折,我們還是設法帶走了戰鬥趨勢內幾位主要理論家,包括組織的創始人格蘭特,並贏得了一層重要的工會同志的支持。我們留住了一些有經驗的同志,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能建立起我們的趨勢。這些品質以前是,現在也是我們成功的最佳保證。
在分裂時,塔夫拿下了包括青年在內的絕大多數成員,他很快就失去了所有的成員,失去了報刊、金錢和組織。他一開始在各方面都佔優勢。然而十年後,他的管理成果有目共睹。他幾乎是一手把這個組織搞垮了。由於組織的財務發生危機,他們不得不賣出位於赫普斯科特路的巨大中心。他們現在靠過去收益過活,但這筆錢終究不是無限的。同時,他們也失去了整個蘇格蘭組織。正如我們所想的那樣,謝里丹最後沈浸在蘇格蘭民族主義,脫離了戰鬥派並與克里夫集團合併。
後來,大多數曾經是多數派領袖的人在士氣低落的情況下退出組織了。利物浦地區的整個領導層都被開除。塔夫就這樣成功地摧毀了他多年來負責培植的利物浦分會,這個分會曾被視為是戰鬥趨勢的旗艦。戰鬥趨勢的成員人數大幅減少,大概只剩下幾百名活躍份子(1992年分裂時他們聲稱有5000人)。甚至連「戰鬥派」這個在英國和國際間廣為流傳的名字也被毫不客氣地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從未有人聽說過的名字。簡而言之,他們成功地摧毀了幾十年來所建立的所有成果。
他們輕率地扔掉了國會議員——故意挑釁工黨開除他們的黨籍——以及數十年來耐心工作所建立的其他重要支持點。在國際方面,他們失去了多個國家支部,經歷了一系列的分裂——這些分裂仍在繼續。在他們保留了一些支持的地方,主要歸功於泰德在過去發展的政治資本。為了繼續尋找一步登天的捷徑,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的雨傘組織。當這個組織最近被克里夫集團奪下主導權時,塔夫派一氣之下就離開了。總之,他們已經表明,他們只擅長破壞別人建立的東西。十年後,一切都很清楚了。「每況愈下」的不是工黨,而是塔夫派。
不間斷的傳承
過去十年來,我們從頭開始重建了我們的趨勢組織。在英國,我們以工會中的重要支持點為基礎,現在正在重建我們的青年基礎。在國際範圍內,我們取得了一些嚴重的成功——特別是在西班牙、義大利、墨西哥和巴基斯坦。
1992年,我們創辦了《社會主義呼喚報》雜誌,該雜誌從英國和國際的角度所做出的嚴肅分析、評論和激進的政見贏得了堅實的聲譽。我們產出的高品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材料是首屈一指的。1995年,我們開始出版書籍,在國際上產生了相當驚人的影響,首先是艾倫·伍茲和泰德·格蘭特的《反叛中的理性》(Reason in Revolt)。這是自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以來,第一次嘗試把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運用到現代科學的成果中的著作。
此後又出版了《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通往革命的道路》和《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的新版。我們的書被翻譯成西班牙文、義大利語、希臘文、俄語、土耳其文和烏爾都文。《反叛中的理性》目前正在翻譯成德語和荷蘭文。我們的文章和小冊子也被翻譯成法文、中文、越南文、韓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塞爾維亞文、馬其頓文、波蘭文、印尼文、希伯來文和其他語言。
我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說,我們的趨勢組織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政治權威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1997年,我們創辦了極為成功的《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www.marxist.com),這個網站在國際上具有深遠的吸引力,全世界有幾十萬人訪問。僅去年一年,我們就有超過100萬人次的頁面成功訪問,而且訪問量還在不斷增加。我們處理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信件,國際合作者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其中許多都有姐妹網站,最近的合作者有土耳其、塞爾維亞、波蘭、愛爾蘭、南非和印尼。
我們成功的關鍵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堅定捍衛,這使我們能夠在我們以前一無所有的一系列國家中獲得重要的追隨者。我們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特別是泰德在過去60年中所作出的貢獻。因此,雖然我們在形式上是一個年輕的趨勢組織,但實際上我們代表著一條不間斷的傳承,可以把它的過去追溯到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時代。
格蘭特在與伍茲的密切合作產生出了極其重要的理論貢獻。泰德的政治經驗是我們趨勢組織的基石。過去,他以托洛茨基的方法為根基的方法和方向,起到了使組織成為英國政治的主要因素的作用。不幸的是,這一進程被不利的客觀條件和領導層的政治弱點所割裂,領導層失去了理智,被它不瞭解的事件吹離了方向。
有些人以為,在戰鬥趨勢的危機之後,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就我們而言,十年前的挫折絲毫沒有削弱我們的信心。恰恰相反,在很多方面我們都得到了極大的加強。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我們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的正確性,這些思想可以在這個或那個細節上進行修改,但它們在根本上仍然與150年前一樣。
恩格斯曾經說過,黨通過自我凈化而變得強大。戰鬥派的分裂是國際左派危機的一部分。我們從這次經歷中得到了寶貴的教訓。誠然,在英國首先是我們失去了很多人,損失了不少成果。但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我們以前也曾是少數派,馬克思主義的過去偉大導師們也是如此。這並不使我們擔心。我們深信,在世界範圍內,在我們面前開啟的風暴時期,偉大的事件將推動工人階級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行動起來。新一代人遲早會開始尋找替代資本主義的死胡同和改良主義的破產政策的辦法。
史達林主義的崩潰,在史達林主義政黨或是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內部產生了危機,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可能性。掌握了正確的思想、方法和途徑,我們就能在國內外建立起真正的群眾性馬克思主義趨勢。十年前,蘇聯的垮臺使左派——尤其是共產黨——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但現在,這個過程已經完全反轉。
在俄國和東歐,市場的引入給群眾帶來了災難。俄國的工人運動逐漸開始恢復,在共產黨黨內部,人們對托洛茨基的思想越來越感興趣。在本書付印的時候,我們的俄國同志將出版艾倫和泰德在1969年完成的著作《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的俄文版。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以《工人民主報》(Rabochaya Demokratiya)為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的思想將在俄國得到廣大的讀者,在那裡,促成新的十月革命將成為當務之急。
拉丁美洲的發展,尤其是阿根廷開始的革命,表明所謂的全球化正在表現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這是世界革命開始的時代。鑒於主觀因素的弱化,這個過程將在一個漫長的時期內展開。這將為我們提供一定的喘息空間,以便積蓄力量。我們早已對無數的宗派團體置之不理,我們對他們說。讓死者埋葬死者!我們將面向青年和工人階級以及其群眾組織的新階層,為革命運動尋找新的戰士。
泰德·格蘭特的偉大貢獻是保存了真正托洛茨基主義的不間斷傳承。在這一不可動搖的基礎上,我們將從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為幹部做好準備,以完成今後的偉大任務。本書無疑將有助於實現這一歷史目標。
我們從我們運動的偉大領袖、思想家和烈士托洛茨基那裡得到了啟發,他在史達林主義清洗審判的高峰時期寫道:
「誰要尋找身體的安適與精神的寧靜,那就讓他到一邊去吧。在反動時期,依靠官僚比較依靠真理是便利得多的。但是那些把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看作空洞聲音,而看作他們的道德生活的內容的人們──前進吧!威脅、迫害、虐待,都不能阻止我們!即令我們不能及身而見,但真理是要凱旋的!我們要傳播走向真理的路。真理是要勝利的!在命運的一切嚴重打擊之下,我將是快樂的,像在年輕時候的最好日子裡那樣快樂,如果我能同你們一道有貢獻於真理之勝利!因為,朋友們,最高的人類快樂不是對於現在的享受,而是對於將來的協力。」(托洛茨基,《我賭我的生命!》)
羅布·蘇沃爾
2002年3月18日
註釋
[1]格蘭特,《戰後時期的史達林主義》(Stalinism in the Post War Period),1951年6月,P. 19
[2]《社會主義展望報》,1951年9月
[3]哈里·拉特納(Harry Ratner),《不情願的革命家》(Reluctant Revolutionary),P. 131
[4]同上,P. 136-7
[5]同上,P. 160
[6]同上,P. 191,我的強調
[7]《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政治任務》(1957年),P. 7
[8]比爾·亨特(Bill Hunter),《革命家的生活和時代》( Life and Times of a Revolutionary),P. 155
[9]拉特納,《不情願的革命家》,P. 228
[10]羅伯特-J-亞歷山大(Robert J. Alexander):《國際托洛茨基主義》(International Trotskyism),P. 663-4
[11]拉特納:《不情願的革命家》,P. 240, 277
[12]肖恩·馬特加姆納(Sean Matgamna),《左翼的苗床》(Seedbed of the Left),倫敦1993年,P. 9-10
[13]全國內部通訊,1964年10月1日
[14]《社會主義工人報》,1969年9月11日。
[15]《社會主義工人報》,1969年8月21日。
[16]參見格蘭特,《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倫敦,1997年,P. 222-226
[17]譯者註:「短劍行動」(Operation Gladio)是由美國中情局和北約組織在西歐多國建立的地下軍事網路,以在蘇聯對西歐發動可能進軍時發動敵後襲擊。這個網路包括不少前法西斯或是納粹份子和團體。這也顯示了此一行動主旨在於反共而不是「捍衛民主」。
[18]喬治·德羅格(George Drower),《金諾克傳》(Kinnock),倫敦,1994年,P. 279
[19]《新轉向》(The New Turn),1991年8月16日,P.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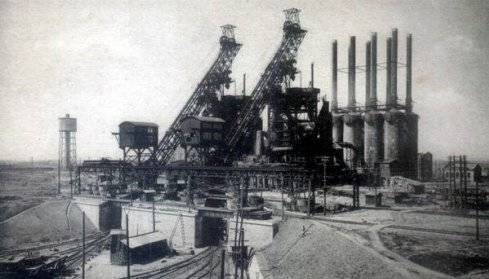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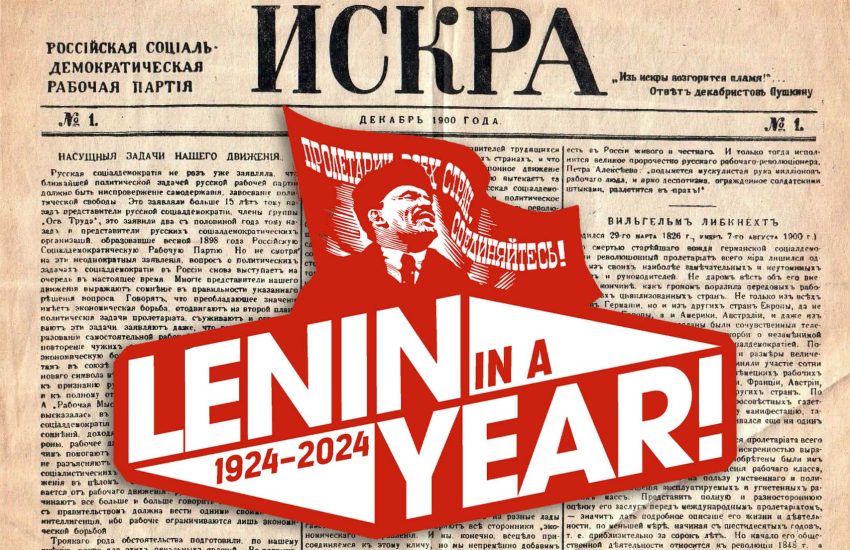

2 thoughts on “《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