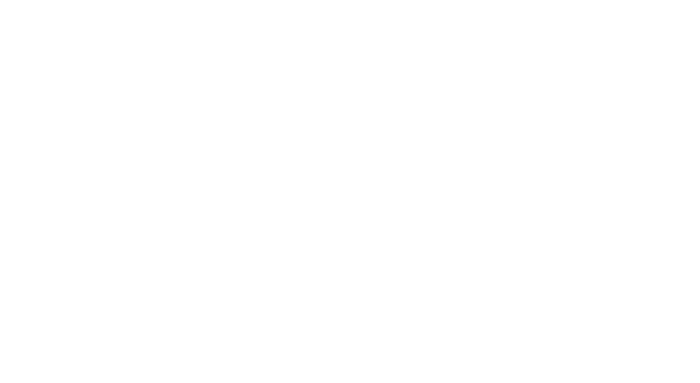如果毛澤東真的希望推進工人民主,那麼為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一直失敗?——如果毛派不願意指出毛澤東和整個官僚體制本身的反動,這恐怕就離不開打不死的「走資派」蟑螂他們神蹟一般的干預了。
今年是324警察暴力事件的十週年,當年歌手大支用《太陽花》這首歌紀錄下了現場的殘酷,展示警察如何暴力鎮壓佔領行政院的學生。 如今十年過去,在監察院去年的報告中,警察不僅嚴重違反比例原則,踐踏法治,現場指揮官責無旁貸。然而卻沒有人受到應有的處分。作為鎮壓太陽花劊子手的方仰寧在2021年鎮壓南鐵鬥爭以後,如今高升警察專科學校校長,將他當年在現場鎮壓學生的卑鄙賤招教授給年輕的警察。 近期,台灣社會乃至世界也發生了無數起警察暴力事件,我們藉著324警暴十週年的機會,帶讀者們一併統整警察暴力的各種面向。
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其意義不僅僅是反對服貿,更是明示了當統治階級的代議政治拋開群眾、遂行其專制的一面時,群眾將會行動起來,展示其巨大的潛力。
在鋪天蓋地的反「共產主義」宣傳中,經常帶有這樣一種觀念:共產黨領導人在宣揚平等的同時,也要確保自己的個人立場得到充分的照顧。這種宣傳是基於史達林統治下可怕的官僚主義的頹廢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攻擊史達林並不滿意,他們還試圖證明列寧也是如此。
在從理論上和外國例子中看到一個工人政黨應該和不應該把持的路線後,我們終於可以來到評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歷來關於「左翼」或者是工農政黨的嘗試,來為未來的台灣工人政黨組建工作指引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有四十六年。這一事件一般被公認爲中國由計劃經濟時代步入市場經濟時代的轉折點。經過國有資產逐步私有化、徹底融入世界市場、資本輸出等幾個階段之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實際上已經統治著中國,除了「特色社會主義」的狂熱追隨者以外,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
工人政黨在國際上並不罕見,且在大部分西北歐國家都是主流大黨並多次執政過,其他國家也有非常顯著的工人政黨。日本從前的社會黨和現在的共產黨也是我們上述組織定義上的工人政黨。然而我們以下舉出的德國、英國、巴西、義大利和俄國範例,是歷史上最突出代表工人政黨如何興起又如何逐漸被工人唾棄的個案。
2024年1月21日標志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對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列寧)逝世的百年紀念。毫無疑問,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
20世紀70年代的義大利有兩個傳統的工人階級群眾性政黨——共產黨和社會黨,但在它們以左還有幾個規模龐大的極左團體,擁有數萬名黨員和一批國會議員。我們不禁要問:1976 年,當義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與基督教民主黨達成協議並支持緊縮計劃時,這些團體為何未能提供替代方案?它們後來又為何垮台?
民主黨人蠱惑人心地偽裝成「普通人」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