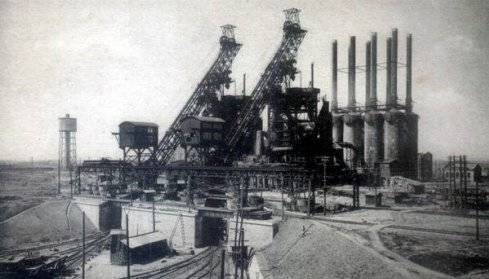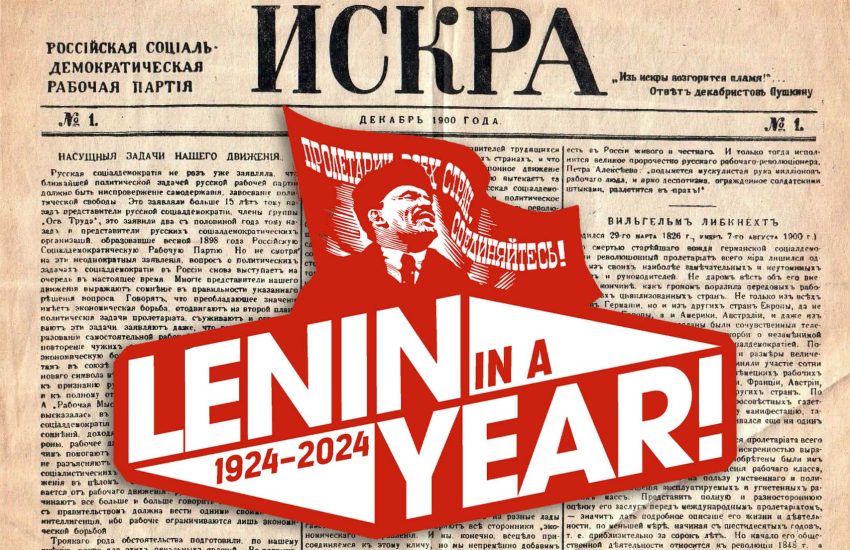托洛茨基談組織問題
(按:以下是弗雷德·澤勒(Fred Zeller, 1912-2003)的著作《三點即全部》(Trois points c’est tout)中的翻譯節選。澤勒當時是塞納(巴黎)青年社會黨人的書記,也是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運動的同情者,於1935年10月底去挪威拜訪過托洛茨基。那時,社會黨領導人正在驅逐青年社會黨人中的左派,並企圖瓦解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趨勢,這一趨勢的成員在1934年底加入了SFIO(第二國際法國支部,即法國社會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趨勢是當時在法國支持托洛茨基的團體。譯者:洪磊)
在與托洛茨基進行了這些討論之後,澤勒被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贏取了過來,脫離了以馬修·皮韋爾(Marceau Pivert)為領導的中派(即站在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之間搖擺的派系)。他最初發揮了領導作用,但後來又離開了運動。文中對托洛茨基在一些問題上的態度和想法,包括托洛茨基派面臨的組織問題,作了重要的闡述。)
大約是在1935年10月,戴維·盧塞(David Rousset)向我發出邀請,邀請我去挪威訪問托洛茨基同志。
當時我還沒有加入第四國際的行列。在這一時期,那個「老人」的名字每天都被人在泥潭中踐踏著。他們責備他像個「帕夏(大爺)」一樣生活在「城堡」裡,周圍簇擁著「僕人」和一群秘書。我並不介意他邀請我去看看真相如何。說實話,在見識過了法國社會黨和社會主義(第二)國際領導人以後,我對終於能見到一位真正的偉大革命領袖而感到萬分高興……
范(實名 Jean van Heijenoort)同志把我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完美,10月底我便離開了巴黎。我在德國的科隆和漢堡駐留了一會兒,那裡是希特勒剛剛掌權的地方。在換乘火車的空隙之間,我目睹了南軍、黨衛軍和希特勒青年軍的游行,他們用靴子的後跟敲打著人行道,並不斷粗著喉嚨吼著什麼,周圍的民眾似乎都呆住了,而且絕對都被它們嚇壞了。我仔細端詳著這些盯著頭盔、下巴上系著帶子的法西斯面孔。他們的氣息中既沒有智慧也沒有善良,似乎毫不懷疑自己,也毫不懷疑他們的領袖。
我在瑞典的特雷勒堡下了船。在火車上和車站裡呆了四天三夜後,一位挪威的同志在奧斯陸與我會合,為我接下來的旅程擔任向導。第二天早晨,一列緩慢的火車載著我穿過雪坡,穿過在寒霜中瑟瑟發抖的杉樹和閃閃發光的峽灣,直到我抵達霍內福斯,一個有著幾千居民的小鎮。其他挪威同志正在車站等我。一輛破舊的汽車把我們帶到了山上,到了韋克薩爾,一個由散落在雪地裡的木屋組成的小村莊。
那個「老人」和「老婦」(托洛茨基的伴侶娜塔莉婭·塞多娃)就住在那裡。挪威社會主義議員康拉德·克努森(Konrad Knudsen)將兩個房間分租給了他們:一間臥室和一間帶沙發的書房。餐廳是公用的。克努森夫婦在那裡吃飯的時間比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早一個小時,後者二人在一樓有一間臥室和一間帶浴缸的小浴室。
小木屋的開闊窗台提供了極好的湖景,身處於大自然絕對的舒緩和寧靜之中。我是在1935年10月的最後幾天到達那裡的。幾天後的11月7日,恰逢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社會動蕩的18周年,我訪問了俄國革命的軍事組織者。四十年後,我回憶起這段時光,不無感慨……只要我還活著,這段時光就會令我難以忘懷。
曾任托洛茨基秘書的沃爾特·海爾德(Walter Held)打開了分隔餐廳和書房的折疊門。我聽到他用德語說:「弗雷德·澤勒同志來了。」
正在工作的「老人」站了起來,用俄國人的熱情擁抱了我。他比我想像的要高大,身強力壯,肩膀寬闊,非常活潑、靈活,微笑著,看起來非常高興,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樣。他穿著厚重的羊毛襯衫,領口用領巾封住,套著毛衣和藍色的亞麻外套,褲子是灰色的。
他讓我坐在沙發上,坐到他身邊,又詢問起我的行程。他立刻就想知道法國同志們的消息。
「他們怎麼樣了?有什麼事嗎?……對了,先不要回答我。我想讓我的娜塔莉婭也在這兒聽你講。」
他站起身,到了樓梯上,用俄語告訴娜塔莉婭說我剛剛到了。

我看著那個老人。在我看來,他還非常年輕(那時他五十五歲),也非常快活。我仔細觀察了他的臉,銀灰色的頭發覆蓋著寬闊的眉毛,令人欽佩。給我印像最深的是他那雙堅毅的灰色眼睛,威嚴十足,靈光多變,頃刻間就能洞察出頑強的意志、自信、審視、驚訝、欺騙和希望。他的嘴巴極其靈動,被他那傳說中的八字胡和山羊胡須框在中間,銜接得非常完美。幾乎所有不得不與其他人鬥爭並為之受苦的人,從某個年齡段開始,唇角就會出現一道垂直的苦澀皺紋,而我在他身上卻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的一切都散發著寧靜的氣息。在我看來,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許還可以補充一點,就像安德烈·布列東(Andre Breton)指出的那樣,在他的本性深處還埋藏著一絲童年的氣息,盡管他經歷了種種艱難困苦,依舊被保存了下來。
娜塔莉婭是踮著腳尖走進來的。她的身材嬌小而虛弱,灰金色的頭發框著一張精致的臉,神情柔和而憂傷。
「現在,」老人說,「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朋友們的消息和健康狀況吧。然後,您喝杯茶,我們讓您在沙發上休息一會兒,直到吃午飯。今天下午,我們再更認真地討論些事情。」
然後,他自娛自樂地問起了一堆問題,從讓(Jean Rous)的體重,到莫里尼埃(Molinier)的「活力」,從納維耶(Naville)同志的反覆無常,到伊萬·克雷波(Yvan Craipeau)的信仰危機,還擔心他非常喜愛的範同志的物質狀況,以及他兒子列夫·塞多夫(Leon Sedov)的健康。
他的雙眼凝視著,縮放著,打量著,然後目光變得遙遠了。他殷勤而友好,試圖把你放在時間線裡,把你更具體地放在當時參與大規模衝突的人中間。「他能堅持住嗎?他會放手嗎?他會成長嗎?他的真正角色會是什麼?」我對他有這麼多沉默的問題,但我感覺還是很好。
在最初的幾天裡,我們的談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法國的形勢;各黨派、他們的政治、群眾的反映……老人要求我詳細報告危機的發展情況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內部的分裂情況。他始終專注地聽著,並提出問題,要求了解活躍分子和特殊趨勢的細節。他非常重視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主義青年的潮流正在跳過史達林主義,走向第四國際。
「法國的你們已經進入了革命的準備階段,他說。(決定權的)斧子傳到了你們手上。你們必須密切關注局勢。很快你們就會經歷宏大的事件。你們如果能花點時間,堅定自己的立場,就將發揮重要的作用。隨著鬥爭的進展,工人們會逐漸發現,他們今天所信任的人已經背叛了他們。而明天,他們就會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了。」
他認為,我們在與法國社會黨官僚的閑談中浪費了太多時間,而拖延「重新入黨」的談判是符合他們利益的。這種幻想最能分裂鬥爭派,使他們能夠依靠投降派,而投降派在面對一點兒榮譽和有利可圖的職位時,總是願意卑躬屈膝。
「同樣」,老人認為,「你們花這麼長時間跟隨著皮韋爾中派,尤其是幫助他們組建(他們的)『革命左派』(組織),是錯誤的。這些同志會轉過身來反對你們。他們會把你們自己的一些積極分子引導走,因為那些人嘴裡一旦喊起你們的口號,就會認為留在社會黨的圈子裡比獨立追隨你們更明智,當然風險也會更小。」
據他所言,那些「被驅逐出里爾」的人期待自己能被重新入黨,這只是一種幻想。
「對你們的驅逐是政治性的。社會黨的領導層正與激進派領導人在幕後籌備人民陣線政府。他們不能容忍自己的黨內存在誠實、獨立的革命者。他們還受到卡欽(Cachin)和托雷茲(Thorez)的鼓勵,而這兩個人是像僵屍一樣服從史達林的。
「你們成功的唯一機會,也是避免你們最優秀的積極分子被蠶食而失去士氣的唯一方法,就是啟動向獨立組織的過渡。你們必須為馬克思主義綱領說話。務必要在政治上武裝你們的同志。否則,在改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駭人聽聞的壓力下,他們會迅速被分解掉的。
「我認為,你們應該在你們的運動中,通過報刊、內部公報、新聞會議,以及組織一次特別代表大會,發起一場關於加入第四國際的綱領和旗幟的討論。然後,我們便可以考慮在你們的同志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進行合並。」
他又笑著說:「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在《革命報》(社會主義青年左派的報紙)上讀到你們公開宣布支持第四國際的消息,那將會是決定性的一步。我就在小木屋的屋頂上升起一面紅旗!」
一天午飯時,他問我:「是什麼決定性的因素說服了你,要靠近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組織?」
我給他講了皮埃爾·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如何邀請我去著名的咖啡館Auge rue des Archives,參加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的上一次會議。在那裡,所有的政治討論都是在出色的詳細報告後進行的,特別是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讓·魯斯、戴維·盧塞和巴丹(Bardin)的報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在社會黨的全國會議上,每個人都以支持他們自己的選舉為主,那種閑散混亂的場面與這裡截然不同。
在投票和核查授權期間,我還驚訝地得知,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在全國範圍內只有四百人。從他們發聲的強度和他們每天受到的攻擊來看,我還以為他們有幾千人呢……托洛茨基覺得這非常好笑。
這個年輕革命政治組織只有如此少的成員,卻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並能使其對手感到如此恐懼,我想它會是未來的力量之一。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都要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這個組織。
托洛茨基經常堅持討論組織問題,也正確地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不在運動的每一個層次上都培養優秀的、嚴肅的行政人員,那麼你們即使再怎麼正確,也不會勝利。尤其在法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始終缺乏的,就是組織者、優秀的財務人員、準確的賬目,以及可讀性強、編輯得好的出版物……」
我與托洛茨基最嚴重的分歧,如果我敢這麼說的話,是與民主集中制相關的。在我看來,和社會民主黨從不允許基層支部成員決定性地影響黨的方向相比,這種無情的專制觀念同樣危險。
列寧的政治局實行了中央集中制,使得奪取政權成為可能。而在史達林的統治下,它則導致了革命的失敗和所謂共產黨的墮落。
托洛斯基極力強調說,列寧的政治局實行的是「民主的」集中,而史達林的政治局實行的則是「官僚的」集中。他承認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針對這個問題有過思想鬥爭,而這使他與列寧分裂了多年。
「不過,」他又說,「列寧又一次是對的。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集中的黨,我們就永遠不會奪取政權。中央集中意味著把組織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它的『目標』上。這是領導千百萬人民與占有階級鬥爭的唯一手段。
「如果你和列寧一樣,承認我們處於帝國主義階段,即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就必須要有一個足夠靈活的革命組織,以應對秘密鬥爭以及奪取政權的要求。因此,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中的黨,能夠引導和領導群眾,並支撐他們完成這場巨大的必勝鬥爭。因此,在走出每一步時,也都需要進行集體的、忠誠的自我批評。」
他補充說,集中制的實施不能像從外部強壓在現實之上的藍圖,而是必須從政治形勢中發展出來。他舉了俄國共產黨的例子:1921年,俄國共產黨從內戰強加的極端集中的軍事形勢,轉變為了以參與經濟重建的工作場所為基礎細胞的組織。
「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領導黨的工作,並保證在各級嚴格執行由多數人決定的政策。動不動就回到方向問題上是不行的,因為這樣就會扭曲黨所確定的政策的實施。」
他經常談回到工人階級先鋒隊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宗派主義。它會使人疲憊、枯萎、士氣低落且被孤立。
「這也就是威脅法國部分的原因。這是我們敦促我們的同志作為一個『趨勢』加入法國社會黨的主要原因之一。實踐證明,這一點是正確的,因為這使得他們能夠在群眾中工作,檢驗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擴大自己的影響,並強化自己的組織。
「列寧一生都在和宗派主義的偏差作鬥爭,因為這些偏差會把革命者同群眾運動和對形勢的認識割裂開來,而事實也正是這樣。在許多場合,他不得不同『老布爾什維克』作鬥爭。當他不在的時候,這些人幾乎不能使『神聖的文本』與現實相匹配。」
托洛茨基回顧了1905年發生的事情;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當時的布爾什維克對彼得格勒蘇維埃采取了宗派主義的立場,所以只起到了微小的作用:
「理論上的例行公事,這種政治和戰術創造力的缺失,不能取代對洞察力的需求、對事物一目了然的推測能力、『感受』局勢的天賦,以及與此同時理清主要線索並制定出一個總體戰略的能力。正是在革命時期,特別是在起義時期,這些能力才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聽了他的話,我想到了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她在1918年夏天,被謀殺前不久,寫下了這樣的話:
「革命運動必須是一股沸騰的、無邊無際的生命洪流,這樣才能找到數以百萬計的新形勢、即興創作、創造性力量以及健康的批評。它需要糾正並最終超越自己所有的錯誤。」
加強鬥爭中的同志之間兄弟情誼的必要性,也是托洛茨基反覆談到的:
「有必要維護這種關系,鼓勵它、觀察它,」他反復說道。「一個有經驗的戰鬥工人,對於組織來說,是一筆不可估量的財富。要想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需要多年的時間。因此,必須竭盡全力挽救一個成員。如果他軟弱,不要打垮他,而要幫助他克服弱點,走出自己的懷疑時刻。
「不要忽視那些『跌倒』在路上的人。如果你在革命道德方面沒有什麼無可救藥的事情要責備他們的話,就要幫助他們回到組織中去。」
傍晚時分,我們在山坡上散步時,他會想起討論同志們的身體健康問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身材」問題。他很關心這一點。他想到了要關心那些已經疲憊不堪的人,想到了保存最弱者精力的必要性。
「列寧總是關注他的合作者的健康。他過去常說,『在鬥爭的道路是漫長的,我們必須能走的越遠越好。』」
組織的內部氛圍讓他很著急。在逆流而上的小先鋒運動中,內部爭執有時是最嚴重、最激烈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集團被排擠出社會黨後,分成了幾個敵對的派別:
托洛茨基說:「如果同志們把眼光放得更遠,把精力集中在對外和實際工作上,『危機』就會消退。但必須時刻注意,組織內的氛圍必須是始終健康的,必須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每個人都必須全心全意地工作,並且要抱有最大的信心。
「革命黨的建設需要耐心和艱苦的工作。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不能讓優秀的人氣餒,而要表現出自己能和任何人一起工作。每一個人都是一支杠杆,要盡可能地利用他來加強黨的建設。列寧深諳此道。在最活潑的討論、最激烈的論戰之後,他知道用什麼樣的言辭和姿態來緩和那些不當的、有冒犯性的言論。」
對於托洛茨基來說,未來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形成並鞏固組織機構。如果沒有組織機器,就不可能完成政策的實行:一切都將局限在沒有實際意義的喋喋不休上。完成巨大人類集體成就的難處,就在於明知地選擇哪種人格最適合哪種角色。組織者的藝術,就在於使個人習慣於共同合作,使每個人都互相成為對方的補充。一個組織「機器」就像一個管弦樂團,每個樂器都單獨地表達自己,但這只是為了融入並淡入共同創造出的和諧當中。
「要避免在同一個工作委員會中安排才華和氣質相同的成員。他們會相互抵消,從而得不到預期的結果。
「知道如何選擇同志去完成某項任務;耐心地解釋清對他們的期望;巧妙地、有技巧地行事,這才是真正的領導之道。
「把最大的主動權留給負責工作的同志。如果他犯了錯誤,要向他友好地解釋這如何損害了黨的利益,由此加以糾正。只有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才能給予處分。總的原則必須是允許每個人的進步、發展和提高。
「不要迷失在次要的細節中,而掩蓋了整體的情況。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除非是在決定性的情況下,否則永遠不要超越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
老人還說,不能無限期地繃緊同志們的神經。每次努力過後,都要喘口氣,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來。在組織層面,一定要做到有條不紊、精確無誤,不能抱有僥幸心理。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給自己定一個目標,哪怕是一個非常小的目標也好,但要努力去實現它。然後詳細制定一個短期或長期的計劃,並以鐵的手腕,毫不妥協地加以運用。這是實現進步和整個組織發展的唯一途徑。」
一天上午,郵遞員帶來了法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傳單和內部公報。在閱讀它們時,托洛茨基顯得很煩躁、很不耐煩。他拿著一支紅鉛筆,不停地劃去字眼、畫著下劃線,然後粗暴地說道:
「你們的油印出版物非常糟糕。它們讀起來讓人很不舒服,就和你們的報紙和其他出版物一樣。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用現代化的機器還能打印成這樣,政治分析上也許不錯,但文字讓人難以辨認。你們需要向專家請教一下這個問題。我向你保證,沒有一個工人會費勁去閱讀一份印得不好的傳單。
「我還記得我在我們敖德薩圈子裡發表的第一篇宣言。我是用紫色墨水手寫出來的,用大寫字母寫的。然後我們把它塗在一張明膠上,做成了幾十份。我們當時用的是原始方法,但我們的傳單卻非常易讀……而且也很受歡迎!」
他對我們報紙的批評是最嚴厲的:
「一份革命的報紙首先要面向工人。你們制作並編輯《真理報》(當時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報紙)的方式,讓它變得與其說是報紙,還不如說是理論性的學術雜志了。知識分子會對它感興趣,但工人不會。從另一方面來說,你們出版過幾期很不錯的《革命報》。
「但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可恥之處是,發表的報紙竟然有那麼多拼寫和排印錯誤,給人留下一種態度極其不端正的印像,這是不能容忍的。
「報紙是黨的臉面。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報紙來判斷黨的。它所面向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同志或同情者。你不能用過於高深的詞彙來疏遠任何人。一定不能讓那些偶爾拿來讀一讀的人認為:『我理解不了這些人』,因為他以後就再也不會買了。
「你們的報紙應該要有很好的表現力,簡單明了,口號總能讓人聽懂。工人沒有時間閱讀長篇的理論性文章。他需要的是風格簡明的快速報告。列寧說過:『要想有一份好的報紙,就必須要用心去寫。』
「不要再以為你們是在為自己或你們的成員寫作。那是理論評論和公報要做的。給工人看的報紙一定要生動、詼諧。工人就喜歡你嘲笑並揭露當權者的作為。
「而且,還要請你們組織中的工人同志來為報紙寫稿。要以友好的方式幫助他們。你們很快就會發現,一個工人寫出的、關於資本主義剝削實例的簡短文章,比那些自認為學術、博學的文章要好得多。例如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它們簡單、生動、可讀性強,對於普梯洛夫的工人和大學生來說都是如此。」
老人不斷提起列寧,那個對他的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那個他萬分欽佩的人。
當我向他講述我們經濟上的擔憂、定期出版《革命》所產生的問題,以及有關工作場所文件、傳單和人事變動的一切時,老人告訴我:
「一件事如果經過了深思熟慮,並且能夠表達清楚……那麼想找個方式把它說出來就很容易了!如果你對事物有明確的理論設想,那麼你也就會有實現它們的政治意願。如果你真的想成功地去做你已經明確理解了的事情,那麼你也就會有能力找到辦法來做成它。」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