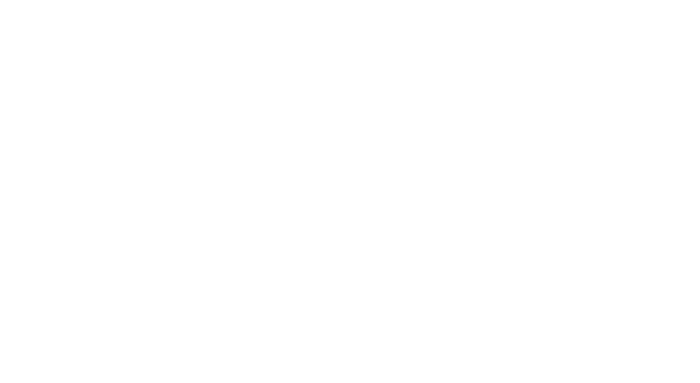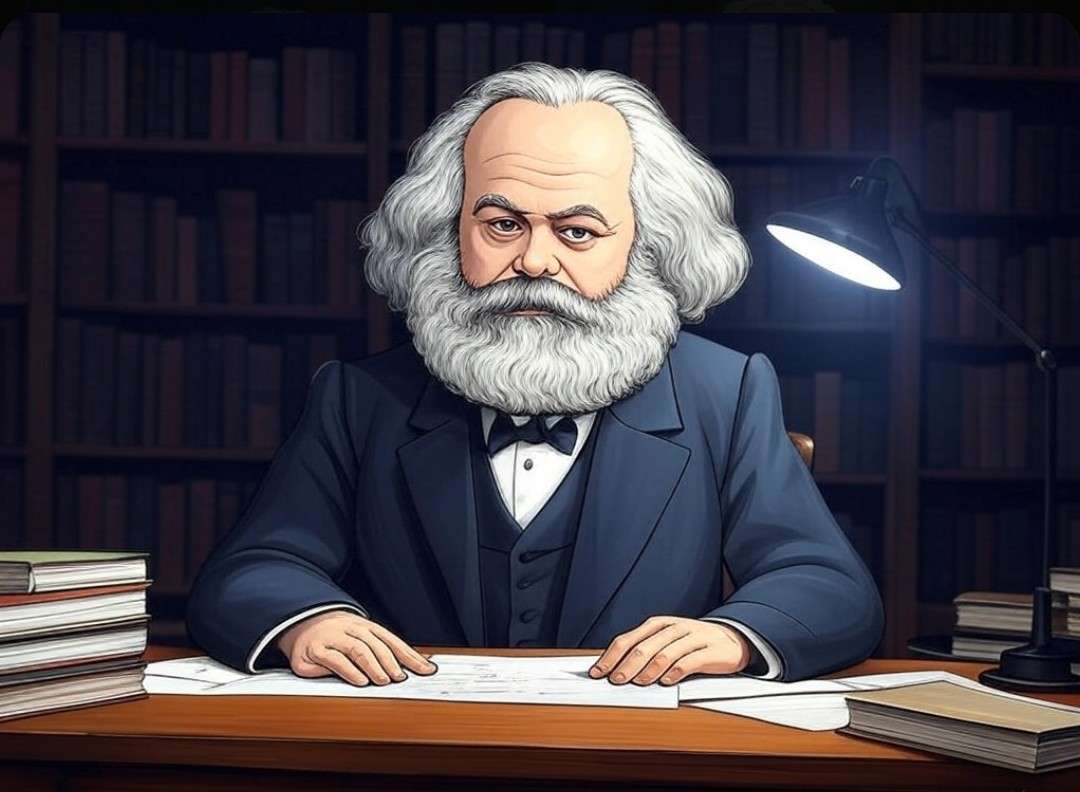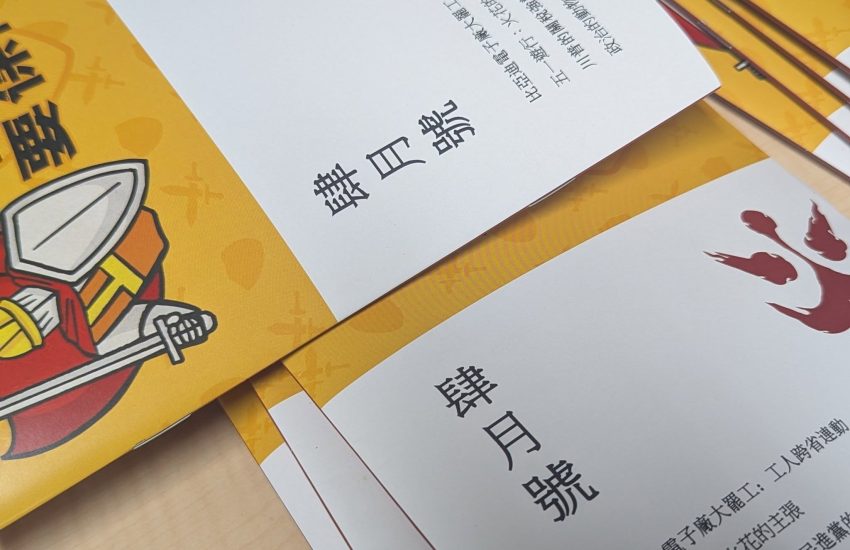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文化
由革命共產國際發行的《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In Defence of Marxism)是我們國際組織最重要的理論教育刊物。每一期的內容都對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革命事件和經濟學等領域提供深度分析。
然而,讀者們也可能注意到最近期的《捍馬》雜誌內也包含了許多關於文藝的文章,譬如關於喬伊斯、巴爾扎克、岡察洛夫等作家的生平和文學地位,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對戲劇的影響等等。讀者們可能會納悶:革命這樣拋頭顱灑熱血的正經事,理論方面不就應該著重在政治、歷史、科學和社會分析方面嗎?為什麼在《捍馬》雜誌這樣重要的理論期刊上,卻開始出現了關於文藝、文化這樣看似屬於休閒性質題目的評論?
誠然,對於我們這樣為打造革命黨而戰鬥的人來說,我們的事業絕非兒戲,需要用最嚴謹、科學和準確的態度,以最高度的紀律來從事我們的工作。而我們工作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理論:馬克思主義。
然而,許多人會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事業想像成為工人階級爭取更好生活條件的鬥爭,而把我們革命共產主義者當成一些死板中二,只會背誦馬恩列托文章,每天吶喊著鬥爭革命口號的人。許多左派的人確實也如此看待自己。
藝術、文化的作用和爭取它的目的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給工人階級更好的福利、薪資和生活環境。它能帶來的遠不止這些。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內指出,無產階級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它是要取代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統治階級,而是永遠消滅階級社會,讓全人類能夠在高度物質富裕的環境中提升我們的文明。
用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裡的話說:
「人將無可比擬地更有力,更聰慧,更機敏;他的身體將更協調,其動作將更有節奏,其聲音也將更有音樂感。生活方式將具有富於變動的戲劇性。中等類型的人也將達到亞里士多德、歌德、馬克思的水平。在這一山脈上將聳起眾多新的高峰。」
理論家艾倫·伍茲(Alan Woods)也經常如此形容革命後的社會潛力:「偉大的文化之書將被打開,供以所有人一探究竟。這才是恩格斯所謂自由的王國。」
讀者們或許可以認同這些,但可能會追問:這些是革命以後的願景,但是我們現在該學的理論不就是跟政治經濟還有辯證唯物主義最相關的東西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嗎?
當然,這些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也是剛入門的同志們必須確立好的知識基礎。然而,尤其是在哲學的層面上,我們必須記得: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全方位的分析手法,可以解釋科學、也可以解釋其他社會產物,文化也是如此。運用它來理解所有具體存在的事情是訓練我們各自哲學和理論能力必要的。因為,用唯物辯證主義來理解文化不僅可以讓我們以另一個角度洞見每一個文藝作品和其他文化產物背後所表現的社會進程,從而充實我們對這些進程的整體理解,我們更可以看到它們又展現了它當代社會對自己創造性的潛力和未來的感性想像。
因此,文化是一個我們每個人可以充實自己作為革命共產主義者思維的重要環節,教育這個道理給新一代的革命者們,賦予他們這樣的認識和技能,也就是理論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此外,文化也牽涉到了許多重要的政治問題。伍茲在《藝術是必要的嗎?》一文中提到,統治階級時常運用文化產品作為壓抑或淡化階級意識的工具,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另一方面,尤其在中國這樣有著史達林主義傳統的國家,歷史上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國家對文藝的嚴密控管、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等錯誤的理論,都是我們需要能夠回應的。
馬克思主義對文藝的態度
首先我們要確立的一點方法論就是:儘管文化和藝術固然是精神活動後創造出來的產物,但馬克思主義始終將其置放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去考察,理解這些個別創作者和作品都是在某種物質的社會環境和時代下產生的,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射了當時的情況。
但同時,不同的創作者或流派透過文藝所展現的意涵也不會是某種政治或經濟情況的直接反射,社會的整體情況和創作者個人的處境、狀態、技巧和其他特殊因素之間的關係,最終也會反映在作品的呈現及其影響上。而觀眾和作品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同樣塑造其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因此,文化的展現通常與社會整體的發展有著矛盾性和辯證性的關係。
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把文化作為一種獨特自成的領域來考察,探究這些關係,就是馬克思主義考察文化所探究的重點。這有別於許多用完全主觀的、唯心主義的方式探究創作者的心理和個人環境或是技巧等等狹隘的評論方式。但我們也不像許多機械的左派簡單把某種作品歸納為「革命的」和「反動的」這樣一筆概括的貼標籤。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會試圖去規定每個人對於每件作品、形式或者是方法都要有千篇一律的反響和看法。這本來就是不可能的。每個人的偏好和品味,都是透過千絲萬縷的偶然性塑造出來的。對於不同作品的評價,當然必須允許各種討論和辯論。
然而,這就讓我們斷論文藝就完全沒有可以探究的客觀層面嗎?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所有產物都具有一樣的價值或者同樣沒有價值這樣的理論真的經得起考驗嗎?
當然不是。不然,為什麼《蒙娜麗莎》五百年後還是被廣泛視為一幅曠世巨作,全世界的人慕名花錢去巴黎羅浮宮一睹她的風采,但是筆者畫的塗鴉就算貼錢也沒人要看呢?肯定是因為蒙娜麗莎在橫跨這麼久的歷史期間對不同時期的人類社會持續造成了可以度量的影響,而我這張塗鴉的宿命不會是進入歷史的垃圾堆,而是我家的垃圾堆。
那就讓我們看看歷史上幾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如何看待文化,我們又能從他們的方法中學到什麼吧!
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對藝術和文化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開始,他們就把文藝當作是研究社會真實存在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兩人作為當代傑出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了最高等藝術的薰陶,熟悉、酷愛當時世界內最傑出的文藝作品。儘管馬克思他作為革命者大半生涯中苦於拮据的經濟環境,但他仍然堅持對文藝的欣賞和追求作為他的精神糧食。在養育他的孩子們的過程之中,他也用生動的方式教育他們文藝的重要性,例如他們時常會在自己的客廳裡上演莎士比亞的戲碼,這也讓他的女兒艾琳娜·馬克思在從事英國的革命工作期間大量參與戲劇工作。
雖然馬恩兩人畢生的著作中對文藝著墨不多,但是他們兩人對於藝術在現實人類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視。在他們早期澄清哲學和政治經濟方法論的著作中,藝術一貫被視為研究上層建築的重要部分。譬如在1844年哲學經濟手稿內,對於私有制以及革命的作用,便有以下解釋:
「這種物質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財產,是異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質的、感性的表現。私有財產的運動-生產和消費-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展現,也就是說,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
而對於藝術本身,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了一段精簡而重要的觀察,確認了藝術自身儘管不能脫離客觀社會環境的發展,卻也衍生出自成一格的發展趨勢,他說: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他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畫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麼,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於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這段話於是簡單地澄清並確立了唯物辯證主義如何考察文藝的方法。馬恩兩人也透過他們酷愛的巴爾扎克文學作品,展現了他們如何應用這種方法。
巴爾扎克個人的主觀政治立場絕非革命共產主義者。他沈浸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沒落的貴族階級氛圍內,嚮往著反動地倒退回封建時代的烏托邦。機械唯物主義者會認為,由於他所隸屬的階級已經被資產階級打敗,他所嚮往的社會制度已經被資本主義淘汰,因此他的文化作品必然不是迂腐的,就是洩氣、軟弱無力的,不值一提的。但是馬恩兩人卻如此鍾愛他,因為他在寫作中採用的現實主義及其獨特視角,反而犀利地揭穿了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迂腐,並間接展現了革命派所追求的社會所蘊含的潛力。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寫給瑪格麗特·哈克尼斯(Margaret Harkness)的信中所指出的:
「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贊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年)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
在此,我們能看出馬恩兩人在欣賞巴爾扎克這個政治反動派的作品時,並沒有因為他主觀的政治主張而拋棄他的作品,而是將他的作品和觀點致於具體的歷史環境過程之中,找到它生動有力的矛盾和內涵。
學習怎麼用這樣的方法看待文化藝術,是我們深化自己對唯物辯證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的方式,也是深化我們理解我們所追求的世界蘊含著什麼樣潛能的途徑之一。誠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內所言:「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說完了馬恩祖師爺們如何看待、分析文化藝術,就讓我們看看列寧有怎麼樣的看法。
列寧對文藝的真正看法
如同馬恩,列寧接受了當代俄國最高等教育的薰陶,熟悉俄國和歐洲的經典文藝作品。如果多讀列寧的文章,會發現他時常會引用各式文學小說的人物和語句來補充他的論點。他經常引用歌德的巨作《浮士德》裡的經典台詞:「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來教導布爾什維克們如何避免僵硬而機械的使用理論在實踐上。而他所鍾愛的一本小說,俄國早期革命民主派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怎麼辦》也變成了列寧那本布爾什維克黨建方法經典著作的標題。
從這裡可以看到,列寧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實踐者,但是他絕對不會庸俗地忽視圍繞文藝展開的理論問題。據說他個人的文藝品味相對保守,但在早期蘇聯,他未妄想動用國家力量去限制,乃至審查當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各類前衛文藝風潮。換言之,他清楚地將個人的文藝品味和對文藝的社會政策加以區分,理解雖然他雖然不甚喜愛當時的新興文藝風潮,但是也理解這些現象是一個工人革命國家朝向新社會形態過渡的社會表徵。對於蘇聯內部重大的文藝發展,例如人類最早電子樂器——泰勒明的發明,列寧非但不會排斥,而且要求工人國家贊助並推廣這個樂器至全世界。列寧同時也酷愛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並且也提倡它的發展作為啟發群眾的途徑之一。
列寧對藝術發展所把持的開放、鼓勵態度,與後來廢黜百家,獨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史達林有著天壤之別。
不過在領導俄國工人階級贏得政權之前,列寧就曾對分析圍繞在文藝人物的政治問題展現了重要的分析手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列寧關於托爾斯泰的評論。1908年,列寧把托爾斯泰比喻為「俄國革命的鏡子」,指出這位犀利批判俄國社會卻狂熱迷信宗教的偉大文豪,展現了19世紀最後30多年俄國實際生活的矛盾條件。此外,列寧也觀察了其他政治流派對托爾斯泰的評價,並點出它們評價背後的階級觀點。托爾斯泰在1910年11月去世後,俄國社會對他,尤其是他的政治主張引起一陣熱議。有人當時運用托爾斯泰的大名,鼓勵工人階級學習他的烏托邦的反動政治主張。
此時列寧就寫了兩篇評論抨擊這些人,解釋道:
「阻礙這一(革命)運動前進的,是所有那些把托爾斯泰稱為『公眾的良心』、『生活的導師』的人。這些說法是自由派故意散布的謊言,他們想利用托爾斯泰學說中與革命相抵觸的一面。某些過去的社會民主黨人,也跟著自由派重復這種謊言,說托爾斯泰是『生活的導師』。」
由此以來,我們看見了列寧不僅觀察了文藝創作者和作品本身,也考察了其他評論者們的觀點和政治目的,並加以揭發他們,由此澄清俄國革命真正必須採取的路線。
當然,指出托爾斯泰個人政治主張屬於反動性質,不代表日後的蘇維埃政權就會把托爾斯泰和所有他的著作打成「地主階級毒草」而被摧毀。相反的,蘇維埃政府有意識地完全保存了托爾斯泰故居和文庫,將其改建為托爾斯泰博物館,並以公費聘請托爾斯泰的家屬擔任博物館的管理員,讓後世的群眾有機會參訪、學習。
列寧在蘇聯時期也對「無產階級文化」論做出了重要的理論反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論和提倡者的問題,讀者們可以參考左遼的出色長篇評論。但是簡單來說,無產階級文化論的擁護者機械性地認為任何資產階級的文化產物都該被摒棄,而革命者應該為工人階級創造出某種文化,抑或是以為工人階級現有的生活方式就應該被視為是被尊崇的文化。列寧對此在工人民主的框架下做出了理論批評,譬如在1920年他就向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代表大會遞交一份決議案草案,並申論:
「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後的鬥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
這是至關重要的態度。我們要記得:工人階級現在是一個被壓迫、被剝奪文化的階級。尊崇他們現有的生活環境及其在底層發展的文化,只不過是試圖讓他們接受現有的壓迫環境。況且,工人階級是嚮往著文化的。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各地的劇院和表演場所都爆滿了之前沒有錢或時間去享受文化的工人觀眾,想要觀賞那些有名的經典作品,這正是一個例證。「無產階級文化論」不僅是強加在工人身上的唯心主義論點,日後更被史達林主義者用來達成反動的政治目的,用以鞭策、控管群眾思想。
史達林和毛澤東如何看待文化
在這裡,我們就需要指出另一個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巨大區別,也就是兩者對文化的態度和理論。我們之前已經解釋了列寧如何正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來處理文化的相關政治問題。左遼的文章也提到了史達林如何在俄國沿用了「無產階級文化論」並因此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壟斷了文化領域的地位。但在中國,史達林主義是如何對文化造成反動影響的,也相當具有國際性參考價值的。
首先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一份惡名昭彰的演說,也就是1942年5月二日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份講話的核心概念是利用列寧於1905年寫的一篇文章,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英文譯名是“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在這裡列寧的Party Literature明顯指的是黨的出版物,但是毛澤東當時把它說成是黨的文藝,藉以做出以下的結論:
「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
這也不只是對於具有中共黨籍的人所做的限制,而是對所有統一戰線團結對象的人應該要達成的目標,他說:
「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讚成,這個團結的範圍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絡著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裡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這樣的邏輯是:黨把持著唯一革命的文藝形式,而任何要成就革命成功的人都必須遵照黨的文藝指揮來進行,不符合黨決定的文藝和創作都要先以「團結」藉口來拉攏,而後對其鬥爭。當然我們也知道在這裡,毛澤東的史達林主義式鬥爭方法不是理論上的辯論和澄清,而是組織性的排擠、剷除任何不聽話的人。
於是乎,我們就看到,在1949年後,雖然起初有些支持革命的文豪享有一定的創作自由,但是在無產波拿巴政權獨裁越來越鞏固的情況下,文化自由不斷被官僚的政治需要壓迫。從高崗-饒漱石事件到以《海瑞罷官》劇評作為幌子而發動的文革,文化雖然不是這些政治鬥爭的核心原因,但是因為文藝由於被當作是作者對某個派系的效忠代表而被暴力壓迫,無數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寶藏和創作者在文革的旗幟下被摧毀、暴打、殺害、逼上絕路。樣板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繪畫和海報,還有那些句句不離政治口號的中二八股文,變成社會唯一允許的文藝形式。說這一切與真正的列寧主義文化處理手法之間留著一條血河,是毫不為過的。
托洛茨基怎樣看待文藝
毛澤東在同一份演講裡也忍不住刺了一下托洛茨基,聲稱托洛茨基簡單地說「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是資產階級的。」但是,老托對於文藝的分析真的只是如此嗎?
在馬恩列托之間,托洛茨基大概是對文藝問題做出最多著墨的理論家。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對馬克思主義分析文藝作出重要貢獻,而讀者們也可以在如《論日常生活問題》文集和其他文集裡面看到托洛茨基對不同文化領域的看法。托洛茨基畢生酷愛文藝,在年輕時代就已經積極地寫作文藝評論,一度還想要成為一名作家。
托洛茨基認為,文藝、文化實際上是人類爭取自由和解放的表現,是人類在同物質和自身社會所佈置的枷鎖的衝撞。他不諱言在絕大部分階級社會中,藝術當然需要在統治階級能夠提供的優渥環境下展開,但這本身並不代表它就是從屬於階級的,而本身是為了解放於任何桎梏而鬥爭,無論是它所表達的內涵,還是它的表現形式。
1908年,托洛茨基就曾做出以下的見解:
「你看,參觀藝術展覽是我們對自己實施的一種可怕的暴力行為。這種體驗藝術快感的方式表達了一種可怕的兵營資本主義野蠻主義……讓我們以景觀畫為例。它是什麼?一片被任意切割的大自然,被裱起來掛在牆上。在大自然、畫布、畫框和牆壁這些元素之間,存在著一種純粹的機械關係:畫面不可能是無邊無際的,因為傳統和實際的考量注定了它必須是方形的。為了讓畫面不起皺摺、不倒扣,畫框就被裱起來;為了讓畫面不躺在地上,人們會在牆上釘上釘子,再在釘子上固定一條繩子,然後用這條繩子把畫掛起來。然後,當所有的牆上都掛滿了畫,有時還會排成兩排或三排,人們就稱之為美術館或展覽。然後,我們被迫一口吞下所有這些東西:風景畫、風格畫、畫框、繩子和釘子……
「但我希望繪畫摒棄的是它的絕對主義,重新建立起它與建築和雕塑的有機聯繫,因為它早已脫離了建築和雕塑。這種分離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哦,不!從那時開始,繪畫就展開了一段非常漫長且具有啟發性的旅程。它征服了風景,變得內向、親切,並發展了驚人的技巧。但現在,豐富了所有這些天賦之後,它必須回到它母親的懷抱–建築… 我希望繪畫不是以繩索,而是以其藝術意義與牆壁或穹頂、與建築的目的、與房間的特點連結在一起……而不是像帽子一樣掛在帽架上。畫廊,那些色彩與美感的集中營,只是我們無色且難看的日常現實的畸形附庸。」【註1】
所以我們看得見,托洛茨基始終認為藝術有著表現和超越的可能,來展現出現實的豐富、多面性。
那托洛茨基又怎麼看待政治和文藝之間的關係呢?托洛茨基試圖在藝術家和革命運動之間找到交集,試圖說服藝術家們社會革命才能使文藝和全人類得到真正的自由。在他與安德烈·布烈東(Andre Breton)和達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共同撰寫的《宣言:創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藝!》一文中,托洛茨基闡述了藝術家和革命之間的關係:
「藝術論題的自由選擇,以及消除對其探索的範圍的限制——以藝術家為職業的人,有權去宣布這是他們的不可侵害的權利。藝術創作的領域——想像力必須擺脫任何限制,必須不被任何借口去讓它被扣以枷鎖。對於那些——無論是在今天還是明天——勸告我們去容忍藝術從屬於我們認為是基本上與藝術的本質不能並存的紀律的人,我們給予一個坦白的拒絕,而我們站在藝術的完全自由的立場上,提出我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回答。
我們相信在我們時代裡,藝術的最高任務是積極而自覺地參與革命的准備工作。但除非藝術家主觀地吸收了革命的社會內容、除非他每一條神經都感受到革命的意義和實質,並且自由地尋求在其藝術中賦予其自身內在世界的體現,否則藝術是不能為爭取自由的鬥爭而服務的。」
所以,不同於毛澤東機械性地指控托洛茨基說「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是資產階級的」,托氏認為藝術是解放全人類於階級社會的一部分,而它本身如果要對解放事業作出貢獻,就需要創作者們在有意識參與鬥爭的同時,用自己的創意,而非黨的紀律來表達,而革命黨的作用就是吸引藝術家們站到革命的陣營來,如此而已。
當然,如列寧一般,托洛茨基也在理論上向錯誤的文藝理論辯論,尤其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論」。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對創作自由也不是空想地、無政府主義地理解。在捍衛革命政權和抵抗反革命的大框架下,創作的自由還是需要有一定的界線。譬如在《文學與革命》內,托洛茨基就對喜劇做出了以下解釋:
「我們需要的僅僅是嬉笑怒罵的蘇維埃的風俗喜劇。我有意用了舊語文課本上的這些術語,毫不害怕被指責為開倒車,因為,新的階級、新的生活、新的惡習、新的愚蠢,都需要有人把它們大聲說出來,而當這件事完成時,我們就將獲得新的戲劇藝術,因為,沒有新的手法,你就無法再現新的愚蠢…當然,如果您的喜劇想要說:『瞧把我們帶到哪兒了,還是退回到舊的可愛的貴族之家吧。』——那麼,審查官就會禁演這出喜劇,他做得很正確。如果您的喜劇要說:『瞧,我們正在建設新生活,可我們周圍有多少舊有的和新的卑鄙、下流和蠻橫啊,讓我們來清除它。』——那麼,檢查制就不會橫加干涉,如果在什麼地方受到了干涉,那也是因為愚蠢,我們將一同與這樣的檢查制作鬥爭。」
也就是說,喜劇乃至整個文藝完全有權去諷刺、批評新社會的不足之處,並用他來展現群眾要求社會主義社會變得更加完善的心願。而當文藝實際上是為反革命做宣傳鼓動的時候,工人民主的政權就有權去制止它,使新社會得以存續。
但是這種需要也是會存在於物質環境之下的。我們必須記得,在托洛茨基寫下這些文字時,蘇俄剛剛打贏內戰,但仍然處於孤立和拮据的狀態,且國內外反革命勢力依然構成巨大威脅。然而,如果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並在全球範圍內擴散、鞏固,那任何反革命的宣傳文藝也將失去其根基,無需再進行審查。就像今天如果某位編劇試圖用他的喜劇來鼓吹中國恢復清朝或帝制,那觀眾的笑聲就不再是他們對這齣戲橋段的共鳴,而是在訕笑創作者的荒唐。
托洛茨基對各式各樣的文藝和文化有太多太多非常值得注意的評論,本文無法一一敘述,希望這引發讀者們的興趣,自己去探索。
文化與當今革命黨的建構
我們革命共產國際的首席理論家艾倫·伍茲也花了大量筆墨在文化評論上。筆者推薦讀者們可以參閱伍茲關於莎士比亞、瑟凡提斯、肖斯塔科维奇、貝多芬、艾森斯坦、義大利未來主義等文章與講座。
伍茲深知我們在當下社會環境以及我們政治鬥爭工作的壓力下,總是會有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忽視文化的傾向,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對理論忽視的開端。各式各樣的左派組織轉向運動主義、藐視理論教育,結果就是在理論觀點上採納了工人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化、科學、哲學等等題目都跟工人生活毫無關係。工人只想要聽關於工會、薪資、待遇還有當下各國政府的消息。這一切的結果就是越來越多改良主義的主張,作為屈服於資本主義社會壓力的表現。對這種經驗主義壓力的最佳反制就是理論教育,而文化教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伍茲在《藝術是必要的嗎?》這篇社論中提到,實際上,文化也可以被統治階級用來做為壓迫的一種工具。私有化的音樂和影視工業雖然立足於盈利的動機,但也時常被統治科技作為在群眾之間散播各種偏見來淡化階級意識和防止革命的工具,儘管它的效益終究無法克服階級鬥爭作為一種物質過程的發展,但是在一定時間和條件下,確實能夠起到作用。
這當然不是某種陰謀論性質的觀察,好似所有作品都是統治者們腦袋中設計好並散布給群眾,群眾也只會消極的照單全收。雖然很明顯具有宣傳愛國主義的主旋律電影和文藝確實存在,但是也有更多其他的文化或風潮同時也會迎合並加深群眾之間的反動情緒,抑或是企圖麻痺群眾的思想。
各式各樣所謂「無腦放鬆」的「爽片」,充滿了煽情、惺色和暴力以及個人主義的老生常談,對其涉獵的性、性別關係、情感、衝突等等可以發人深省的主題毫無探究。好萊塢著重投資並不斷推銷給群眾觀看的東西,像是第一千部《復仇者》、《玩命關頭》續集,真人化老迪士尼動畫電影,等等。真正有內涵的電影大多都要在緊迫的預算和經濟限制下被製作,能不能被散播也需要經過發行公司的關口。
又如《魷魚遊戲》(Squid Game)這樣以清楚階級鬥爭或是批評資本主義為主題的影視作品爆紅全世界,又後來被盈利動機反噬,實際上,影視工作者們沒有被給予和作品收益程度同等的回報,反而被迫製作不必要的續集。於1993年出品的劃時代經典鉅片《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也是本身就帶有對資本主義不計代價盲目追求利潤的強烈批判色彩,但而後又被製片公司作為斂財工具而出品了一部比一部爛的續集。
台灣的情況則是此一鏡像的另一面。我們不乏抱有極富創意和才華的文創工作者。但是他們都必須面對缺乏必要資源實現他們作品,因為台灣資產階級和國家始終對發展文化這方面興趣缺缺,以致雖然台灣的獨立藝術雖然還是在發展,很多藝術家只能選擇旅居海外,或者到對岸去接受中共的黨國審查標準以換取創作的資源。
以商品化的文藝為主軸的所謂流行文化,一方面為文化產業資本家斂財,一方面也抑制了群眾透過涉獵經典的現代作品來提升自己的階級意識,認清當代社會體制的侷限,並投身改變世界運動的行列。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統治階級自己內部產生的文化,也由於整個社會體制已經過時,統治階級自己作為統治者們的無力,也產生了迂腐和倒退的文化。現在所謂上流社會的藝術作品都充斥著後現代主義思想的悲觀和胡謅氣息,卻又被某些收藏者用大把鈔票來買下,作為壟斷他的使用權或者是作為藝術市場賭博,抑或是鑽漏洞避稅的工具。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沒有無法提供給社會任何的進步,卻成天膽怯被工人階級推翻,從此也就反映在他們所偏好的藝術潮流內。
社會與人格的解放與提升
回到我們自己作為革命者和文化學習上的問題。作為未來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幹部組織的一員,我們認識文化不只是增強我們的唯物辦證主義哲學觀點。歸根究底,學習文化是讓我們了解真實生活的奧妙和潛力的一部分。當我們越從學習中理解人類文明迄今的發展是多麼的豐富、多面和偉大,我們就更可以理解我們現有的物質環境蘊藏著多大的潛能,從而加深我們對革命事業的堅持。
革命堅持這件事情看似是種情感層面上的事情,好像脫離了理論和理性的認識,不是我們能夠有意識控制的。但是其實不然,當你越深切有意識的認識到某件事情的真實性,你對它的情感反應會逐漸改變。大部分的人投身革命,當然都是在某種過程中對現有社會所有的不公不義和苦難所產生的反感所驅動的。我們常常說「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也當然不是錯的。
這樣消極性質的口號當然也會在社會危機越發嚴重的時代有更多的說服力。然而,如果我們僅僅是消極地說我們要爭取社會主義不然就滅亡,卻不認識到社會主義可以帶來的巨大正面發展和創造力的內涵,那麼我們最終還是無法堅持下去。學習文化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深化我們對革命後世界潛力的認識,不僅是從意識上,也是從情感上。
當你在認識一個人的時候,他的哪方面最能展現這個人的人格和獨特之處呢?當然,每個人的出身背景、成長過程、職業等等都是這個人的一部分,但最能展現出這個人個性和特殊性的部分,在絕大部分的人之間,就是他們在閒餘時間選擇從事的興趣活動。我們無法選擇和控制我們的出身和成長過程,絕大部分人的職業也不是他們偏好而選擇的,而是由於生存需要而被迫進入的。但是一個人在閒餘時間所選擇的活動,是這個人真正展現自己人格的活動。而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就是文化。
讓所有人們不必要花時間為生存為掙扎,一起爭取到更多閒餘時間的物質環境,讓自己有更多選擇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個體和集體層面創造出更多文化,就是我們想要爭取到的社會。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內將縮短工作日定位為建立自由王國的根本條件,是一個意涵無限深遠的觀察。這個自由王國內可以爆發的創造力,是就算我們正在搞革命的共產主義者也無法完全預測的。願我們這個時代能夠一起成就革命,在那個世界一起目睹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宏偉超越。
註釋
【1】摘引自伍茲,“Marxism and art: introduction to Trotsky’s writings on Art and Culture”,https://marxist.com/marxism-art-trotsky.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