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鬥爭與階級鬥爭
一百年前的今天,來自17個國家的99名婦女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人民之家舉行的社會主義婦女大會。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探討婦女節的起源,婦女在階級社會中受壓迫的根源,以及資本主義如何為解決婦女解放問題奠定了物質基礎。經驗表明,一旦婦女開始在工作場所組織起來並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就會消除分歧,團結男女工人,加強婦女和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婦女解放是工人階級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按:原文發表於2010年3月8日,譯者:梅洛)
「階級鬥爭就是婦女鬥爭!婦女鬥爭就是階級鬥爭!」 這是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口號,尤其是丹麥「紅襪子」女權運動的口號。如今許多人聽到這句口號時都會輕蔑一笑,但這句口號一點兒也不好笑,因為無論是在丹麥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婦女仍然受到壓迫。
在國際「三八」婦女節100周年之際,我們應該在整個工人運動中,在所有追求公正社會的青年和工人中間,對婦女問題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左派中的許多人拒絕接受階級鬥爭的思想。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為婦女受壓迫與階級社會是密不可分的。資本家正在利用工人階級內部的一切分歧來輔助他們對所有工人生活環境的攻勢。反對壓迫婦女的鬥爭是整個工人階級的鬥爭,不分性別;工人階級的唯一力量在於團結和凝聚力。
我們認為,如果想要爭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全人類的解放,那麼將婦女解放與階級鬥爭聯系起來是至關重要的。在丹麥,壓迫婦女的現像依然存在。以丹麥為例,通過仔細觀察婦女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我們可以了解到盡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接受教育和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原因。
國際勞動婦女節
1910年8月,社會主義婦女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每年舉行勞動婦女行動日的提案。第一年的行動日是在3月的一個星期天,但後來確定為3月8日。
社會主義婦女國際(譯按:第二國際婦女處)秘書處領導人、德國社會主義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召集了這次會議,並提議設立國際婦女節。來自 17 個國家的 99 名婦女參加了在哥本哈根狩獵路69號人民之家(後稱「青年之家」)舉行的會議。
 克拉拉·蔡特金,1897 年
克拉拉·蔡特金,1897 年
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爭取婦女選舉權,這在當時只有極少數國家被實行。丹麥婦女在 1908 年贏得了市議會選舉權,但直到 1915 年才獲得國家議會選舉投票權。
蔡特金的決議案指出:
「與各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達成一致,各國的社會主義婦女應每年組織一次婦女節。首先,婦女節應以實現婦女普選權為目標。這一主張應符合社會主義對整個婦女權利問題的理解。婦女節應具有國際性,必須精心籌備。」
會議決定行動日的要求是:
- 爭取婦女選舉權
- 反對戰爭威脅
- 為母親和兒童獲得社會照顧而鬥爭
- 反對物價上漲
第一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於1907年在斯圖加特舉行,作為第二國際大會的序幕。1889年,第二國際在恩格斯的主持下成立了。在主導著整個國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早在19世紀90年代就成立了由蔡特金領導的婦女秘書處。
在此之前,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之間一直保持著相對自由的關系。婦女運動自認為是跨政治的,受到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1907 年,工人運動決定將婦女選舉權問題放在議程的首位,並停止與「資產階級」婦女組織的合作,轉而開展自己的運動。
現在已經很清楚,社會主義者是為工人階級婦女而鬥爭,婦女問題不能與階級問題和反對一切壓迫、爭取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分開。
小資產階級婦女並不認為婦女問題和階級問題有關,而認為所有婦女在不同的階級中有著相同的利益。對她們來說,這關系到選舉權、受教育權以及成為律師和醫生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者也為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的完全平等而奮鬥,但我們也要解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盡管法律上的平等可能會確立,但這並不意味著壓迫會消失。對於中產階級婦女來說,這種女性主義這意味著她們可能會接受教育、成為醫生等,但這並不能解決絕大多數婦女的問題。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這種女性主義不承認階級對立和資本主義這一敵人,只承認所有女性與男權社會的爭權鬥爭。
在丹麥,工會和社會民主黨采取了與國際相同的立場,並於1908年通過了以下聲明:
- 只有一個工人運動是存在的,負責黨員和社會主義選民的教育。
- 黨內沒有單獨的婦女協會。只有各行各業的沒有男性工人的婦女工會,其隸屬於中央組織管轄。
- 必須為婦女入黨提供便利,她們只應支付一半的黨費。
- 婦女運動和婦女黨派(獨立於黨)是多余的。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也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兩翼,俄國革命進一步加深了這一分裂。
改良主義者認為,可以通過改良來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例如實現全民選舉權、爭取更高的工資等。他們維護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希望能逐步改良社會。
站在另一方的是革命者,其中包括蔡特金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他們解釋說:不能簡單地逐步改良社會,資本家的任何讓步都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成果。不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就無法實現人的徹底解放。
革命派在俄國革命後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該組織堅持將 3 月 8 日定為國際婦女節。
 德國革命家蔡特金盧森堡(1910 年)
德國革命家蔡特金盧森堡(1910 年)
受壓迫的婦女
全世界13億貧困人口中有70%是婦女和女童。發展中國家約有25%的男性因缺鐵而患貧血症,而同病症患者在女性內占 45%,缺鐵導致每天有300名婦女死於分娩。
在發展中國家內,許多地方的婦女仍遭受著野蠻對待,婦女在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被賣為人妻。在巴基斯坦,如果婦女有損男子及其家庭的名譽,就會被潑硫酸毀容或是被殺害。在法庭審判中,需要五名女性證人才能推翻一名男性的證詞,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哲學家夏爾·傅立葉(Charles Fourier)說過:「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用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幸運的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的條件已經大為改善。主要是因為這裡的經濟發展更進一步,因此條件才得到了改善,文化也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但是,即使條件改善了,法律平等了,壓迫婦女和男女不平等的現像依然根深蒂固。丹麥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丹麥於1976 年通過了《同工同酬法》,從那時起,男女之間的工資差距一直停滯在 12-19%之間,視職業而定。這種差距既是男性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多於女性的部分原因,又是女性每天在家務勞動(家務、送孩子去幼兒園等)上花費的時間平均多於男性一小時的原因。社會一直在進步,技術的發展理應意味著更多的自由時間。可是恰恰相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場所的工作時間都有所增加。
世界範圍內對利潤的追求和競爭的加劇,一方面加劇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提高了工作節奏和生產力水平,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工作時間的延長。這是一個與資本主義生產機制密切相關的世界現像。與此同時,過去三十年來工人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侵蝕,社會服務的私有化和福利預算的削減使工人階級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因為他們要保障對子女和老人的照顧。自 1987 年以來,男性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增加了一小時,女性增加了一個半小時。
從法律上講,婦女不再依賴於男人,但眾所周知,作為單身母親是非常困難的,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撫養子女和所有其他實際事物。雖然法律上的依賴已經廢除,但仍有千絲萬縷的紐帶將婦女與男人和家庭捆綁在一起。
歷史上女性失業人數遠多於男性,女性一直被用作勞動力的後備軍,在經濟危機期間,她們受到的衝擊往往最嚴重。在當前的經濟危機中,我們第一次看到歐洲以及丹麥的男性失業人數多於女性,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危機對私營企業造成了沉重打擊,而在這些行業就業的主要是男性。在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將看到對福利的嚴厲打擊,也就是對許多婦女工作的公共部門的打擊。當有大量工人失業時,資本家就會開始雇用男性。(誰會雇用一個育齡婦女呢?)許多婦女於是會想:與其去找一份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工作,還不如多生幾個孩子。(譯按:丹麥的少兒補貼børnepenge、兒童津貼børntilskud、托兒所/不入托補貼等生育福利制度非常發達。)
婦女問題不僅僅是工資上可衡量的差別,也不僅僅是誰在家裡做什麼的問題。婦女問題不止涉及到婦女的生活狀況,還是一個意識形態和文化問題。針對婦女的偏見和偏執依然層出不窮,隨著資本主義的普遍衰落,文化也在野蠻化,尤其是在婦女的代表性方面。
由於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階段和文化發展水平不同,世界各地對婦女的壓迫有多種形式。但無論婦女受壓迫的形式如何,其壓迫根源是相同的,因此解決辦法也是相同的。
不平等的起源
馬克思主義者是歷史唯物主義者,這意味著我們將人類物質條件的演變視為根本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解釋了婦女受壓迫是如何與階級社會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歷史的早期,人類只能生產僅夠自己生存的產品,沒有多餘的產品,因此當時不可能存在不平等。
如果說存在勞動分工的話,那也是兩性之間的勞動分工,其基礎是婦女由於生育、哺乳等原因而在部分時間裡被束縛在「家裡」這一生理事實。早期原始社會男女分工的確切性質尚不清楚,但隨著生產力的初步發展,兩性之間出現了分工。婦女的任務除了照顧孩子之外,就是采集草根、漿果等,尤其是做飯。男人的任務則是狩獵、在戰爭中保衛領地等。許多研究表明,婦女的作用對早期人類生存至關重要,婦女受到極大的尊重,例如,氏族以母系血緣維系,因為在生理上母親是唯一可以確定的父母(譯按:氏族社會的群婚制難以確定誰是孩子的父親)。
重要的是,那個社會與我們今天所知的社會完全不同。雖然父權制是一個女性受壓迫的社會,但沒有任何跡像表明在父權制之前的母系社會裡女性壓迫過男性,只有兩性間的相互尊重。當時沒有我們今天所知的父親和母親組成的家庭;家庭以氏族或家族為單位生活,撫養下一代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任務。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發展出了能夠滿足自身基本需求的生產方式。他們開始耕種土地、建造圍欄和飼養動物。人類第一次開始生產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剩餘產品。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這也意味著第一次出現了不平等。一些人開始比其他人擁有更多,隨之產生了階級社會。除了社會被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之外,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出現了。屬於男人的傳統工作開始創造剩餘,這使他們處於優越地位。這意味著男人如果想把財產留給後代,就必須以男性血脈為紐帶,於是男性主導女性的家長制家庭出現了。
「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女性開始淪為生殖機器和男性奴役的對像,男性憑借他們掌握財產的事實,依據手中的經濟權力來支配新的家庭秩序,開啟了男性的統治時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對婦女的壓迫是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而產生的,因此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與反對階級社會的鬥爭密不可分。生產方式的變革也導致了國家的興起,壓迫的觀念和形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婦女解放的基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解釋了女性在世界歷史上的失敗是如何導致婦女的工作失去其社會性的。同時,他還解釋了資本主義如何第一次改變了這一狀況。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整個家庭都被卷入了生產,這一方面給婦女帶來了有償勞動和家務勞動的雙重負擔,另一方面也為婦女解放奠定了基礎。通過工作,婦女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而參與階級鬥爭。
「男女婚後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情況也不見得更好些。我們從過去的社會關系中繼承下來的兩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在經濟上受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的古代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委托婦女料理的家務,正如由男子獲得食物一樣,都是一種公共的、為社會所必需的事業。隨著家長制家庭,尤其是隨著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產生,情況就改變了。家務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干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只有現代的大工業,才又給婦女——只是給無產階級的婦女——開辟了參加社會生產的途徑。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她們仍然履行自己對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務的義務,那麼她們就仍然被排除於公共的生產之外,而不能有什麼收入了;如果她們願意參加公共的事業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麼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義務。不論在工廠裡,或是在一切行業直到醫務和律師界,婦女的地位都是這樣的。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
現在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須是掙錢的人,贍養家庭的人,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就使丈夫占據一種無需有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的統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不過,在工業領域內,只有在資本家階級的一切法定的特權被廢除,而兩個階級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權利確立以後,無產階級所受的經濟壓迫的獨特性質,才會最明白地顯露出來;民主共和國並不消除兩個階級的對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個為解決這一對立而鬥爭的地盤。同樣,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的獨特性質,以及確立雙方的真正社會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時候,才會充分表現出來。那時就可以看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我們的重點)
在丹麥,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婦女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歷了長期的復蘇,生產得到了巨大發展,世界市場也得到了擴展,這使得福利得以擴大。家務勞動的普遍減輕以及育兒、照顧老人等壓力的減小,使婦女有可能從事有償工作(丹麥的育兒比例居世界之首)。與此同時,丹麥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公共部門,雇用了許多婦女。
丹麥的女性就業率,即勞動適齡婦女的工作比例急劇上升。1960年,女性就業率為33.9%,而男性就業率為83.6%,但到1981年,女性就業率上升到70.8%,而男性就業率為86.8%。1998 年,男性就業率降至81.6%,而女性就業率則增至73.2%。
1967年,婦女在勞動力中占80萬人,1998年的相應數字為130萬。1967到1998年,勞動力總數從 230 萬增加到 290 萬。
相比之下,英國和美國的相應數字如下:
1971年英國:女性占 42.4%,男性占 80.6%。
1973年美國:女性 42%,男性 75.5%。
1990年英國:女性為 50.3%,男性為 70.5%。
1990年在美國:女性 54.3%,男性 72%。
2008年英國:女性 56.2%,男性 68.5%。
而在瑞典,婦女在勞動力中所占比例分別為:
1975年:42%;1980 年:45%;1985 年:47%;1990 年:48%;2008 年:47%.
婦女參加工作為婦女解放奠定了基礎,但也僅僅是基礎而已。戰後的復蘇是歷史上的一個例外,危機爆發於 20 世紀 70 年代初。福利的擴大或多或少地停滯了;公職人員的條件年復一年地受到攻擊。兒童、病人和老人的條件惡化,這尤其給婦女造成了巨大壓力。資本主義並沒有為勞動婦女或世界大多數人口創造繁榮,只有通過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才能為全面解放奠定基礎。
婦女鬥爭與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消滅婦女壓迫的潛力已經形成,同樣,廢除一切壓迫的基礎也已奠定。資本主義最初是一種進步的制度,它將生產手段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現在可以生產出足夠多的產品,沒有人需要遭受苦難,不平等可以通過大幅提高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來消除。然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生產是為了盈利,而不是為了人類的需要。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數以百萬計的人失業,而其他數以百萬計的人疲於奔命;新技術的引入是為了讓人們更快地工作,而其他的人則被解雇。
有了計劃經濟,我們就能立即提高產量,並利用技術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工作時間將立即縮短,這是婦女解放的關鍵一步。與此同時,我們還將能夠引進一系列其他東西,使我們更接近婦女解放。
首先,我們將利用現有資源提高公共福利,使工人及其子女、老人和病人獲得體面的條件。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技術來消除或多或少的家務勞動。掃地機器人、人人都能使用的洗衣機、公共洗衣房、市民餐廳、人人都能享用的優質健康和廉價食品、所有幼兒園、學校和所有工作場所的膳食、翻新的住房、公共窗戶清潔、清潔幫手等等,將僅僅是人類解放任務的開始。我們目前的前景受到當前形勢的限制;我們的子孫後代將發展所有這些有益於人類解放的事物。
但這一切都不會自動實現,這需要沒收資本家的財產,消除他們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也就是說,工人階級必須接管最大的公司,從而控制經濟的關鍵部門。今天,少數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即工廠和機器等。正是他們決定生產什麼以及何時生產,這取決於他們能從什麼產品中賺取利潤。但實際上,財富是由絕大多數人創造的,即工人階級,他們每天都要為資本家工作。工人階級必須接管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例如丹麥的 200 家最大的公司——這樣,大多數人才能民主地決定生產什麼,才能制定出盡可能利用現有技術和生產的計劃,從而提高產量,降低工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消除一切奴役女人和男人從事家務勞動和為他人工作許多小時的現像。通過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人類在文化、科學、創造力等方面的真正潛力將首次得到充分發揮。
俄國革命後,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非常重視婦女問題,十月革命首次允許了最廣大的群眾參與政治。
「在資本主義舊社會裡,要從事政治活動需要有特殊的素養,因此,甚至在最先進、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婦女也極少參加政治活動。我們的任務是要使政治成為每個勞動婦女都能參與的事情。自從土地私有制和工廠私有制被消滅、地主資本家政權被推翻以後,政治任務對於勞動群眾和勞動婦女,已經是一種簡單明白、大家完全能參與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婦女處於無權的地位,與男子相比,她們是極少參與政治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有勞動者的政權,有了勞動者的政權,政治的首要任務就同勞動者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了。」(列寧:《論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在莫斯科市非黨女工第四次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19年9月23日)
布爾什維克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法律上確立了完全的性別平等。除其他事項外,他們還引入了離婚權、墮胎權和教會外的公證結婚權。但正如列寧所解釋的,法律上的性別平等遠遠不夠。必須利用生產的發展來建立托兒所、學校、公共廚房,並發明方便家務勞動的機器。今天,這些東西很多都已經存在,但首先它們並不向小市民提供,而且這些服務的質量也不斷受到利潤的影響。如上所述,無論男女,家務勞動和外出工作都在增加,而自由時間和養育兒童的質量卻在下降。
我們的願景不是分擔家務勞動和有償勞動,而是消除所有苦役。
「布爾什維克革命即蘇維埃革命徹底鏟除了婦女受壓迫和不平等的根源,這是過去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們蘇維埃俄國,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經完全取消了。蘇維埃政權徹底消滅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別可恥、卑鄙、偽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對子女關系上的不平等。
這只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哪怕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不敢走這第一步,因為它害怕觸犯「神聖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廢除土地和工廠的私有制。這樣,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使婦女獲得真正徹底的解放,通過從單獨的瑣碎的家務勞動向社會化的大規模勞動的轉變擺脫「家庭的奴役」。
這個轉變是困難的,因為這關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習以為常的、陳舊和僵化的「規矩」(老實說,這不是什麼「規矩」,而是醜惡現像和野蠻行為)。但是這個轉變已經開始,事情已經向前推進了,我們已經走上新的道路。」(列寧:《國際勞動婦女節》,1921年3月4日)
但是,蘇聯經濟的發展還不足以消除家務勞動和家庭——想要消除家庭,必須拿其他東西取代它。正是蘇維埃俄國的落後和封閉,為以史達林為首的官僚集團奪取蘇聯政權奠定了基礎,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蘇聯沒能發展出新的家庭類型,而是回到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社會的規範。史達林領導下的官僚機構不是與不平等和壓迫作鬥爭,而是需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隨著蘇聯官僚主義的墮落,蘇聯公民,特別是婦女的自由急劇減少。墮胎和自由離婚的權利被廢除,工人和農民婦女仍然被束縛在家務勞動中。列寧和托洛茨基時期的蘇維埃俄國還對同性戀采取了最先進的態度,但史達林官僚集團同樣將這一點完全推翻了。沒有民主,計劃經濟是行不通的,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言的那樣,蘇聯經濟最終崩潰了。
然而,蘇聯的史達林主義墮落並不能成為拒絕社會主義的理由,我們在蘇聯看到的並不是社會主義。但革命最初幾年取得的成就表明,革命是勢在必行的第一步,它為婦女和人類的解放奠定了整體基礎。
「同樣,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條件而作的物質准備,基本上不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作分離開來。工人國家必須變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兒童的公共教育、將家庭從廚務和洗濯工作的重擔下解放出來,得以嚴肅解決。我們的經濟若沒有顯著的改善,就無從想像把家務工作和兒童教育社會化。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把家庭從家務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些重擔現在正壓迫著家庭,令其解體。洗衣工作應交給公共洗衣房,膳食應交由公共食堂,縫紉交由公共工場。兒童必須交由敬業樂業的良好公共教師來教育。這樣一來,丈夫和妻子間的盟約才得以從任何外來的或偶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一方不再依賴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終於確立,雙方的盟約將系於相互愛慕。當然這盟約會因人而異,但對誰都是沒有強制性的。」(托洛茨基:《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1923年7月)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必須在公共餐廳就餐,也不意味著永遠不允許自己做飯,公共兒童教養也不意味著孩子不能由家人撫養。它的意思是取消了所有強制措施。你不必每天買菜、做飯、洗衣、打掃衛生和准備盒飯;但你只有在願意的情況下才會做這些事情。托兒所、學校、休閑中心、醫院、老人護理中心等都將配備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他們有時間做好本職工作,不斷提高專業水平,同時工作時間也將立即縮短。
今天,我們在技術創新方面顯然取得了更大的進步,例如洗衣機、洗碗機、微波爐等。與當代發展相比,布爾什維克的目標具有驚人的遠見卓識。試想一下,在當前的技術水平下,我們今天能取得什麼樣的成就。
那麼,我們該如何爭取婦女解放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深入探討男女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
生物學與女性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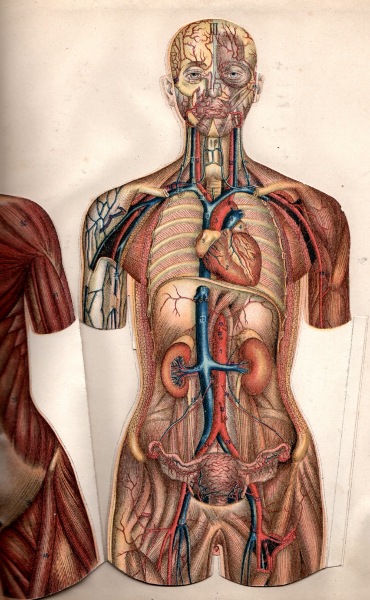
有些人認為,男女不平等的基礎是生物性質的。這種關於生物學的爭論有多種形式。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受壓迫是父權制造成的,而父權制是男性壓迫女性的天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人類早期的歷史表明,婦女並不總是受到壓迫,並不總是處於低於男性的地位。因此,沒有證據表明男性壓迫女性是他們的天性,正如人與人之間相互壓迫一般也不是他們的天性。天性論是唯心且悲觀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還有人提到「女性天性」。所謂「女性天性」的說法與「壓迫女性是男人的天性」的說法一樣反動。這種觀點類似於那些試圖說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的本性是貪婪、自私等。事實上,「人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人性」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新石器時代的人與現代人之間的差異遠遠大於當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差異。看看非洲原始部落和當今西方世界對女性行為的要求有何不同就知道了。或者看看在好萊塢長大的女孩和在中國農村長大的女孩之間的差別,這種差異是巨大的。
泰德·格蘭特和艾倫·伍茲在他們關於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的著作《反叛中的理性》中解釋了人性是歷史的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說,‘人類自己創造自己’。人性與意識一樣,是當時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的產物。這就是為什麼人性會隨著社會自身的發展而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化的原因。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人的特征似乎是通過基因在生物學上固定下來的,這就為‘你無法改變人性’的神話提供了依據。事實上,所謂的‘人性’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經歷了多次轉變和再轉變。」(《反叛中的理性》,英語版第329頁)
但有人會反對,因為女孩和男孩的行為方式確實不同。男孩更喜歡玩武器和汽車,女孩則更喜歡玩洋娃娃。(譯按:這其實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而影響個人的意識的體現。廣義上人的經驗和成長環境,狹義上顏色被社會賦予的定義,顏色的使用環境和頻率,顏色在藝術上和技術上的組合和運用等都會影響人的選擇。)最近,一位母親在電視上回答「為什麼給她的女兒買女孩子的玩具」時說:「她太喜歡粉紅色了,我相信這是遺傳。」這就是我們社會中隨處可見的生物學論證的庸俗版本。這種思維方式常被用來支持一種反動觀點:婦女獨自照顧孩子是母性和本能,因此她們天生就屬於家庭。
不同的成長環境
如何區分生物學和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即從男孩和女孩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受到不同的教育。當然,這種現像不會自行改變,研究表明,在丹麥和瑞典等發達國家,這種現像依然存在。這是所有國家的固有文化,因為所有國家都存在階級和不平等。既然男女沒有接受相同的教育,我們就無法斷定男孩和女孩在行為方式上有什麼生理差異。我們認為,男孩和女孩的不同的成長方式無疑影響了他們性格的形成。歷史表明,人類的行為方式、所珍視的准則和價值觀並不取決於「人性」,而恰恰取決於我們成長環境和受養育的物質條件。
丹麥語言和心理學副教授、專門研究兒童大腦發育的安-伊麗莎白·克努森(Ann-Elisabeth Knudsen)描述的一項測試表明,我們是如何從嬰幼兒時期就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兒童的。在實驗中,一組志願者被要求照顧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半小時。實驗在一個裝有隱藏攝像頭的房間裡進行,孩子被特意穿上了不分性別的衣服,所以無法分辨出男女性別。
「與孩子一起坐了一會兒後,所有測試者(包括男性和女性)都覺得受不了了。在(孩子)母親回來之前,所有受試者無一例外都會拉一下尿布,以確認孩子的性別!隨後,我們可以從視頻記錄中明顯看出他們的欣慰之情,就好像他們在說:‘哦,你就是那種性別!’: ‘哦,你真好!現在我知道怎麼抱你、和你說話、和你玩了。’這發人深省,尤其是考慮到三個月大的女孩和男孩在生理需求上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因此,我們對待幼兒方式的不同,可能深深依賴於我們無意識的性別期望」(安-伊麗莎白·克努森:《好女孩和笨男孩》,2002 年)
克努森的基本觀點是:「大腦的發育會受到影響。」因此,當我們區別對待男孩和女孩時,他們的大腦發育也會不同。幸運的是,大腦的發育貫穿一生,因此也會受到整個生活的影響。
實驗表明,女孩和男孩從出生開始就受到不同的影響,正如上文所述,「女性天性」和「男性天性」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化。隨著影響因素的變化,女孩和男孩的發展也在發生變化。因此,說女性屬於家庭、不懂數學或在其他方面不如男性是沒有生物學依據的。就像說男人有壓迫女人的生理衝動一樣,也沒有任何依據。人類的發展是受環境影響的。
女童和男童從一出生就面臨著不同的期望,而隨著資本主義的普遍停滯,以及文化的退化,這種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瑞典監察專員最近譴責了玩具反鬥城的一本玩具目錄,因為其中的性別定型觀念太強。只要翻開最近的玩具目錄,就會發現頁面越來越多地分為粉色和藍色:帶車把籃子和兒童座椅的粉色兒童自行車適合女孩,而兩側帶火焰的藍色自行車適合男孩;洋娃娃是女孩玩的,而樂高積木則是男孩玩的。
大腦研究表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旦消除了目前壓在我們身上的所有負擔,人類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這無關性別。當人類最關心的問題不再是獲取每日的面包時,就可以將精力用於發展我們每個人(無論男女)所擁有的才能。
社會建構主義?
為了反對這類反動論點,即女性受壓迫是基於生物學的自然現像,女性主義中出現了一個學派——社會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者正確地指出,性別是由社會建構的,並不是先驗的生物學給定的。但社會建構主義者不僅否認生物學的作用,還否認物質因素的影響。他們認為:婦女受壓迫沒有完全沒有物質基礎。
羅斯基勒大學副教授克里斯特爾·斯托姆霍伊(Christel Stormhoj) 這樣解釋道:
「生物性別與社會/文化性別之間的差距已經消除。身體在邏輯上或時間上並不存在於其表述之前,而是一個真實的客體[……]這意味著,通常所說的生物性別被視為部分由話語和規範構成(譯按:注意!後現代主義哲學最常用的詞「話語」、「敘事」、「脈絡」、「規範」,他們認為社會交往中的形式在人類歷史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並能通過改變「話語」和「規範」來根除一切不公。),因而是一種效果[……]因此,性別不能被視為建立在[……]話語之外的物質性基礎之上。」 (斯托姆霍伊:《社會科學女性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理論立場》,載於《社會科學中的科學理論》, 2003)
許多左翼青年被這些觀點所吸引,因為它們斷然拒絕生物學論證,批判既有的壓迫性體制規範,表達了對當權者的普遍反抗。關於性別概念是如何產生的,已經有許多有趣的社會建構主義研究。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反對社會建構主義,因為這種理論既不能解釋也不能改變對婦女的壓迫。
首先,我們必須自問:這種社會建構的基礎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你會得到這樣的答案:社會建構是相互演變的。是的,但第一個建構的起源是什麼,為什麼建構朝著一個方向而不是另一個方向發展?社會建構主義者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社會建構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唯心主義理論。它不是人們日常所理解的理想主義,不是美好的理想,而是哲學上的理想主義,它把歷史解釋為思想的歷史,把人們的行為解釋為抽像的思想,而不是物質的需要。在哲學唯物主義中,觀念和思想也很重要,但它們並不是脫離物質基礎而獨立存在的。
因此,解決方案同樣變得模糊不清。如果重要的是社會建構、規範和語言,而物質基礎並不存在,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是努力擴大規範的範圍,證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這就產生了大量(通常是好的)文章、研究等,展示壓迫性的規範,以及各種家庭和生活形式的「社會實驗」,例如我們在 20 世紀 70 年代看到的。許多實驗,例如集體生活方式,都有許多好的一面,例如共同分擔家務、照顧孩子等,但它們無法解決壓迫問題,特別是婦女受壓迫的問題,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即壓迫的物質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已經解釋過,社會結構、思想、規範、觀念都有其物質基礎。
馬克思主義與意識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這首先意味著我們認識到,世界是在我們的意識之外獨立存在的。沒有物質的大腦,就不可能有思想,也就不可能有性別、構造等概念,而物質的大腦需要身體,身體又需要吃喝。思想和規範最終取決於物質基礎,馬克思是這樣解釋這種聯系的:
「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
物質決定思想,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時,思想也會發生變化。上述內容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主義絕對沒有機械地看待物質與觀念之間的關系,許多人試圖這樣聲稱,而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也一直這樣做。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機械地看待經濟與思想之間的關系。為了絕對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引用了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話: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像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系,認為這種聯系並不存在)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弗·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1890)
事實上,人類意識是非常保守的。在正常的歷史時期(占絕大多數時間),它遠遠落後於物質基礎的發展。從表面上看,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工人們不願參加鬥爭,會默默接受老闆的一切攻擊。但是,不能根據任何特定時刻的表面情況,就意識和階級鬥爭如何發展得出結論。正是這種想法讓一些宗派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喪失了革命意識。
在工作場所,表面上可能風平浪靜,工人們默默地接受老闆說的一切:他們不能互相打招呼,否則就會被解雇;他們必須加快工作速度;必須提前15分鐘到公司換衣服;多工作半小時,等等。一切秩序井然,什麼也沒發生。但終有一天,工人們受夠了,他們不准備再接受任何東西,於是他們開始罷工。正如《聖經》所說:「那在後的將要在前。(the last shall be the first.)」
意識的發展不是直線式的,而是螺旋上升的。在鬥爭過程中,意識會跟上客觀形勢的發展,迅速向前。這顯然不是直線前進,既有失敗、挫折,也有向右和向左的轉折。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每走一步,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都要盡我們所能,提高工人階級對自身力量的認識,得出正確的結論。
“物質與意識之間存在辯證關系。創造歷史、改變世界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但他們是在物質條件所設定的框架內進行的。當物質基礎發生變化時,最終也會改變思想。
關於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一定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於社會之上。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1845年稿本)
絕大多數人都是從經驗中學習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還必須開展思想鬥爭,反對壓迫婦女和對婦女的任何偏見。但是,即使我們反復解釋我們生活在一個階級社會中以及廢除私有財產的必要性,也只有少數人會因為讀了一本書或聽了一次政治演講而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只有通過鬥爭,絕大多數人才會得出革命性的結論,婦女問題亦如是。
婦女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圖片來源:由卡洛·尼古拉( Carlo Nicora)在Flickr 上拍攝
圖片來源:由卡洛·尼古拉( Carlo Nicora)在Flickr 上拍攝
女性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區別在於,女性主義者將婦女問題置於階級問題之上或與之相提並論。他們認為,婦女受壓迫與階級壓迫、種族壓迫等處於同等地位(也就是說,盡管他們之中有真正承認存在階級壓迫的人,但也有許多人拒絕承認階級壓迫)。馬克思主義者解釋說,階級壓迫是根本性的。這並不意味著貧窮的黑人婦女可能不會比白人男性工人更痛苦。這意味著,階級分化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壓迫所圍繞的基本矛盾。正如我們所解釋的,對婦女的壓迫起源於階級社會。婦女問題離不開階級問題,階級問題也離不開婦女問題。工人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反對一切分裂。婦女鬥爭和階級鬥爭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隨著普選權等最基本的法律權利的實現,婦女問題就是階級問題變得越來越明顯。資產階級太太要求獲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接受與男子同等的教育,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捍衛自己的財產,簡而言之,分享他們的特權。而勞動婦女則被允許與她們的丈夫一起分擔勞動,與她們的男人一起分擔家務,與她們的男人平等地經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奴役。當然,我們會為實現男女法律平等的所有要求而鬥爭,同時我們堅持階級路線,並解釋說任何民主進步都只能是反資本主義鬥爭的跳板。
另一方面,婦女的鬥爭顯然也是階級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資本家不擇手段地分化工人階級,如果他們能讓一部分人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會對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造成壓力。如果他們能讓一部分工人看不起另一部分工人,這就會分裂反對資本家的共同鬥爭。工人階級的唯一力量在於跨越性別、種族、性取向等的團結。因此,反對壓迫婦女符合包括男性在內的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
婦女問題不僅被左翼提出,也被右翼蠱惑利用。例如,丹麥人民黨(Dansk Folkeparti)就利用婦女問題發表針對丹麥移民問題的種族主義言論,口頭上聲稱為婦女解放而戰,但實際上卻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種族主義和壓迫無產階級的行動。
例如,反對穆斯林家庭強迫婚姻被用來作為實施 24 歲移民規則(24 Year Rule)的論據,(譯按:該規則規定,非居民配偶只有年滿24才能與居住在丹麥的居民配偶團聚和同居;這對夫婦的聯系必須比他們與祖國的聯系更牢固,除非一方已經在丹麥居住超過28年;必須有10萬丹麥克朗的擔保,擔保金額每年隨通貨膨脹變化;一年內沒有領取過現金補貼或失業救濟金,不欠當局錢,並有福利金兩倍以上的收入供養伴侶;夫婦必須證明他們擁有或租有房屋,人均面積至少20平方米,每間房最多容納2人。)
這一民族主義的和反移民主義的規則實際上是在攻擊家庭團聚權(譯按:家庭團聚是一項普遍權利。當難民被迫逃離祖國時,他們的家庭有時會被拆散並長期分離。各國有責任通過家庭團聚程序保護和恢復難民的家庭生活。聯合國難民署幫助保障難民家庭團聚的基本權利;我們努力為失散的難民家庭提供支持,並增加他們利用家庭團聚程序的機會。),它對強迫婚姻的影響微乎其微,只是打著保護婦女的幌子而已。順帶一說,它也無法阻止強迫婚姻,婦女完全可以被強行送往另一個國家結婚,比如挪威和瑞典。(譯按:由24歲規則拒絕居留許可的案件中,通常只有不到1%的夫婦的婚姻涉嫌強迫或權宜婚姻。如2004年的2808例拒絕案件中只有7例與強迫婚姻有關。)
在這種情況下,婦女解放甚至一再被用來為帝國主義入侵阿富汗辯護。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是如何利用婦女問題來分化工人階級並引入各種反動觀念的。
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
不幸的是,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也悄然進入了工人運動的某些領域,盡管出發點是好的,但卻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丹麥左翼的許多人提出了在丹麥公司中增加女性管理人員的要求。但這意味著什麼呢?對於絕大多數不會成為老闆的女性來說,這完全沒有任何改變。至於她們應該從女老闆還是男老闆那裡領取越來越低的工資,或者是女老闆還是男老闆解雇她們,這都沒有任何區別,這都不會改變她們的處境。支持增加女性管理者的一個論點是,事實證明,有女性進入董事會,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就會是正數——這實際上意味著她們從男女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餘價值。女高管、女教授、女政治家的家務可以交給拿很低報酬的女保姆,而職業女性卻要承受長時間工作、日托服務開放時間縮短等巨大壓力。這些要求模糊了階級對立,縱觀歷史,資產階級一直試圖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營造一種「我們團結一致」、「我們正在努力解決問題」的感覺。
美國黑人中的佼佼者獲得了很好的職位,給人一種種族歧視已經不存在的錯覺,而實際上絕大部分黑人仍受到系統性壓迫。奧巴馬在美國大選中獲勝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希望,但這並不意味著絕大多數美國黑人的生活境況會發生改變。
正如希拉蕊·柯林頓擔任國務卿對大多數美國婦女來說沒有任何改變一樣。八十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和今天德國的安吉拉-默克爾的上台都不能說是向婦女解放邁進了一步——情況恰恰相反。
婦女問題也被用來支持勞工運動中的右翼。在社會民主黨主席選舉中,右翼候選人海勒·托寧·施密特(Helle Thorning Schmidt)擊敗弗蘭克·延森(Frank Jensen)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名女性。在 LO(丹麥工會聯合會)上一次總書記選舉中,左翼候選人哈拉爾德·伯斯汀以同樣原因(Harald Børsting)擊敗右翼候選人蒂內·奧爾維格-胡根伯格(Tine Auervig-Huggenberger),贏得了選舉。
處於工運高層的女性和男性一樣,都可能遠離普通群眾,背叛他們的利益和要求。決定一個人能否最好地領導婦女解放鬥爭的不是性別,而是這個人的政治立場。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也反對任何積極的性別歧視,例如按性別劃分的發言人名單,黨的領導機構、董事會中的特殊配額等。我們反對在董事會中為女性保留特別配額和席位。右翼往往利用這一點來提拔自己的人,反對真正的階級鬥士。政治問題而非性別問題必須決定工人運動領導層中的多數。我們還拒絕所有類似於在運動中對會議發言人名單進行性別隔離的提議。關鍵在於思想,而不是性別。
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除了這些完全無法使更多的婦女走上歷史舞台的倡議之外,還貶低了廣大勞動婦女,暗指後者不能表達「真正女性」的觀點,不能為理想而奮鬥,不能憑借想法和作秀贏得配額席位和優惠待遇。
我們反對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倡議,因為它們分裂了工人階級,使得男人反對女人,女人反對男人。我們在整個工人運動中為使婦女問題得到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的重視和討論而奮鬥。
早期工人運動中的婦女鬥爭
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婦女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那時起,婦女就參與了階級鬥爭。丹麥第一次有婦女參加的罷工發生在 1886 年,魯本斯蒸汽紡織廠的 225 名無組織婦女自發使工廠停轉。
如今,婦女占勞工組織成員的 49%,但婦女的組織並非一帆風順,問題依然存在。隨著女性勞動力在市場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她們的組織程度和參與階級鬥爭的程度也在增加。下面簡要介紹丹麥女工中的一些重要鬥爭,特別是汲取的經驗教訓。
許多女性主義者拒絕共同鬥爭,她們解釋說,工人運動中的男性過去和現在都是沙文主義者,婦女必須單獨組織起來,而這是自 1871 年丹麥社會民主黨和丹麥婦女協會成立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問題。毫無疑問,在工人運動中曾經存在偏見,而且現在仍然存在,但歷史表明,通過共同的鬥爭,這些偏見是可以打破的。
魯本斯蒸汽織布廠的罷工婦女加入了紡織工人工會,並得到了他們的罷工支持,但罷工最終還是失敗了。工會領導把這次失敗說成是「女性天性」的表現,認為這是由於婦女不懂得團結,不了解何時以及如何進行鬥爭。這是丹麥勞工運動中工會領導層第一次將失敗歸咎於罷工者本身,但絕對不是最後一次,「當婦女參與其中時,女性的天性總是難辭其咎。」這種情況和說法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女性牌匾漆工糾紛中再次發生,等下我們會討論這一問題。
在早期的工人運動中,許多工會不對婦女開放,盡管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婦女約占所有產業工人的 20%。此外,還有其他形式的女性有償就業,例如女佣。對於許多工薪家庭來說,婦女的收入非常重要,而對於單親母親家庭來說,婦女的收入更是至關重要。
盡管婦女通常更難組織起來,部分原因是許多婦女在家工作,因此完全與世隔絕,但婦女組織仍在穩步發展。19 世紀 90 年代末,丹麥約有 20% 的女性產業工人加入了工會,這一比例超過了大多數其他國家。
從 1888 年起,丹麥社會民主黨將「不分性別、種族或國籍的人類全面解放」納入其綱領,並要求男女享有相同的選舉權和同工同酬。這並不意味著勞工運動內部過去和現在仍然沒有偏見,也不意味著勞工運動在許多方面對婦女問題從未采取過反動的態度。但是,女性主義者對工人運動在婦女問題上的批判有選擇性地忽略了這一進步。
在工人運動中,婦女應該待在家裡的理念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 60 年代。男人被認為是養家糊口的人,因此工人運動的目標就是讓男人獲得足夠的薪水,這樣妻子就沒有必要工作了。盡管在現實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工薪階層婦女都無法承擔全職太太的代價而必須外出工作。
今天,我們很容易說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是一種進步,但在 19 世紀末以後,工人階級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上並沒有太多的奮鬥目標。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婦女可以從事醫生或律師等職業,而工人階級婦女只能希望從事 10-15 個小時的艱苦繁重工作。同時,也沒有公共托兒所,資產階級婦女可以通過雇佣保姆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對於工人階級婦女來說卻難有兩全法。
女性主義者還指責工人運動偏袒技術男工的利益,將婦女的利益置於一邊,並以禁止在家工作的討論為例進行了強調。在工人運動的早期,許多人都在家工作,例如裁縫。而對許多婦女來說,這是兼顧工作和家庭責任的唯一途徑。工會爭取禁止在家工作,因為這會分裂工人階級,而且在家工作的工人組織不力。女性主義者反對這項禁令,她們的回應是,這表明婦女必須置身於工會運動之外。馬克思主義對此的回答是,工人運動必須提出要求,為所有人提供適當、安全和負擔得起的兒童保育、生活工資和人道的工作時間。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解釋的那樣: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共產黨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它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共產黨宣言》)
我們看到他們是如何強調「整個無產階級」的,勞工運動是繞不過去的,婦女問題不能被視為與階級鬥爭問題相分離。工人運動的領袖們也並不只是在婦女問題上沒有進步路線,縱觀歷史,工人運動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裂。例如,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一直相互對立。
正如我們最近在2008年春季看到的那樣,在與工資談判有關的公務員罷工期間,公務員、護士、托兒所工作人員、老人護理人員等不同群體因不滿提出的工資協議而舉行了長達數周的罷工。一些沒有參加罷工的公務員工會的領導人在媒體上要求,罷工者的工資不得高於擬議的協議,以防他們的成員可能感到不滿。參加罷工的不同工會的領導人也相互爭鬥;例如,護士工會(DSR)的領導人就非常強調社會和醫療工作者的收入不應高於護士的要求。這次罷工是各行各業團結一致、要求為低收入婦女行業提高工資的一個公開案例。
然而,盡管工會領導人相互爭鬥,但罷工確實打破了一些偏見。隨著婦女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她們也成為了鬥爭的一部分。正是通過共同的鬥爭,跨性別或宗教等的團結才得以建立。
1875 年發生了這樣一場勞資糾紛,資本家想要將組織起來的婦女將接替罷工男子的工作。這改變了煙草工人工會的態度,他們意識到也必須把婦女組織起來。煙草工人的總書記在罷工後說:
「由於一種令人遺憾的錯誤觀念,迄今為止,女工和男工一直作為競爭對手相互敵視。但我們通過社會主義理論認識到,所有工人必須團結一致地抵御來自資本主義的攻擊。在這一理論中,我們還明確了女性與男性的平等,因此,從事同樣工作的女工必須獲得與男工相同的報酬。」(拉森一世:《丹麥勞動史》,2007 年,第 376 頁)
20世紀70年代牌匾女工的罷工
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所謂的「野貓」罷工(即官方認可的談判程序之外的罷工)越來越多。在許多罷工中,包括在工業罷工中,婦女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在 1954 年的菲利浦罷工中,大多數雇員都是婦女。
在整個1960年代和70年代初,女工們通過鬥爭提出了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不分性別同工同酬的要求。1970 年代,新的群體開始參與罷工行動,主要是公務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幼兒教師、護士等開始將罷工行動作為一種武器。
1970年代婦女中最著名、最重要的罷工之一可能是1972/73年皇家瓷器廠女牌匾漆工的罷工。這次罷工成為了整個工人階級的榜樣,引發了其他工人的大力聲援,同時也表明婦女當然能夠罷工。
大約150名在皇家瓷器廠繪制牌匾的女工抱怨工作條件惡化,計件工資下降。工廠管理層同意就新的工資協議進行談判,但兩周後又終止了新協議。牌匾女工拒絕按照舊協議工作,但會繼續按照新協議工作。她們要求工廠遵守提前兩個月通知終止當地協議的標准。在此背景下,工廠管理層以罷工為由將她們遣送回家。牌匾女工們每天都到工廠示威,要求按照新協議上班。
勞工法院受理了這一案件,法院同意了這些婦女的說法,即工廠非法廢除了當地協議。勞資爭議法庭判處工廠因非法終止當地協議而支付20000丹麥克朗的罰金,但同時卻因牌匾女工的非法罷工而判處她們72000丹麥克朗的罰金。
在罷工期間,牌匾女工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她們以前從未想過自己能夠改變什麼,她們向自己和其他工人階級表明,婦女可以罷工,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可以領導階級鬥爭。牌匾女工們每天都開會討論罷工問題,許多以前不敢在大型集會上發言的婦女也開始參與討論。牌匾女工們還組織參觀了其他可能的工作場所,並介紹了她們的罷工情況。各工作場所在道義上和經濟上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同情。總共募集到了 352,311 丹麥克朗,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而勞資爭議法庭的判決又引發了全國各地自發的募捐活動,總共又募集到了60,000丹麥克朗。
工會和勞工組織領導了勞資爭議法庭的談判,但沒有讓牌匾女工參與其中,而且普遍對這些婦女不屑一顧。當牌匾女工們詢問什麼是專業仲裁時,她們從工會代表那裡得到的答案是「一個有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的房間。[……]說再多你們也不會明白。」(勞工組織主席托馬斯·尼爾森(Thomas Nielsen)對媒體評論說,牌匾女工們被處以巨額罰款是她們自己的錯,她們是「愚蠢、固執和愚昧的」(《女漆工的奮鬥》,1974 年)。另一方面,來自工作場所的巨大支持表明,雖然工會領導層對牌匾女工不屑一顧,但工會的普通員工絕對不是這樣。
當女性主義者指責工會由男性主導時,她們忘記了領導層和基層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一般來說,工會領導層對基層成員的行為普遍都很傲慢,這不分性別,特別是針對邊緣群體。我們的任務是在基層員工中建立團結,反對工人階級的這種分裂,從而向領導層施加壓力,而不是幫助加劇分裂。
罷工本身與婦女問題無關,但罷工本身也向參與罷工的婦女提出了這方面的問題。牌匾上的一位女工解釋了這是如何產生的:
「我想我們一直都認為,盡管我們只是女人,但也不應該讓她們對我們說三道四——但直到去年,我們才真正意識到這一點。不是作為女性,而是作為人類。以前人們無法想像婦女可以坐下來參與罷工,但現在不再是這樣了。許多地方的人告訴我們,他們沒有想到一群婦女能夠堅持這麼久而不與自己為敵,這是男人對女人的老式看法。但事實是,罷工對許多女人來說,可能是一個比對類似的男性群體來說更大的問題。」(蒂格森/Thygesen, 《勞工鬥爭的經驗教訓》, 1974 年,第 66 頁)。
許多婦女認為,衝突發生在三條戰線上,即資本家、工會和家庭戰線。對於單身母親來說,卷入爭端顯然是很難的,但對於許多有伴侶的婦女來說,當她們的男人不理解罷工是為了什麼並抱怨被忽視時,她們也很難接受,罷工導致了幾位牌匾女工離婚。罷工往往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包括對相關人員的個人影響,離婚並不罕見。
正如幾位牌匾女工所描述的那樣,「她們醒悟了」,而這也改變了家庭的狀況。一些婦女隨後成為工會的積極分子。但是,單靠一次罷工並不能解決問題;在人們真正獲得自由之前,必須開展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普遍鬥爭。罷工結束後,一位牌匾女工的評論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現在我們回去工作了。很奇怪,我滿心歡喜,但同時也痛苦萬分。我又要開始計件工作了,我不應該思考,不應該說話或行動,我難以忍受這種折磨。我看著我的同事們,他們的日子也一樣難過嗎?我們不可能真的再次成為生產機器,沒有任何機會討論和思考我們所經歷的一切。」(蒂格森/Thygesen, 《勞工鬥爭的經驗教訓》, 1974)。
爭取同酬
在女工多年的壓力下,特別是在造船廠起重機女司機罷工期間,以及在工會婦女和紅襪子運動的聯合行動下,同工同酬於1973年被引入私營部門的集體協議中。丹麥女工工會(KAD)多年來一直堅持同工同酬的要求。1945年,她們在工資協議中采納了這一要求,整個1960年代,幾個工會都將同工同酬提上了議事日程。更廣泛地說,作為社會思潮激進化總體進程的一部分,社會更加關注婦女問題。年輕人,尤其是中產階級婦女開始提出婦女問題,並組成了不同的團體,這些團體被共同稱為「紅襪子運動」(Red-stockings)。「紅襪子運動」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紅襪子」的第一個著名活動是在 Strøget(哥本哈根的主要街道)焚燒胸罩,活動當天,她們來到圖博格啤酒廠散發傳單,呼吁同工同酬。
紅襪子活動引起了人們對這一要求的關注,但只有當工會中的職業婦女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提出這一要求時,這一要求才有可能得到落實。1971 年成立了一個同工同酬小組,參加該小組的有活躍的工會婦女,特別是來自KAD第 5 部(產業工人)、「紅襪子」以及可能來自其他團體的婦女。參與該小組的不是全國性的KAD,而是工會中的左翼。該團體組織了一次同工同酬示威游行,並在哥本哈根的大型工作場所散發了 13000 份傳單,幾個主要工作場所的婦女也參與了示威游行的組織工作。1971 年 2 月 8 日舉行的示威游行有數千人參加,圖博格公司的女工舉行了罷工。
示威游行和越來越多的非法罷工(如牌匾女工罷工)給工會領導層帶來了壓力,KAD的總書記在 1971 年的集體談判後威脅說,如果 1973 年不實行同工同酬,女工就會舉行大罷工。關於性別平等的討論開始在社會民主黨內蔓延,並於 1976 年通過了《同工同酬法》。同工同酬的鬥爭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動員了工人運動的所有成員,從而使領導層受到了壓力。
「紅襪子運動」引發了一些重要的辯論,許多「紅襪子」也在工人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紅襪子運動」繼續沿著女性主義的道路前進,建立了獨立的婦女組織,並將重點放在「純粹的」婦女問題上。工人運動和一些左翼人士被認為缺乏與婦女的團結,被指責帶有性別偏見。也許部分情況下確實還存在許多偏見,例如,丹麥總工會總書記托馬斯·拉森(Thomas Larsen)就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但歷史已經證明,在工人運動之外成立單獨的團體是沒有出路的。活動無論多麼轟轟烈烈,新聞報道如何鋪天蓋地,都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必須在工人運動內部、工會和工人政黨中開展鬥爭。
隨後我們看到,男女之間的薪酬差距絲毫沒有改變,同工同酬法案的通過實際上只是揭示了:女性受壓迫問題完全無法通過法律和協議來解決。
在2010年春季丹麥的下一輪集體談判中,同工同酬似乎可能再次成為一個問題,因為一些工會的領導層已經提出將其作為一項主要要求。這無疑是積極的一步,但目前工人階級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失業問題,而且失業率還在不斷上升,各地的資本家都在利用解雇的威脅對工資和工作條件施加壓力。同工同酬的要求很有可能被資本家用來要求凍結最低工資,甚至降低男性工人的收入。我們決不能接受這種做法!這將分裂工人階級。我們必須要求資本家立即糾正這種情況,執行 30 多年前在集體協議和法律中商定的同工同酬!
公務員參與日益壯大的罷工浪潮
如前所述,絕大多數公務員都是女性,在1970 年代日益高漲的罷工浪潮中,她們開始與其他工人階級平等地舉行罷工。丹麥的勞動力市場具有嚴重的隔離性,女性占市政部門工作人員的 75%,而男性約占私營部門雇員的 66% ,婦女的狀況與公務員的狀況密切相關。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公共開支被大幅削減,公務員的優厚就業條件被取消,私有化浪潮興起,公務員的工作條件普遍受到破壞。每名教育工作者或教師負責的兒童人數,或每名家庭護理負責的老人人數等都有所增加。
從2001年起,右翼政府繼續推行這一政策。但從千年之交開始,階級鬥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群眾抗議活動開始恢復力量。幾年來右翼政府主要通過地方議會進行削減福利,這導致了大規模的運動。2006年秋,許多城市的幼兒園教師和其他人員舉行了罷工。第二大城市奧胡斯Aarhus)的托兒所教師率先舉行了長達4周的野貓罷工。2007年夏天,一個全新的群體開始行動起來,社會和醫療保健工作者開始舉行罷工,以爭取更高的報酬。
自2006年春季起的18個月內,共舉行了三次反對削減福利的示威游行,參與人數超過10萬。這些男女勞動者缺乏的不是戰鬥精神或勇氣,而是缺乏領導。公職人員工會並不支持罷工,也不協調各市的罷工,因此罷工頻頻失敗,削減福利的行動仍在繼續。
2008年春,公職人員集體談判導致護士、幼兒教師以及社會和醫療保健工作者舉行了多周的罷工行動。他們的要求是「同工同酬」和「女工拿男人的工資」,但其含義並不明確。如前文所述,各工會領導人,無論是罷工的還是未罷工的,都再互相爭鬥內訌。一個生動的畫面是,同一天的同一時間,在市政廳廣場舉行了護士示威游行,在議會前廣場舉行了教育工作者示威游行。工會領導層再次決定身披「黃」甲,雖然DSR護士工會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但領導層明確表示:同工同酬更多地適用於護士,而不是社會和保健工作者。
就如同牌匾女工們,罷工意味著相關職業婦女的生活和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1973年,護士們第一次舉行罷工,當時她們就表示要打破將護士工作視為一種神聖使命和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精神的觀念,罷工者在2008年的罷工中重申了這一點,這被稱為「乖女孩」的終結。
這次罷工以失敗而告終,工資漲幅微乎其微,這不是因為罷工者,而是歸咎於罷工工會的領導層。工會領導層之所以沒有讓罷工者參與決策,是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將失去對罷工的控制,同樣,他們也沒有協調鬥爭,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影響力,因為他們沒有把這場鬥爭看作是一場聯合鬥爭,而只是一場從州和市預算中同樣有限的資金中獲得盡可能多的讓步的鬥爭。罷工本應擴大到其他群體,尤其是私營部門的工人,但這可能意味著罷工會完全脫離領導層的控制,出現類似於1985年丹麥大罷工的情況。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明白了,工會領導層的性別並不決定他們是否會在鬥爭中起帶頭作用。DSR 護士工會的領導層中90%是女性,她們在確保罷工勝利方面並沒有發揮比其他工會領導層更好的作用。其次,在罷工期間,公共部門工人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一大批工人階級婦女的人物也變得明朗起來。實際上,他們的雇主是政治家,但同時政治家又否認自己有任何責任,並提到了 「丹麥模式」:即在丹麥,工會鬥爭和政治問題應該是分開的。但事實上,這兩者是無法分開的,尤其是對公共部門的工人而言。為公職人員爭取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同工同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問題,無法僅靠工會來解決。
工會和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人民黨和團結名單)的工運領導層本應共同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以消除所有公務員的工資差異。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右翼政府的政策之外提出一個明確的替代方案。公務員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們確實沒有私營部門工人那樣的影響力來支持自己的要求。罷工的目的是打擊雇主的腰包,但當公職人員罷工時,政治家的腰包卻不會受到影響;相反,他們往往會影響到兒童、老人和病人。為了避免這個問題,例如護士在罷工時總是提供應急人員。這意味著,盡管在 2008 年的罷工期間所有護士都正式罷工,但在許多醫院科室,值班護士的人數比平日還多,因為應急人員比日常人員多,這也體現了工作條件的瘋狂和惡劣。
公務員不可能獨自贏得這場戰鬥,他們必須呼吁私營部門的工人並讓他們參與進來,因為私營部門在實現體面的福利服務方面也有很大的利益,公務員和私營部門工人之間的分裂應予以克服。以前,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協議是同時談判達成的,例如,幼兒園教師要求每周工作35小時,這在1985年的大罷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他們被分割開來,分別談判合同。我們必須呼吁消除組織內部以及薪酬和條件談判中的所有分歧。
爭取婦女解放!
婦女在歷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開始到法國大革命的一系列革命中也是如此。俄國革命是由俄國婦女在國際勞動婦女節要求面包與和平而發起的。今天,盡管許多參與近期罷工的人已經幻想破滅,而且當前的經濟衰退總體上導致罷工數量暫時下降,但這並不意味著表面之下什麼都沒有發生。在每一次鬥爭中,整個工人階級都會學習到寶貴的經驗,無論鬥爭是以勝利還是失敗告終。目前的僵局只是暫時的,表面之下正在得出明確的結論。其中一個結論是,現在必須在政治上進行鬥爭!公務員罷工的結果之一就是加入和投票支持社會主義人民黨的人數大幅增加。
工人階級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戰鬥,他們要求有一個堅定的領導層來領導這場符合他們利益的鬥爭。從根本上說,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開展一場改變社會的鬥爭。這樣才能為婦女的全面解放和消除一切壓迫奠定基礎,婦女的鬥爭是工人階級爭取解放鬥爭的一部分。
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創造一個能夠解放婦女和全人類的社會。縱觀歷史,女工們展現了她們的勇氣和戰鬥精神,在爭取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用恩格斯的話說,在那個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將從 「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