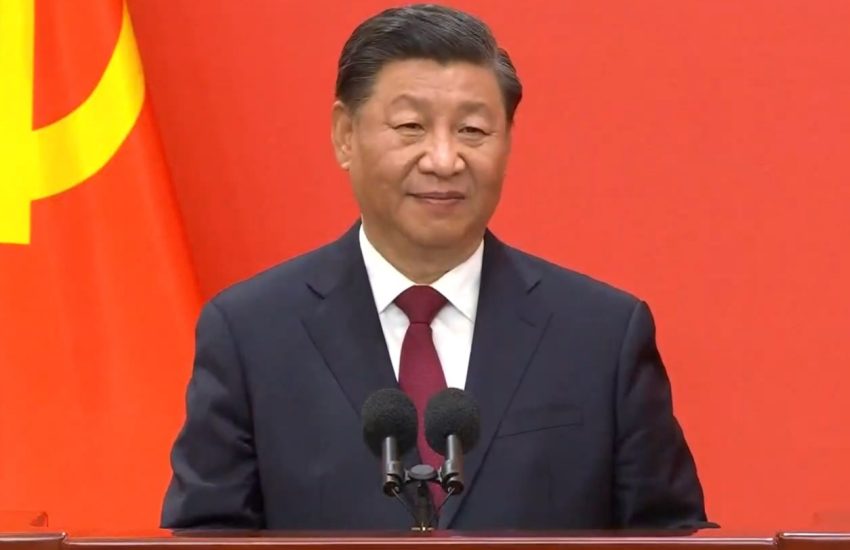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革命辯證法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是著名的多產的文學天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是現實主義風格的先驅,後來被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和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著名作家所效仿。在這篇文章中,Ben Curry探討了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方法、他的著作的主題以及位於其核心的迷人的矛盾。(譯者:梅洛)
「親愛的天使,你真是一相情願了;你以為路易-菲力浦能控制這些事情嗎?不,他在這方面也不是一相情願的呢。他跟我們一樣的知道:在大憲章之上還有那聖潔的、人人敬重的、結實的、可愛的、嫵媚的、美麗的、高貴的、年輕的、全新的、五法郎一枚的洋錢!」(譯注:出自小說《貝姨》(La Cousine Bette))[1]
從1789年的大革命到1848年的大革命,法國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蕩,這是法國資產階級飛速發展的時代。在革命開始時,這個階級是波旁王朝專制政權下受壓迫的 「第三等級 」的一部分;在革命結束時,它已然是無可爭議的統治階級,並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法國社會。
與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同時存在的,是它的歷史學家和最能描繪其動人精神的藝術家,是世界文學的巨匠之一,現實主義小說之父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盡管巴爾扎克不是一個革命者,他仍深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鐘愛。恩格斯這般評價他的文學作品「這裡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國歷史……多麼大膽無畏!(譯注:巴爾扎克在挑戰重要的和有爭議的社會問題和探索人性復雜性時非常勇敢,常常不顧可能帶來的後果和社會規範。)在他詩意的正義中蘊含著革命的辯證法!」[2]
在大量咖啡因的刺激作用下(據估計他一生中喝了50萬杯咖啡!),巴爾扎克一生都在不舍晝夜地工作。不幸的是,他在五十歲時就逝去了。然而在30年的工作中,巴爾扎克創作了不少於90部小說、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其中包括60部長篇小說和數十部傳世之作。
單獨來看,巴爾扎克的一部部小說確實很偉大,但只有將它們聯系在一起,才能充分欣賞它們的價值。他龐大的作品群,被統稱為《人間喜劇》,構成了一幅宏偉的法國社會畫卷,時間從拿破侖的垮台到1848年,地點從巴黎都會到外省鄉村,人物涵蓋了士兵、警察、間諜、政治家、貴族和農民、銀行家、藝術家、記者、官僚、罪犯和娼妓等等,所有這些角色都被精湛地描繪出來,直擊他們所處世界的核心。
與其說是對法國社會的描寫,不如說是對過去和現在的小氣、貪婪和野蠻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刻描寫。
現實主義文學
巴爾扎克出生於1799年,拿破侖在這一年發動了霧月政變,標志著法國大革命的結束,這場革命在法國受壓迫的群眾中激起的幻想破滅了。
一種剝削形式被換成了另一種。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3]
隨著資產階級的勝利,《共產黨宣言》的作者解釋了人類如何 「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4]」在《人間喜劇》的各卷中,巴爾扎克的藝術就像強效的嗅鹽,幫助這個世界從破碎的幻想中清醒過來,迫使它直面現實。
不同於當時在法國盛行的浪漫主義風格所追求的理想化的過去,我們在《人間喜劇》中看到的是充分地展示現在,包括其傷痛和缺點。巴爾扎克的方法完全是唯物主義的,在「現實主義」的旗幟下,它代表著文學和藝術的新起點。
在他關於巴爾扎克天才的論文中,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ewig)對其方法給出了生動的描述:
「這個他稱之為文學‘拉馬克主義’的概念,後來被丹納公式化了,即每一個多元體對一個統一體的作用力不亞於一個統一體對一種多元體的作用力;每個個體都是地理和氣候、成長的社會環境、風俗習慣、機遇以及命運賦予他的一切的產物;每個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吸收著周圍的氛圍,同時自身也輻射出氛圍並被其他人吸收;這種內外世界對性格形成的普遍影響成為巴爾扎克的公理。一切都相互交織;所有力量都是流動的,沒有一種是自由的—這就是他的觀點。」[5]
雖然巴爾扎克明確拒絕「唯物主義」的標簽,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明顯的唯物主義方法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極其辯證的方法。
巴爾扎克打算把《人間喜劇》作為居住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 「社會物種 」[6]的一個完整的、活生生的代表,而不是簡單的 「事實 」的干巴巴的積累。任何藝術都不可能希望記錄社會的每一個細節,也不需要這樣做。藝術的真正目的是超越偶然性,以掌握更深層、更本質的真理。巴爾扎克不需要描寫3000萬法國人和婦女來為法國畫像。只要抓住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就足夠了。在他的筆下,《人間喜劇》中的2000多個人物就足以完成這一任務。
在《人類喜劇》中,也許與現實主義作品相反,我們發現男人和女人被用以大膽誇張的色彩描繪,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使用明暗對比法來突出人類表情和動作中的戲劇性。巴爾扎克的人物常常被描繪成在他們的激情中異常獨特的形像。但正因為這個手法,他們才更加真實:他們變成了他們的階級和激情動機的原型。
紐沁根男爵(Baron de Nucingen)成為整個百萬富翁銀行家階級的典型;葛朗台(Eugenie Grandet)為吝嗇鬼扮演同樣的角色;高布賽克(Gobseck)為高利貸者;克雷維爾(Crevel)為資產階級新貴;馬爾內夫夫人(Madame Marneffe)為資產階級交際花;歐也納·德·拉斯蒂涅(Eugene de Rastignac)和呂西安·德·呂邦潑雷(Lucien de Rubempre)代表有抱負的鄉村人;伏脫冷(Vautrin)則代表整個巴黎犯罪階層。
正如化學家將自然界無數化合物分解為純淨的成分元素進行分析一樣,巴爾扎克試圖「將我們稱之為‘人民’的這種復合物分解為其組成部分的元素」[7]。正如他所說,巴爾扎克「將心比心」,「擁抱他人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他們的破衣爛衫穿在穿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我深入了解他們的靈魂,同時不忽視外在特征,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完全掌握了這些外在特征,以至於我立刻看到了超越它們的東西。」[8]
貴族階級
在政治方面,巴爾扎克與革命者相距甚遠。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在兩個永恆的真理—宗教和君主制—的照耀下寫作的;正如當代事件所顯示的那樣,這兩者是人類社會所必須的。每個有理智的作家都應該努力引導王國的回歸。」[9]
他的一生都在徒勞地尋求進入上流社會。從貴族中那些無聊而不被賞識的妻子中收到的讀者來信,都能使他陷入極度狂喜之中。他會做白日夢,幻想著一場婚姻能給他帶來貴族頭銜和財富—作為一個垂死的人,他只能獲得,卻永遠無法享受的東西。但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裡發現了地主貴族階級的注定失敗的真實的、不加修飾的形像。

在《人間喜劇》中最早的小說《1799年朱安黨人或布列塔尼地區》中,我們見到了朱安黨人的貴族領袖—布列塔尼的反動游擊隊崛起。在小說中,共和國軍隊是一支紀律嚴明的戰鬥部隊,由真誠地想像他們的第一執政官拿破侖保衛著他們因大革命而獲得的土地的農民們組成。另一方面,由布列塔尼農民組成的朱安游擊隊被描述為加入保皇黨的隊伍,只為了搶劫驛站和死去的共和國士兵的屍體—這種做法在秘密的森林彌撒中被教會莊嚴地奉為神聖。
至於朱安游擊隊的領袖,當他們貪婪地提出對貴族頭銜、地產和主教職權的要求,作為對他們繼續效忠國王的回報時,我們就可以一覽他們的所思所想。
在《幻滅》和《高老頭》中,我們發現舊的貴族:小氣、偏執、兩面派和自負,由於歐洲的反動軍隊,他們又一次重新回到了御座上。但是對路易十八來說,重建他的宮廷和貴族們和在巴黎重辦沙龍是一回事,而恢復舊的財產關系又是另一回事,因為舊制度曾經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法國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金錢構成了它現在所圍繞的新軸心。崛起的資產階級在各個領域對舊貴族施加壓力:在戲院、在政壇、在輿論界。衰落的貴族們可能不屑於讓新貴們進入他們的沙龍,但他們卻必須把自己的財富托付給證券交易所,他們向資產階級木材代理商出售從其莊園的森林中砍伐的木材,他們請求資產階級高利貸者資助他們的婚姻不忠行為。
在外省,貴族們發現自己的地位稍微穩固一些,巴爾扎克描述了這群毫無價值的烏合之眾:
「所有聚集在那裡的人都有最可憐的心理品質,最卑微的智慧,是方圓50英里內最可悲的人性標本。政治上的討論都是誇誇其談和歇斯底里的俗語:《法蘭西日報》(Quotidienne)被認為對君主制不冷不熱不忠;路易十八本人被套上雅各賓派的帽子。婦女們大多是愚蠢的,沒有風度,衣著簡陋;他們每一個人都被一些缺陷玷污了;一切都不如意,談話、服裝、思想和身體都是如此……舉止和階級意識、紳士風度、小貴族的傲慢、對禮儀規則的熟知,都是為了掩蓋他們內心的空虛。」[10]
這不是一個注定要滅亡的階級的鮮明寫照嗎?
巴爾扎克對其所鐘愛的天主教會的描繪也好不了多少。像所有舊秩序的最後堡壘一樣,它發現自己被來自四面八方的圍攻,甚至被迫成為資產階級本身:「在上帝的殿堂裡,它屈服於一種可恥的販賣座椅和租金的行為……盡管它不能忘記耶穌將錢商趕出聖殿時的憤怒。[11]」在出生、結婚和死亡時,我們發現教會的代表伸出手掌,在每個階段收取他們的費用。
資產階級的悲劇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由偉大的、貧窮的法國人民群眾在最崇高的激情感召下爭取而來的。但是,它們幾乎全部被資產階級的大手收割了。
這些非常真實的人物,勝利者和失敗者,被巴爾扎克高超的筆觸轉化為小說,成為《人間喜劇》的主角。
資產階級不是被描繪成社會類型的剪影,而是被描繪成真實的、活生生的人。我們在1799年見到了銀行家,他只在乎保護和增殖自己的財富,對保皇黨和共和黨都表示冷漠。我們見到了小資產階級的投機者,如合作社的葛朗台(Grandet),戴上了像征自由的紅帽,以便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發財。在塞萊斯坦·克雷維爾(Celestin Crevel)—一個為復辟貴族制作香水而致富的調香師身上,巴爾扎克為我們生動描繪了資產階級道德的虛偽形像。
在《人間喜劇》中,我們可以讀到關於資本主義下家庭生活的無數真實悲劇的虛構描述。我們發現父親詐騙和勒索兒子;男人為了嫁妝向女人求愛;通奸的丈夫為了養情婦而毀掉家庭;家財萬貫而「節儉」的守財奴父親只給女兒提供面包和冷水作為一日三餐;丈夫為了事業的發展協助妻子出軌;孩子被父母當作動產對待。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12]
罪犯和資本家
巴爾扎克的批判依次觸及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方面,這裡只能提到其中的幾個方面。

在《高老頭》中,重述了莎士比亞在資產階級時代的悲劇《李爾王》,故事的真正主人公,如果他能被稱為主人公的話,是歐也納·德·拉斯蒂涅,一個貧窮的外省貴族。剛到巴黎的他在兩種發財方式之間徘徊:一種是「誠實」的方式,即勾引高老頭的一個女兒,通過與銀行家紐沁根結婚而致富;另一種是通過肩膀被打上烙印的苦役犯伏脫冷提供的一條流血的捷徑。
這有什麼區別呢?在伏脫冷看來,他為拉斯蒂涅提供咨詢,幫助他度過良心的煎熬,使其認清道德和法律的虛偽:
「沒有一條(法律)不荒謬。戴了黃手套說漂亮話的人物,殺人不見血,永遠躲在背後。普通的殺人犯卻在黑夜裡用銑棍撬門進去,就犯了加重刑罰的條款了。」[13]
資本家和殺人犯一樣會殺人,雖然手上沒有沾一滴血。對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譴責之詞,出自一個被冠以罪名的惡棍之口卻不失其威力:
「難道你比我們強嗎?我們肩膀上背的醜名聲,遠遠比不上你們心裡的壞主意,你們這些爛社會裡的蛆!」[14]
最終,拉斯蒂涅不得不同意伏脫冷的觀點:
「他看到了社會的本相:法律跟道德對有錢的人全無效力,財產才是金科玉律。他想:‘伏脫冷說得不錯,有財便是德!’。」[15]
巴爾扎克的革命辯證法
貴族沒有能力領導社會;而資產階級同樣不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最接近自傳的作品《幻滅》中,巴爾扎克對米歇爾·克雷田(Michel Chrestien)這樣的革命共和主義者不吝贊美,他稱其為 「具有聖茹斯特(Saint-Just)和丹東(Danton)水平的政治思想家」,是 「曾經腳踩法蘭西土地的最高尚的生物之一」。
這些毫無保留的贊美之詞因巴爾扎克在整個《人間喜劇》中對各階層男女的行為進行評論時隨意辛辣的諷刺而顯得更加引人注目。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寫給瑪格麗特·哈克尼斯(Margaret Harkness)的信中所指出的:
「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贊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譯注:恩格斯這裡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工人起義,參加起義准備工作的有共和黨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團體,構築在聖瑪麗修道院的街壘是最後陷落的街壘之一。),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年)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16]
但巴爾扎克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發現,革命共和黨人所向往的「理性王國」是一種奇異的現像,只能以資產階級赤裸裸的腐朽統治告終。他的這一評估是正確的,並在1848年爆發的革命中得到了證明,同年,巴爾扎克放下了他的筆。
也是在這一年,巴黎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在自己的階級旗幟下,手握武器,奮起反抗。相反,資產階級對其革命任務感到恐懼而退縮,俯首聽任冒險家路易·波拿巴的擺布,並表現出巴爾扎克所揭露的所有頹廢、懦弱和輕浮。
當我們拋開巴爾扎克作品中包含的反動幻想,剩下的就是對資產階級社會及其虛偽道德的尖銳批判。他開創的現實主義方法激勵著其他偉大的作家,如查爾斯·狄更斯和埃米爾·左拉,承擔起描寫工業無產階級狀況的任務。它還對《共產黨宣言》的作者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共產黨宣言》的篇幅在1848年首次見諸報端,當時巴爾扎克的偉大文學生涯即將結束。
在《共產黨宣言》中—和《人間喜劇》一樣—我們看到了不可阻擋的歷史車輪在旋轉著。對於向後看的巴爾扎克來說,這種向前的運動摧毀了他理想中的舊社會,以及對國王、上帝和家庭的敬畏,是一件令人深感遺憾的事情。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他們向前看,看到巴爾扎克所描繪的這種破壞性力量同時也是一種巨大的創造性力量。這種向前的運動為一個新的、無階級的社會奠定了基礎,在這個社會中,資本主義帶來的所有惡習都將永遠消失。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注釋
[1] 巴爾扎克,《貝姨》,企鵝出版社,1965年,pg. 305
[2]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致勞拉·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6/042.htm
[3] 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4] 同上
[5] S Zweig,《三位大師》,George Allen and Unwin出版社,1930年,pg. 16
[6] 巴爾扎克,《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導言》,巴爾扎克書店,2012年7月14日
[7] S Zweig:《巴爾扎克》,維京出版社,1946年,pg. 29
[8] 同上
[9] 巴爾扎克,《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導言》,巴爾扎克書店,2012年7月14日
[10] 巴爾扎克,《幻滅》,企鵝出版社,1971年,pg. 46-47
[11] 巴爾扎克,《貝姨》,企鵝出版社,1965年,pg. 427
[12]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致勞拉·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6/042.htm
[13] 巴爾扎克,《高老頭》,牛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pg. 103
[14] 同上,pg. 184
[15] 同上,pg. 74
[16]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三十七卷,「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7/0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