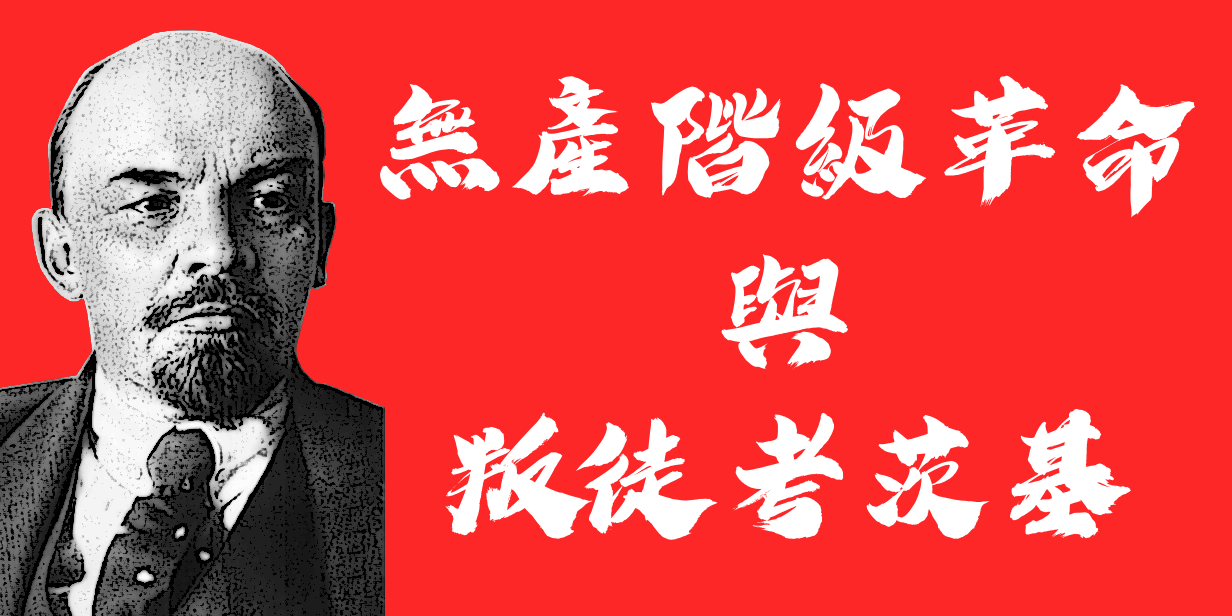《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蘇維埃憲法
我已經說過,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標誌。就是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時,也並沒有事先說過要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專政的這個組成部分並不是依照某個政黨的「計劃」出現的,而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產生的。歷史學家考茨基當然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不了解,當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在蘇維埃占統治地位的時候,資產階級自己就已經同蘇維埃分離,抵製它,同它對抗,對它施展種種陰謀。蘇維埃是在沒有任何憲法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從1917年春至1918年復)也還沒有任何憲法。資產階級痛恨被壓迫者的這種獨立的和萬能的(因為是包括所有人的)組織,肆無忌憚、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地反對蘇維埃,公開參加(從立憲民主黨人到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米留可夫到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叛亂,——這一切造成了資產階級被正式排除出蘇維埃的結果。
考茨基聽說過科爾尼洛夫叛亂,但是他竟大模大樣地不顧歷史事實,無視那決定專政形式的鬥爭進程、鬥爭形式。的確,既然講的是「純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實呢?因此,考茨基對取消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批評」是那樣地……天真,如果是一個小孩子,這種天真倒很可愛,但如果是一個尚未被公認為蠢才的人,這種天真就令人憎惡了。
「……如果資本家在普選制下落到了區區少數的地位,他們就會寧可順從自己的命運」(第33頁)
……這不是說得很可愛嗎?
聰明的考茨基在歷史上多次見過,並且根據對實際生活的觀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資本家是尊重大多數被壓迫者的意誌的。
聰明的考茨基堅持「反對派」的觀點,即議會內鬥爭的觀點。他真是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的:「反對派」(第34頁及其他許多頁)。
啊,好一個博學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您該知道,「反對派」是和平鬥爭而且只是議會鬥爭的概念,就是說,是適合非革命形勢的概念,是適合沒有革命的情況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內戰中的無情的敵人,——象考茨基那樣害怕內戰的小資產者無論發出怎樣的反動的悲嘆,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當資產階級進行種種罪惡活動時(凡爾賽派及其同俾斯麥勾結的例子,對於任何一個不是象果戈理小說中的彼特魯什卡119那樣對待歷史的人來說,是多少能說明一些問題的),當資產階級向外國求援並同它們一道進行反對革命的陰謀活動時,用「反對派」的觀點來看殘酷的內戰問題,這真是笑話。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當象「糊塗顧問」考茨基那樣,昏頭昏腦地把組織杜托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反革命暴動並且付給怠工者千百萬金錢的資產階級,看作合法的「反對派」。
啊,多麽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對問題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興趣,所以一讀到他對蘇維埃憲法發表的議論,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爾的一句話:法學家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考茨基說:
「實際上,單把資本家變為無權的人是不行的。從法律上看,什麽是資本家呢?有產者嗎?甚至在德國這樣一個經濟非常進步、無產階級人數極多的國家裏,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也會使大量的人成為沒有政治權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誌帝國的農業、工業、商業三大部門中的從業人員及其家屬,屬於職員和雇傭工人這一類的約有3500萬人,屬於獨立經營者這一類的有1700萬人。可見,黨在雇傭工人中間完全可以成為多數,但在全體居民中間則占少數。」(第33頁)
這是考茨基的典型議論之一。這難道不是資產者反革命的抱怨嗎?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國極大多數農民不雇傭工人,因而也沒有被剝奪權利,您為什麽把全體「獨立經營者」都算作沒有權利的人呢?這難道不是捏造嗎?
您這位博學的經濟學家為什麽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數字,1907年德國同一個統計材料裏關於農業中各類農戶使用雇傭勞動的數字呢?您為什麽不把德國統計材料的以上數字給那些讀您的小冊子的德國工人看,讓他們知道·剝·削·者有多少,知道剝削者在「農戶」
總數中只占少數呢?
這是因為您的叛徒立場使您變成了一個純粹是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
你們看,資本家原來是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於是考茨基在好幾頁上攻擊蘇維埃憲法的「專橫」。這位「鄭重的學者」容許英國資產階級用幾世紀的時間製定和周密製定新的(對中世紀來說是新的)資產階級憲法,而對於我們俄國工人和農民,這位奴才科學的代表卻不給任何期限。他要求我們在幾個月內就製定出極其周密的憲法……
……「專橫」!請想一想,這種責難暴露出他向資產階級獻媚已經卑鄙到了極點,他那種迂腐已經到了極其愚鈍的地步。資本主義國家那班十足資產階級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動的法學家,在幾百年或幾十年中周密地製定了極其詳盡的條規,寫了幾十本幾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釋來限制工人,束縛窮人的手腳,對人民中的每個普通勞動者百般刁難和阻撓,啊,資產階級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卻不認為這是「專橫」!這是「秩序」和「法治」!這裏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規定得完備,目的是要盡量把窮人的血汗「榨幹」。這裏有成千上萬的資產階級的律師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這些人,想必是因為馬克思非常重視打碎官吏機器吧……),他們能把法律解釋得使工人和普通農民永遠逃不出法網。這不是資產階級的「專橫」,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齷齪、榨取民脂民膏的剝削者的專政,絕對不是。這是一天比一天更純粹的「純粹民主」。
而當被剝削的勞動階級,在因帝國主義戰爭而同國外兄弟們隔絕開來的情況下,在歷史上第一次創立了自己的蘇維埃,號召受到資產階級壓迫、被他們弄得閉塞、愚鈍的群眾起來進行政治建設,並已親自開始建設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在熾熱鬥爭的烈火中、在內戰的烽火中開始擬定出沒有剝削者的國家的基本原則的時候,所有的資產階級惡棍,一幫吸血鬼,以及他們的應聲蟲考茨基,就大叫起「專橫」來了!的確,這些無知的工人和農民,這班「小百姓」,怎能解釋他們自己的法律呢?這些普通的勞動者,得不到有學識的律師們的忠告,得不到資產階級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練達的官吏的忠告,怎麽會有正義感呢?
考茨基先生從我1918年4月28日的講話①中引了一句話:
「……群眾自己決定選舉的程序和日期……」 於是「純粹民主派」
考茨基推論道:
「……可見,每個選民會議大概都可以隨意規定選舉程序。專橫和排除無產階級內部那些不好辦的反對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第37頁)
說這種話,同資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謂群眾在罷工時壓迫「願意做工的」勤勉工人這種叫喊有什麽區別呢?為什麽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下,由資產階級-官吏決定選舉程序,就不是專橫呢?為什麽起來同歷來的剝削者作鬥爭的群眾,在這場殊死鬥爭中受到教育和鍛煉的群眾,他們的正義感就一定趕不上一小撮受資產階級偏見熏陶的官吏、知識分子和律師呢?
考茨基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們可別懷疑這位最可敬的家長、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誠。他熱烈地堅定地擁護工人的勝利和無產階級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識分子市儈和昏頭昏腦的庸人在群眾運動展開以前,在群眾同剝削者作激烈鬥爭(絕對不要進行內戰)以前,先制定出一個溫和謹慎的革命發展章程……
我們這位極其博學的猶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20義憤填膺地對德國工人說,1918年6月14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代表們開除出蘇維埃。
義憤填膺的猶杜什卡·考茨基寫道:
「這個措施不是針對犯了某種罪行的某些個人…… 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根本沒有提到蘇維埃代表不受侵犯的問題。在這裏,被開除出蘇維埃的不是某些個人,而是某些政黨。」(第37頁)
是的,這的確可怕,這是不可容忍地背棄純粹民主,而我們這位革命的猶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這種民主的規則幹革命的。
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應該先保證薩文柯夫之流、李伯爾唐恩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積極派」)不受侵犯,然後再制定刑法,宣布參加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反革命戰爭或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同德帝國主義者勾結起來反對本國工人的人「應受懲治」,只有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才有權根據這個刑法並依照「純粹民主」把「某些個人」
開除出蘇維埃。不言而喻,通過薩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爾唐恩之流或依靠他們的鼓動從英法資本家手裏領取金錢的捷克斯洛伐克軍,以及在烏克蘭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維克幫助之下從德國人那裏得到槍械的克拉斯諾夫分子,在我們沒有製定出正確的刑法以前就會乖乖地坐在那裏,並且會象最純粹的民主派那樣僅限於從事「反對派」的活動……
蘇維埃憲法剝奪「以取得利潤為目的而使用雇傭工人」的人們的選舉權,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樣強烈的義憤。他寫道:「帶一個學徒的家庭手工業者或小業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但是他沒有選舉權。」(第36頁)
這是怎樣的背棄「純粹民主」啊!這是怎樣的不正義啊!固然,直到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並且用無數事實證明,小業主剝削雇傭工人是最不講良心和最貪得無厭的,但猶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當然不是小業主階級(究竟是誰臆造出有害的階級鬥爭理論?),而是某些個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的剝削者。人們認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筆下復活了。這位節儉的阿格尼斯是幾十年以前「純粹」民主派資產者歐根·李希特爾虛構出來傳播於德國文壇的。他預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沒收剝削者的資本將引起無法形容的不幸,他擺出一副天真的面孔問道,從法律上看,什麽是資本家呢?他以被兇惡的「無產階級專政者」剝奪得分文不剩的可憐的節儉的女裁縫(「節儉的阿格尼斯」)為例。有一個時期,整個德國社會民主黨都把純粹民主派歐根·李希特爾的這個「節儉的阿格尼斯」引為笑談。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倍倍爾還活著,他曾坦白直爽地說,我們黨內有很多民族自由主義者124;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考茨基還沒有成為叛徒。
現在,「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帶一個學徒的、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的小業主」身上復活了。兇惡的布爾什維克欺侮他,剝奪他的選舉權。固然,在蘇維埃共和國中,「任何一個選舉大會」,象同一個考茨基所說的那樣,可以允許同該工廠有關系的貧苦工匠參加,只要他(作為例外)不是剝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但是難道能夠指望普通工人舉行的既無秩序又無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廠大會會有實際生活知識和正義感嗎?與其去冒險,使工人有可能欺侮「節儉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的工匠」,不如把選舉權給一切剝削者,給一切雇用工人的人,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讓那些受資產階級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歡迎①的實行背叛的小人去痛罵我們的蘇維埃憲法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吧。這樣很好,因為這會加速和加深歐洲革命工人同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韓德遜和拉姆賽·麥克唐納之流的分裂,同社會主義的老領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壓迫階級的群眾,他們的覺悟的忠誠的領袖革命無產者,一定會贊成我們。只要讓這些無產者和這些群眾了解了我們的蘇維埃憲法,他們立刻會說:這才真正是·我·們·的·人,這才真正是工人政黨,真正是工人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像上述一切領袖們欺騙我們那樣用改良的空話欺騙工人,而是認真同剝削者進行鬥爭,認真實行革命,真正為工人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既然蘇維埃在一年的「實踐」之後剝奪了剝削者的選舉權,那就是說,蘇維埃真正是被壓迫群眾的組織,而不是賣身給資產階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的組織。既然蘇維埃剝奪了剝削者的選舉權,那就是說,蘇維埃不是小資產階級同資本家妥協的機關,不是進行議會空談(如考茨基、龍格和麥克唐納之流的空談)的機關,而是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同剝削者作你死我活鬥爭的機關。
一位消息靈通的同誌幾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從柏林寫信告訴我:「這裏幾乎沒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冊子。」我倒想建議我國駐德國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書收購來,贈給覺悟的工人,讓他們來聲討這個早已成了「發臭的死屍」的「歐洲的」(應讀作:帝國主義的和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
考茨基先生在書末(第61頁和第63頁)傷心地說:「新理論〈他這樣稱呼布爾什維主義,不敢提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這樣的老民主國也找到了擁護者。」「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接受這個理論」,在考茨基看來,這是「不可理解的」。
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戰爭的嚴重教訓使得革命群眾愈來愈討厭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寫道,「我們」向來是主張民主的,現在我們忽然又要拋棄它!
「我們」,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向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且科爾布之流早已公開這樣說過。考茨基知道這一點,但他妄想向讀者掩蓋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爾布之流的「懷抱中」這一明顯事實。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純粹」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看作神聖的東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漢諾夫還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直到他可悲地轉到俄國謝德曼的立場上去以前)。當時他在通過黨綱的黨代表大會上說,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要時將剝奪資本家的選舉權,將解散任何議會,如果這個議會成了反革命的議會。
只有這種觀點才是唯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是任何人即使從我上面引用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中都看得出來的。這顯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來的。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向人民發表過各國考茨基主義者喜歡發表的那種言論,他們向資產階級獻媚,迎合資產階級議會製,諱言現代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只要求擴大這種民主,把這種民主貫徹到底。
「我們」對資產階級說過:你們這些剝削者和偽君子高談民主,同時卻在各種場合百般阻礙被壓迫群眾參與政治。我們抓住·你·們·的話,為了這些群眾的利益,要求擴大你們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以便把群眾訓練好去進行打倒你們這些剝削者的革命。如果你們剝削者企圖反抗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就會無情地鎮壓你們,把你們變成沒有權利的人,不僅如此,還不給你們糧食吃,因為在我們無產階級共和國中,剝削者將沒有權利,將沒有飯吃,因為我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謝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會主義者。
這就是「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說過的和還要說的話,這就是被壓迫群眾一定會擁護我們、同我們在一起,而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會滾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