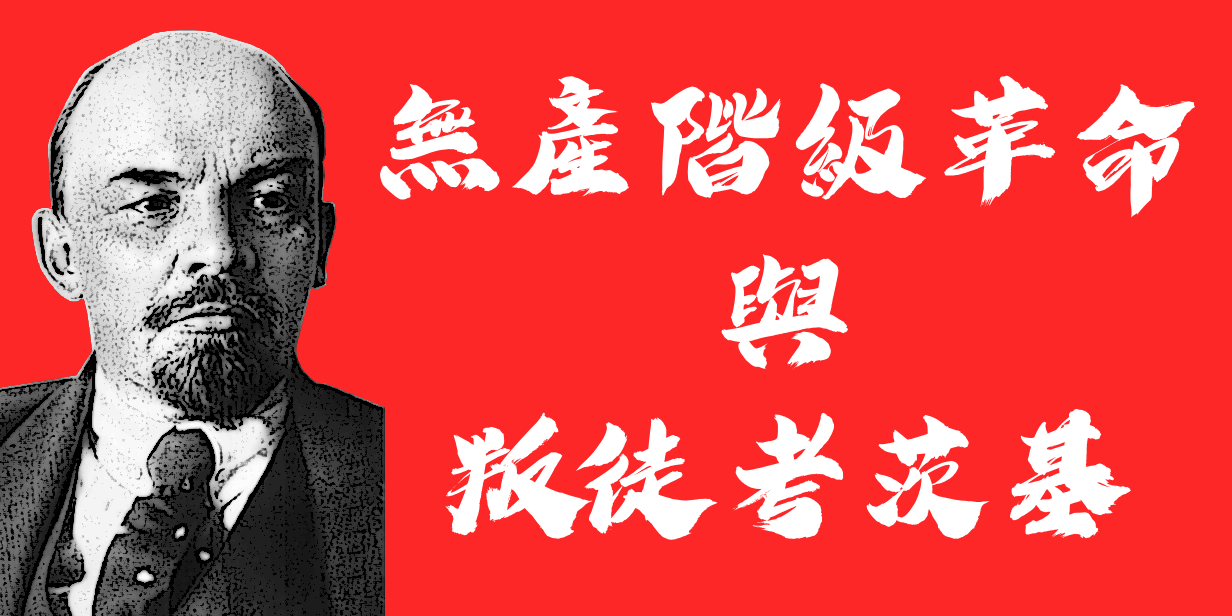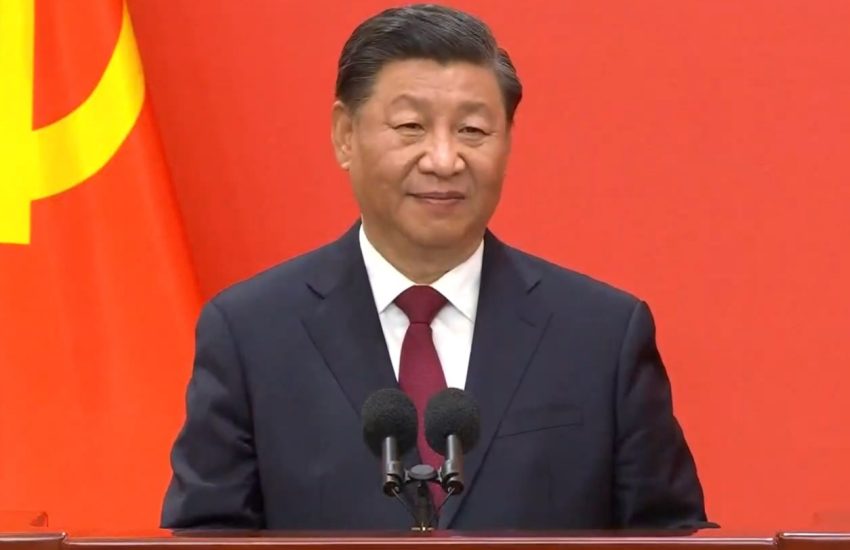《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
被考茨基攪得混亂不堪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僅是既不瞭解階級鬥爭也不瞭解國家實質的無知之談,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演變成習慣,消亡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是「純粹的」 民主)。
「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 歷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無產階級民主。
考茨基幾乎用了幾十頁的篇幅來「證明」資產階級民主比中世紀制度進步、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須利用資產階級民主這樣的真理。 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空談。 不僅在文明的德國,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國,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 考茨基一本正經地談論魏特林,談論巴拉圭的耶穌會教徒,談論許許多多別的東西,這不過是用那套「博學」。的「謊話來矇騙工人,以便迴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
考茨基把馬克思主義中能為自由主義者,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民主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拿來,而把馬克思主義中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無產階級為消滅資產階級而對它採用的革命暴力)拋掉、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抹殺和隱瞞起來。
正因為這樣,不管考茨基的主觀信念怎樣,他的客觀地位必然使他成為資產階級的奴才。
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 正是這個真理,這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不理解的。 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去對那些使一切資產階級民主變為對富人的民主的條件進行科學的批判,反而奉獻出一些使資產階級「稱心快意」的東西。
我們首先要向極其博學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們的書呆子(為了迎合資產階級)可恥地「忘記了的」理論見解,然後再來作一個最通俗的說明。
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而且「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1)。
「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爾的信)(2)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的導言)(3)
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尺規。 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1)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覆解釋這個論點當中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對我們用黑體標出的、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後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卻閉口不談! )。
「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代表和鎮壓(ver-undzertreten)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了同一目的服務於任何一個工廠主一樣。 」(馬克思論述巴黎公社的《法蘭西內戰》)(2)
極其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這些論點,每一條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徑。 在考茨基的整本摺頁冊中,絲毫看不出他理解了這些真理。 他的摺頁冊的全部內容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嘲弄!
只要看看現代國家的根本法,看看這些國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會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處處都可以看到任何一個正直的覺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 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在憲法上總是留下許多後路或保留條件,以保證資產階級「在有人破壞秩序時」,實際上就是在被剝削階級「破壞」自己的奴隸地位和試圖不像奴隸那樣俯首聽命時,有可能調動軍隊來鎮壓工人,實行戒嚴等等。 考茨基無恥地粉飾資產階級民主,閉口不談美國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資產者對付罷工工人的種種行為。
啊,聰明博學的考茨基對於這一點是閉口不談的! 他,這位博學的政治家不知道,對這一點默不作聲就是卑鄙。 他寧願向工人講一些民主就是「保護少數」之類的童話。 這很難令人相信,然而這是事實! 在西元1918年,在世界帝國主義大廝殺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國「的國際主義者(即不像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不像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韓德遜和維伯之流那樣卑鄙地背叛社會主義的人們)少數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頌起「保護少數」。來了。 誰要是願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這本摺頁冊第15頁。 而在第16頁上,這位博學的……人物還把18世紀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102的故事講給你聽呢!
多麼淵博啊! 向資產階級獻媚是多麽細緻入微啊! 在資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們的皮靴的樣子是多麽文質彬彬啊! 假如我是克虜伯或謝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諾得爾,我一定會用百萬酬金酬謝考茨基先生,賞給他猶大之吻103,在工人面前稱讚他,勸人們同考茨基這樣「可敬的」人物保持「社會主義的統一」。 著書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講述18世紀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故事,硬說民主就是「保護少數」,絕口不談「民主」共和國美國迫害國際主義者的大暴行,難道這不是奴顏婢膝地為資產階級效勞嗎?
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國的統治黨僅僅對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才保護少數,而對無產階級,則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問題上,不僅不「保護少數「,反而實行戒嚴或製造大暴行。 民主愈發達,在發生危及資產階級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時,大暴行或內戰也就愈容易發生。 資產階級民主的這個「規律」,原是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104中,在民主共和國美國對黑人和國際主義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國的愛爾蘭和北愛爾蘭事件105中,在1917年4月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 我故意不僅舉出戰時的例子,而且舉出戰前和平時期的例子。 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寧願閉眼不看20世紀的這些事實,卻向工人講述18世紀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十分新鮮、極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資產階級議會來說吧。 能不能設想博學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說過,民主愈發達,交易所和銀行家對資產階級議會的操縱就愈厲害呢? 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應該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布爾什維克利用議會,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更有成效,因為在1912—1914年,我們把第四屆杜馬的整個工人選民團都爭取過來了)。 但是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會像考茨基那樣忘記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有歷史局限性的,是有歷史條件的。 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到這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產者成為雇傭奴隸的千百種事實上的限制和詭計。
正是這個矛盾使群眾認清了資本主義的腐朽、虛假和偽善。 為了使群眾作好進行革命的準備,社會主義的鼓動家和宣傳家向群眾不斷揭露的正是這個矛盾! 然而當革命的紀元已經開始的時候,考茨基卻轉過身子把背朝著革命,讚美起垂死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妙處來了。
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 像考茨基那樣寫出一整本論民主的書,用兩頁談專政,用幾十頁談「 純粹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那就是用自由主義觀點來完全歪曲事實。
拿對外政策來說。 在任何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 到處都是欺騙群眾,而在民主的法國、瑞士、美國和英國,這種欺騙比其他國家更廣泛百倍,巧妙百倍。 蘇維埃政權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對外政策的黑幕。 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對這一點默不作聲,雖然在進行掠奪戰爭和簽訂「瓜分勢力範圍」。
(即資本家強盜瓜分世界)的秘密條約時代,這一點具有根本的意義,因為和平問題,千百萬人的生死問題都是以此為轉移的。
拿國家機構來說。 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連選舉是「間接的」(在蘇維埃憲法中)也提到了,但問題的本質他卻沒有看到。 國家機構、國家機器的階級實質,他卻沒有注意到。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資本家千方百計地(「純粹的」民主愈發達,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眾,使他們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等等。 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嚴格說來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已開始這樣做過)吸引群眾即被剝削群眾參加管理的政權。 勞動群眾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議會任何時候也解決不了極其重大的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著,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覺到,看到和覺察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構,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者的工具,是敵對階級即剝削者少數的機構。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自己的直接的組織,它便於這些群眾自己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建設國家和管理國家。 這裏,恰恰是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具有一種優越條件,就是大企業把他們極好地聯合起來了,他們最容易進行選舉和監督當選人。 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便於團結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的周圍。 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還有財富特權、資產階級的教育和聯系等等特權(資產階級民主愈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多種多樣)——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 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裡奪過來了。 最好的建築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 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築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裡奪過來,就使群眾的集會權利更加「民主「•百·萬·倍,而沒有集會權利,民主就是騙局。 非地方性的蘇維埃的間接選舉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易於舉行,使整個機構開支小些,靈活些,在生活沸騰、要求特別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地方代表的時期,使工農更便於參加。 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 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只有自覺的資產階級奴僕,或是政治上已經死亡、鑽在資產階級的故紙堆裡而看不見實際生活、浸透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觀上變成資產階級奴才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只有不能站在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上提出如下問題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裡,哪一個國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農或者農村半無產者(即佔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群眾的一分子),能夠多少像在蘇維埃俄國那樣,享有在最好的建築物裡開會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紙庫來發表自己意見、 維護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選正是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建設國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個國家從一千個瞭解情況的工人和雇農當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表示懷疑,那是可笑的。 全世界的工人只要從資產階級報紙上看到承認真實情況的片斷報道,就本能地同情蘇維埃共和國,正因為他們看到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對窮人的民主,不是對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都是對富人的民主。管理我們(和「建設」我們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 這是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在內)被壓迫階級中的千百萬人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知道、每天感覺到和覺察到的淺顯明白、無可爭辯的真理。
在俄國,則完全地徹底地打碎了官吏機構,趕走了所有的舊法官,解散了資產階級議會,建立了正是使工農更容易參加的代表機關,用·工·農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農蘇維埃監督官吏,由·工·農蘇維埃選舉法官。 單是這件事實,就足以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考茨基不理解每個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這一真理,因為他「忘記了「提出、」已經不會「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是·對·哪·一·個·階·級的民主? 他從「純粹的」(即非階級的? 或超階級的? )民主的觀點去推論。 他正像夏洛克那樣來論證,只要「一磅肉」,別的什麽都不要。 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我們不得不向博學的考茨基,向「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考茨基提出一個問題: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能平等嗎?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領袖的著作時竟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議。 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談起了考茨基,就必須向這位博學的人說明,為什麽剝削者不可能同被剝削者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