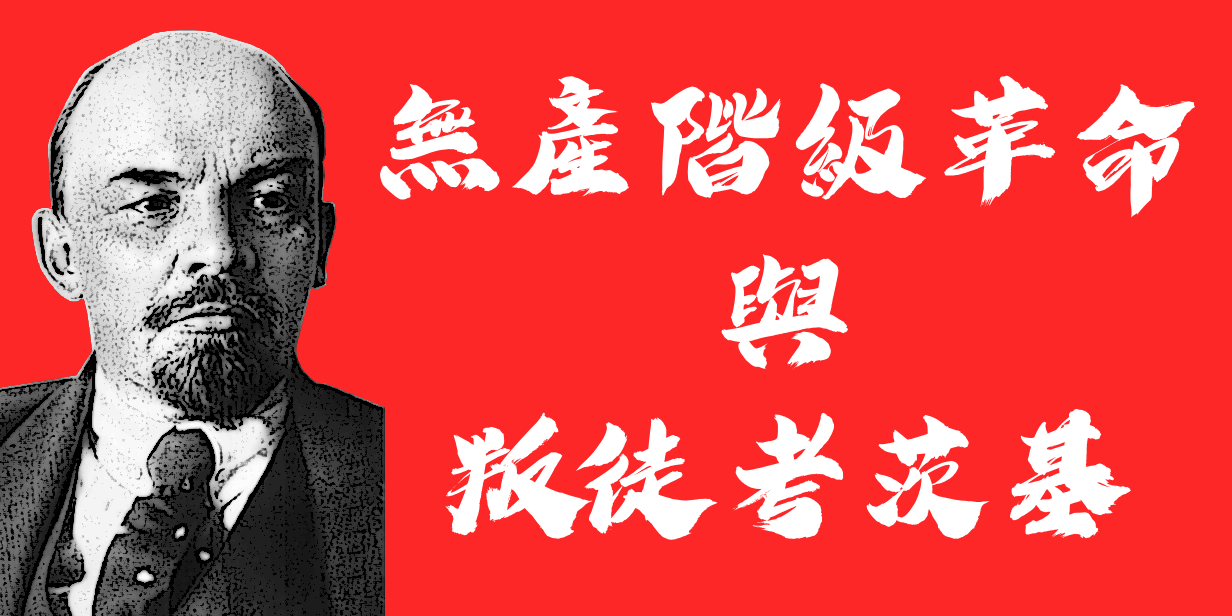《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蘇維埃不得變成國家組織
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形式。一個著書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果真正研究過這個現象(而不是重復小資產階級對專政的哀怨,象考茨基重彈孟什維克的老調那樣),就會先給專政下個一般定義,然後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蘇維埃,把蘇維埃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評論。
既然考茨基對馬克思的專政學說作了一番自由主義的「加工」,當然不能期望他會提出什麽重要見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樣研究蘇維埃是什麽這個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倒是十分有意義的。
他在回想1905年蘇維埃的產生時寫道:蘇維埃創造了「無產階級的所有組織形式中最能包羅一切的(umfassendste)組織形式,因為它包括了全體雇傭工人」(第31頁)。1905年蘇維埃還只是地方團體,而在1917年卻成了全俄國的聯合組織。
考茨基繼續說:「蘇維埃組織現在已經有了偉大的光榮的歷史。它的未來歷史還會更加偉大,而且不限於俄國一國。到處可以看到,面對金融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的雄厚勢力,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versagen;德語這個詞的意思比「不夠」稍強,比「無力」稍弱〉。這些舊方法不能放棄,它們在平常時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時會產生一些任務,用這些方法不能解決,而只有把工人階級的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實力手段集中起來,才能奏效。」(第32頁)
接著他談到群眾罷工,談到「工會官僚」同工會一樣是必要的,但「不適於領導那些日益成為時代標誌的強大的群眾戰鬥……」
考茨基得出結論說:
「……這樣看來,蘇維埃組織是當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它在我們正去迎接的資本同勞動的大決戰中將起決定的作用。
但是,我們能不能向蘇維埃要求更多的東西呢?1917年11月〈指公歷,按俄歷為10月〉革命後,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道在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解散後,竟把向來是一個階級的戰鬥組織的蘇維埃變成了國家組織。他們消滅了俄國人民在3月〈指公歷,按俄歷為2月〉革命中爭取到的民主。與此相適應,布爾什維克不再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把自己稱為共產黨人了。」(第33頁,黑體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過俄國孟什維克著作的人,立刻就會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樣盲目照抄馬爾托夫、阿克雪裏羅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論。的確是「盲目」照抄,因為考茨基為了迎合孟什維克的偏見,竟把事實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顧到向他的情報員,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爾摩的阿克雪裏羅得打聽一下,布爾什維克改名為共產黨人和蘇維埃具有國家組織的作用的問題是在什麽時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這樣簡單的查問,他就不會寫出這段令人發笑的話來,因為這兩個問題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4月提出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綱」就提出過,就是說,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說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來的考茨基的這段議論,就是整個蘇維埃問題的關鍵。關鍵就在於:蘇維埃是應該力求成為國家組織(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同年同月在布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上又聲明他們不以資產階級議會製共和國為滿足,他們需要的是巴黎公社類型的或蘇維埃類型的工農共和國),還是不應該力求這樣做,不應該奪取政權,不應該成為國家組織,而應該照舊是一個「階級」的「戰鬥組織」(馬爾托夫就是這樣說的,他是用天真的願望來粉飾這樣一個事實:在孟什維克領導下蘇維埃是使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復馬爾托夫的話,抓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理論爭論中的片斷,毫無批判、毫無意義地將這些片斷搬到一般理論問題、一般歐洲問題上去。結果弄得一團糟,使俄國每個覺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議論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們向歐洲所有的工人說明事實真相,考茨基也一定會遭到他們(極少數頑固不化的社會帝國主義者除外)同樣的嘲笑。
考茨基像熊那樣給馬爾托夫幫忙,十分明顯地把馬爾托夫的錯誤弄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請看考茨基究竟說了些什麽。
蘇維埃包括全體雇傭工人。面對金融資本,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蘇維埃不僅在俄國將起偉大的作用,在歐洲資本同勞動的大決戰中也將起決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這樣說的。
好極了。「資本同勞動的決戰」是不是要解決這兩個階級中哪一個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問題呢?
完全不是。絕對不是。
在「決」戰中,包括全體雇傭工人的蘇維埃不應該成為國家組織!
國家是什麽呢?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
總之,一個被壓迫階級,現代社會中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應該努力去進行「資本同勞動的決戰」,但不應該觸動資本用來鎮壓勞動的機器!不應該摧毀這個機器!不應該用自己的包羅一切的組織來鎮壓剝削者!
好極了,妙極了,考茨基先生!「我們」承認階級鬥爭,——就象一切自由派那樣承認它,就是說不要推翻資產階級……
正是在這裏,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徹底決裂已經很明顯了。這實際上是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資產階級什麽都能允許,就是不能允許受它壓迫的階級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在這裏,考茨基已經完全無法挽救他那調和一切、用空話避開各種深刻矛盾的立場了。
考茨基要麽是根本反對國家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中,要麽是容許工人階級把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拿到手中,但決不容許他們摧毀、打碎這個機器,並代之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論怎樣「解釋」和「說明」考茨基的論斷,在兩種情況下,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決裂並轉到資產階級方面,都是十分明顯的事實。
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勝利了的工人階級需要什麽樣的國家時就說過:「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①。現在,一個自以為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出來說,已經全部組織起來並同資本進行「決戰」的無產階級,不應該把自己的階級組織變成國家組織。恩格斯在1891年所說的「在德國已經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的「對國家的迷信」①,就是考茨基在這裏所暴露出來的東西。我們的這位庸人「同意」說:工人們,鬥爭吧(對這點資產者也「同意」,因為工人反正都在鬥爭,需要考慮的只是怎樣把他們利劍的鋒芒磨去),——鬥爭吧,但是不得勝利!不要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要用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去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誰真正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承認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誰多少琢磨過這個真理,他就決不會說出這種荒謬絕倫的話來,說什麽能夠戰勝金融資本的無產階級組織不應當變成國家組織。正是在這一點上現出了小資產者的原形,小資產者正是認為國家「終究」是一種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東西。究竟為什麽可以允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去同那不僅統治著無產階級而且統治著全體人民、全體小資產階級、全體農民的資本進行決戰,卻不允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把自己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呢?
因為小資產者害怕階級鬥爭,不能把它進行到底,直到實現最主要的東西。
考茨基說得亂了套,結果露出了馬腳。你們看,他親口承認,歐洲正去迎接資本同勞動的決戰,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而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資產階級民主。
由此可見?……
考茨基不敢進一步去想由此應該得出什麽結論。
……由此可見,只有反動派,只有工人階級的敵人,只有資產階級的走狗,才會在現時把臉朝著已經過去的時代,去描繪資產階級民主的妙處,侈談純粹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製度比起來,曾經是進步的,當時是應該利用的。但是現在,對工人階級來說,它已經不夠了。現在不應該向後看,而應該向前看,應該用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如果說,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範圍內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即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大軍,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麽,到了應該進行「決戰」的時候,還把無產階級限製在這種範圍內,那就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別可笑的窘境,因為他重復馬爾托夫的論據,卻沒有覺察到馬爾托夫的這個論據是以考茨基所沒有的另一個論據為依據的!馬爾托夫說(而考茨基則跟著他重復說),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把蘇維埃從鬥爭機關變為國家組織,為時尚早(應讀作:在孟什維克領袖們幫助下,把蘇維埃變成使工人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機關,倒是適時的)。而考茨基卻不能直截了當地說歐洲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考茨基在1909年還沒有成為叛徒的時候寫道:現在不能害怕革命為時過早,誰因害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當地否認這一點。結果得出了一個把小資產者的極度愚蠢和極度怯懦暴露無遺的謬論:一方面,歐洲已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正在走向資本同勞動的決戰;而另一方面,卻不能把戰鬥組織(即在鬥爭中形成、發展和鞏固起來的組織),即把被壓迫者的先鋒隊、組織者和領袖無產階級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
蘇維埃作為戰鬥組織是必要的,但不應該變成國家組織,——這一思想在政治實踐方面比在理論方面還要荒謬得多。甚至在沒有革命形勢的和平時期,工人反對資本家的群眾鬥爭,如群眾罷工,也要引起雙方極大的憤恨,激起不尋常的鬥爭熱情,也會使資產階級經常搬出他們的老一套,說什麽我還是「一家之主」,而且還要當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騰起來的革命時期,像蘇維埃這種包括一切工業部門的全體工人以至全體士兵、全體勞動的貧苦的農村居民的組織,隨著鬥爭的發展,由於簡單的攻守「邏輯」,必然要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想采取中間立場,「調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恥的破產。在俄國,馬爾托夫和其他孟什維克的說教已經遭到破產,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如果蘇維埃稍微廣泛地發展起來,能夠聯合並鞏固起來,這樣的說教也必然會遭到同樣的破產。對蘇維埃說,鬥爭吧,但不要親自掌握全部國家政權,不要變成國家組織,這就是宣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和「社會和平」。要是以為在劇烈的鬥爭中,這種立場除了可恥的破產外還會有什麽別的結果,那就很可笑了。腳踏兩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運。在理論上,他假裝在任何問題上都不同意機會主義者,其實在實踐上,他在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同革命有關的問題)上都是同意機會主義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