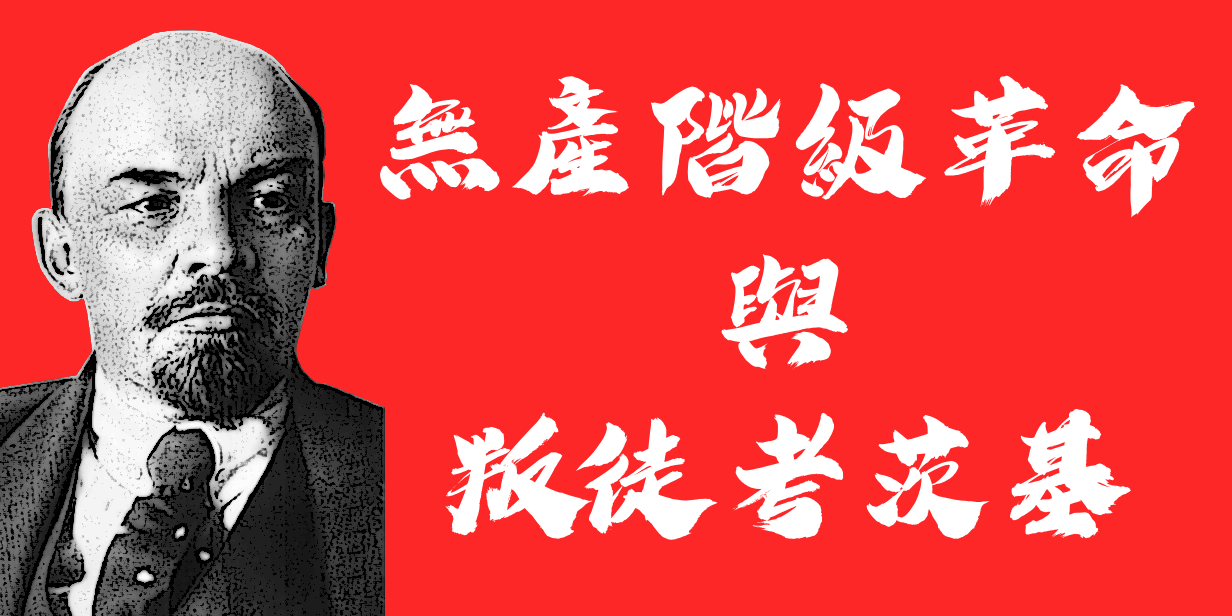《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能平等嗎?
考茨基是這樣推論的:
(1)「剝削者總是只占人口的極少數。」(考茨基的小冊子第14頁)
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從這一真理出發,應該怎樣推論呢?可以按馬克思主義觀點,按社會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關係為基礎。也可以按自由主義觀點,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多數和少數的關係為基礎。
如果按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得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這裏說的是民主,即國家的一種形式)變成本階級即剝削者統治被剝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剝削者還統治著被剝削者多數,民主國家就必然是對剝削者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國家應該根本不同於這種國家,它應該是對被剝削者的民主,對剝削者的鎮壓,而鎮壓一個階級,就是對這個階級不講平等,把它排除於「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得說:多數決定,少數服從。
不服從者受處罰。再沒有別的了。至於國家,包括「純粹民主」在內,具有怎樣的階級性,就根本用不著講了;這同問題沒有關系,因為多數就是多數,少數就是少數。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這樣推論的:
(2)「根據什麽理由無產階級的統治要采取而且必須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頁)接著他就說明無產階級擁有多數,而且說得極其詳細,極其羅嗦,既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又舉出了巴黎公社選票的數字。結論是:「一個這樣牢固地紮根在群眾中的製度是沒有絲毫理由去損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來壓製民主的情況下,這個製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來回答。但是,一個知道自己受到群眾擁護的制度使用暴力,僅僅是為了保護民主,而不是為了消滅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礎,要去掉道義上的強大權威的深刻泉源——普選制,那它就簡直是自殺了。」(第22頁)
你們看,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關系在考茨基的論據中消失了。
剩下來的只是一般多數,一般少數,一般民主,我們已熟悉的「純粹民主」。
請註意,這些話還是談到巴黎公社時說的呢!為了清楚起見,我們現在就來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看看他們談到巴黎公社時關於專政是怎樣說的:
馬克思說:「……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工人……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①恩格斯說:(在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①恩格斯又說:「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麽,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考茨基同馬克思、恩格斯之間,正如自由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者之間一樣,實有天淵之別。純粹民主和考茨基籠統地說的「民主」不過是「自由的人民國家」的另一說法,純粹是無稽之談。考茨基帶著飽學的書呆子的博學神情或者說帶著十歲女孩的天真態度問道:既然擁有多數,還要專政幹什麽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說:
——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為了使反動派恐懼,——為了維持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
這些解釋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看不見它的資產階級性,「始終如一地」主張多數既然是多數,就用不著「粉碎」少數的「反抗」,用不著對少數「實行暴力鎮壓」,只要對破壞民主的情況實行鎮壓就夠了。考茨基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無意中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常犯的那個小小的錯誤: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當作事實上的平等!小事一樁!
剝削者不可能同被剝削者平等。這個真理不管考茨基多麽不喜歡,卻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內容。
另一個真理是:在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一切可能性沒有完全消滅以前,決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義成功或軍隊嘩變時,可以一下子打倒剝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極罕見極特殊的場合,剝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在一個稍微大些的國家中,決不能一下子剝奪所有的地主和資本家。其次,只有作為法律行為或政治行為的剝奪,遠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需要的是在事實上鏟除地主和資本家,在事實上用另一種由工人對工廠和田莊的管理來代替他們。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不可能有平等,因為剝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條件,又有各種技能,而被剝削者大眾甚至在最先進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也是閉塞、無知、愚昧、膽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必然在許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貨幣(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有種種聯系,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訣」(習慣、方法、手段和竅門);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級技術人員(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接近;有無比高超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剝削者只在一國內被打倒(這當然是典型的情況,因為幾國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們依然比被剝削者強大,因為剝削者的國際聯系是很廣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剝削者,即最不開展的中農和手工業者等等群眾,是跟著並且會跟著剝削者走的,這已為過去的一切革命所證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為凡爾賽軍隊中也有無產者,這一點被極其博學的考茨基「忘記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為在比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簡簡單單地用多數和少數的關系來解決問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義者的最愚蠢的偏見,就是欺騙群眾,就是對群眾隱瞞明顯的歷史真理。這個歷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內對被剝削者還保持著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的剝削者,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反抗。剝削者沒有在最後的、拼命的戰鬥中,在多次戰鬥中試驗自己的優勢以前,決不會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的決定。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鬥,為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鬥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著那麽甜蜜的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只好從事「平凡的」勞動……)。而跟著剝削者資本家走的,還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著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難而害怕起來,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張皇失措,他們心慌意亂,東奔西跑,叫苦連天,從這個營壘跑到那個營壘……就象我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樣。
在這種情況下,在進行拼命的激烈戰爭的時代,當歷史把千百年來的特權的存亡問題提上日程的時候,竟談論什麽多數和少數,什麽純粹民主,什麽專政沒有必要,什麽剝削者同被剝削者平等!!
要愚蠢到什麽地步、庸俗到什麽地步才會說出這種話來啊!
但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幾十年(1871—1914年)已使遷就機會主義的各國社會黨象奧吉亞斯的牛圈那樣堆滿了庸俗、近視和叛變的穢物……
讀者大概已經註意到,考茨基在我們上面從他書中引來的一段話內,說到什麽侵犯普選制(附帶指出,考茨基把普選製稱為道義上的強大權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並且也是論述專政問題的時候,卻說的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對「權威」的看法比較一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必須指出,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問題,是純粹俄國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虛偽,把他的小冊子叫作《反對布爾什維克》,那麽,小冊子的書名就符合它的內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權直截了當地談論選舉權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論家」的姿態出現。他把自己的小冊子一般地叫作《無產階級專政》。他只是在小冊子的後一部分,從第6節起,才專門談到蘇維埃和俄國。前一部分(我引證的話就在這一部分)談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專·政。考茨基一談到選舉權,便原形畢露,表明他是一個根本不顧理論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論戰家。因為理論,即關於民主和專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個民族特殊的)階級基礎的論斷,應該談的不是選舉權這樣的專門問題,而是一般問題:在推翻剝削者、用被剝削者的國家代替剝削者的國家的歷史時期,能不能保留對富人的民主,保留對剝削者的民主呢?
理論家就是這樣而且只能是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巴黎公社以及談到巴黎公社時的一切論斷。我根據這種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寫的《國家與革命》那本小冊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專政的問題。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限製選舉權的問題。現在應該說,限製選舉權的問題是專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問題,而不是專政的一般問題。應該是在研究俄國革命的特殊條件和革命發展的特殊道路的時候才談到限製選舉權的問題。我在以後的闡述中是會這樣做的。事先就擔保將來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定都會限製或大都會限製資產階級的選舉權,那是錯誤的。這種做法也許是可能的。在大戰之後,在有了俄國革命經驗之後,可能會這樣做,但這不是實現專政所必需的,不是專政這一邏輯概念的必要標誌,不是專政這一歷史概念和階級概念的必要條件。
專政的必要標誌和必需條件,就是用暴力鎮壓剝削者階級,因而也就是破壞對這個階級的「純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論上就是這樣而且只能是這樣提出問題。考茨基沒有這樣提出問題,也就證明他不是作為理論家而是作為向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來反對布爾什維克。
究竟在哪些國家裏,由於某個資本主義的哪些民族特點,對剝削者的民主要實行(徹底實行或基本上實行)某種限製和破壞,這是關於某個資本主義和某個革命的民族特點問題。這不是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在於:不破壞對剝削者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談這個在理論上唯一重要的本質問題。考茨基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種論述,就是沒有引用我在上面引過的同這個問題有關的論述。
考茨基什麽都談了,能為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們思想範圍的一切都談了,就是沒有談主要的東西,沒有談到:無產階級不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不用暴力鎮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獲得勝利,而凡是實行「暴力鎮壓」的地方,沒有「自由」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民主。
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俄國革命的經驗,談談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同立憲會議之間的分歧——導致解散立憲會議和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