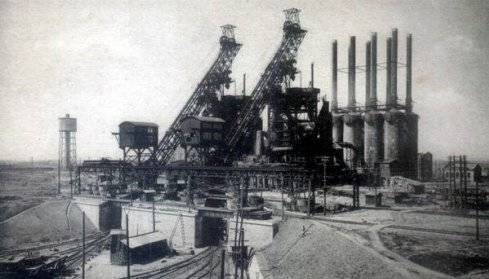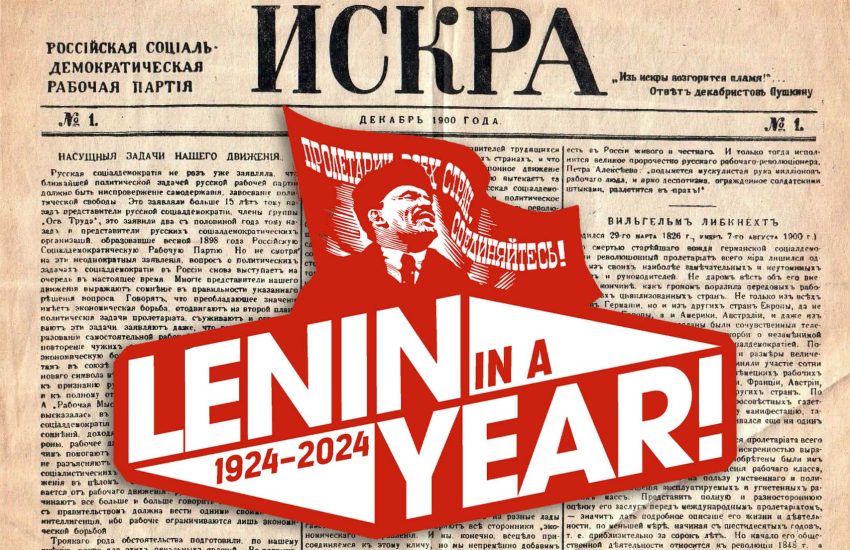歐洲現在是民主的還是波拿巴主義的?答弗朗克
(按:本文是當時作為第四國際英國支部「革命共產黨」之首席理論家的泰德·格蘭特對當時第四國際法國支部要員皮耶·弗朗克(Pierre Frank)先前撰寫的《歐洲現在是民主的還是波拿巴主義的?》(作於1945年11月)的回覆。原文寫於1946年。譯者:顧崇文,楊進 )
列寧說過,我們生活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托洛茨基則補充道:「以及反革命的時代」。三十年來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這個事實。歷史上罕有如此混亂而又如此一成不變的時期;流水的,是各民族間與各階級間那激烈、混亂的鬥爭,和萬花筒般走馬燈式的政權,而鐵打不變的,是金融資本對人民的支配。因此,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教導的繼承者,若是要獨立地社會事件作理論分析,就一定要密切注意這些身邊的變化,以此發展先鋒隊、指導人民群眾。
旨在批判史達林主義的貧瘠概念(即所謂屆時「第三時期」的所有政權都是法西斯主義),托洛茨基巧妙地將這個時代的精髓描述為變化的與浮動的,難以用普遍原則來解釋。先鋒隊必須具體地審視每個革命階段,以此理解、詮釋現實,並得出符合實際的、可以付諸行動的結論。他寫道:
「在急劇社會衝突、政治快速動移、情勢突變的時期,一個正確的理論取向的巨大實際重要性最為顯著。在這樣的時期,既有的政治觀念和概括迅速耗盡用途,並需要被完全取代(這比較容易),或者需要具體化、精確化或部分修正(這較為困難)。在這樣的時期裡,各種過渡、中間的情況和組合不可避免地出現,並擾亂了我們先前習慣的判斷思維,因此對於理論問題上的注意就需要更加持續。簡言之,在和平和「有機」的(也就是戰前)時期,我們仍然可以受益於幾個現成的抽像概念,但在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每一次新事件都強烈地驗證了辯證法的最重要規律:真理始終是具體的。」(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1934年7月)
在第四國際的行列之中,有些同志對這個教訓還是認識不足。他們仍然「吃以前理論的老本」,而不會根據現實修正以前的理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皮耶·弗朗克的這篇文章。
弗朗克試圖讓西歐的所有政權等同為「波拿巴主義」。他的理論還要更加極端:他主張法國自1934年就有了法西斯政府。在歐洲的無產階級奪得權力之前,唯有法西斯主義的和波拿巴主義的政府能夠存在。他自滿地將理論簡化為無形的抽像概念,掩蓋著不可避免的時常性的錯誤。第四國際不會容忍這種自滿。
弗朗克同志不加區分地把資產階級民主與波拿巴主義混為一談,而沒有解釋兩者的具體特征。他將「波拿巴主義」,「波拿巴主義的元素」互相套用,而且將民主自由與「一個可以定義為民主的政權」對立起來。但是,讀者卻無法找到弗朗克提出的,與現實中資產階級民主不同的理想化「民主政權」。他否認今日的歐洲擁有民主,因為「根本沒有(民主)的立足之地」。
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
我們會在這裡重複一些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概念,以達到理解歐洲政權的更替過程和變化(至少是西歐)所需要的清晰。史達林官僚主義主宰的東歐,則在不同的方向與條件下發展。
一個政權的政治性質(波拿巴、法西斯、民主)基本上是由國家內的階級關系決定的,而階級關系在不同階段是不同的。其本質是由其生產方式、財產關系和階級性質決定的。所以希特勒和羅斯福,艾德禮和墨索里尼,弗朗哥和古安,裴隆和薩拉查,德·瓦萊拉和蔣介石的政權[1],都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因為它們依賴於資本家剝削的經濟體系。然而,這些政權的階級性質並不是全部問題。我們需要將資產階級保證其支配地位和統治的工具歸類——因為它們會在不同情況下變化。這一規則的性質不僅取決於金融資本家的主觀願望和需要(這只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因素),而且恰恰取決於特定階段各階級之間的主客觀相互關系,而這種關系是由特定國家的歷史和階級鬥爭的發展所預測的。
主張社會的上層建築是其經濟發展的直接產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是最低劣的一種庸俗唯物主義。
帝國主義「民主」所基於的經濟基礎的消失,並不直接帶來資產階級民主的消失。它僅僅為其未來的坍塌做了鋪墊。這世紀初資本主義朝向帝國主義的發展已經使資產階級民主過時。但我們看到,資產民主階級仍然在其經濟基礎消失後維持自己。
資本主義超越其歷史功能在第一次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已經得到了證明。但這沒有、也不能以其自身的力量,自行導向資本主義的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全球的規模給推翻資產階級帶來了有利的條件。但無產階級自己創造的組織卻阻止了他們完成使命。社會民主黨背叛了革命,並且防止了資本主義體制的毀滅。在一戰後的革命年代,資產階級被迫依賴於社會民主黨的支持——他們維持統治的最後一件工具。在資產階級依賴這樣基於社會民主黨的政權、用改革和半改革來聯合壓抑革命工人時,這只能被視作資產民主。所以,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8年將當時德國由社會民主黨組織的資產階級政府視為反革命政權。
民主的自由是在與資產階級的長達一世紀的鬥爭獲得的,這是一個拼音般的常識;投票權在一個資本主義上升,資產民主的萌芽時期鬥爭中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得。就算是在其全盛期,也從來沒有一個不使用警察干涉和殘暴力量的平靜的民主國家。
然而,即使在資本主義仍處於經濟上升期的這個階段,也不僅有民主政權,也有波拿巴政權的存在。在典型的波拿巴主義國家,路易·波拿巴和拿破崙·波拿巴[2]本人都是在名副其實的繁榮時期上台的,其中一個繁榮時期持續了二十年。按照弗朗克同志的構想,波拿巴主義在這種環境下是沒有基礎的,只有資產階級民主才能存在。但我們看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英國革命共產黨[3]向來把西歐各國的政權(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定位為反革命的民主政權。皮耶·弗朗克同志則聲稱「民主反革命」的概念是「內容空洞」的。因此,他將很難解釋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組織起來的魏瑪德國到底是什麼[4]。於是他便必須如此主張:1918年德國發生的事情不是一場「被民主形式的反革命」背叛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成為一場推翻德國皇帝、建立「純正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民主革命了!而新政權是由軍法管制,且以社會民主黨領袖與德國防衛軍總參部、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密謀造反所建立的這一事實,完全證明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結論,即1911年的德國革命是一場「民主」的反革命,其中資產階級利用了社會民主黨作為其統治的代理人。
托洛茨基已經預見到了將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崩潰時相似的情況。他在1930年一封致義大利同志們的信中寫道:
「接下來就是義大利『過渡』時期的問題。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到底是什麼到什麼的過渡。資產階級(或『人民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是一回事,而法西斯主義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是第一種情況,那麼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就是首先出現的,然後才考慮無產階級在其中的位置。唯有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才能發生。如果是第二種情況,那麼問題就以一系列鬥爭、中斷、挫折、急轉的形式表現出來,代表了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不同階段。這些階段可以很多,但是它們無論如何不能涵蓋資產階級革命或是其神秘的混合體:所謂的『人民革命』。
那難道義大利就不能在一段時間內變成一個議會制國家或是『民主共和國』嗎?我想(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這個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不過它將不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果實,而是源自於早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流產。萬一無產階級先鋒隊無法在大規模的鬥爭和嚴重的革命危機中奪取權力,資產階級就會在『民主』的基礎上重構其權力。
比方說,能否說現在的德意志共和國代表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全面勝利?這樣說是荒謬的。1918-19年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為沒有領導而被欺騙、背叛、消滅了。但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仍然必須適應無產階級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並以『民主的』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存在。同樣的可能性——或是類似的可能性——在義大利被排除了嗎?不,它沒有被排除。法西斯主義的加冕是1920年不完全的無產階級革命所導致的。只有新的無產階級革命能夠扭轉法西斯主義。如果它這次仍然不能成功(共產黨的軟弱,社會民主黨人的背叛,共濟會,天主教徒),那麼反革命資產階級所建立的『過渡性』國家,必定會在它法西斯主義前身的廢墟上重新以議會民主制國家的形式確立。」(《義大利革命的問題》,1930年5月14日)
義大利的事態發展證明了托洛茨基的遠見卓識。資產階級被迫同意廢除君主制,而史達林主義者和義大利社會黨的叛徒們則以「議會民主制國家」所允許的方式來推進無產階級革命。這樣做當然無法獲得穩固的革命基礎,反而會使革命陷於危機與動蕩。弗朗克現在還能拒絕托洛茨基理論的正確性,堅持後墨索里尼時代的義大利仍然是法西斯政權嗎?
弗朗克在他的論述中引述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是無法理喻的,因為它恰恰舉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老托問道:法西斯主義之後是什麼?答曰資產階級為了避免群眾起來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這個關系中,我們注意到:在據稱民主沒有經濟基礎因而產生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可能,是托洛茨基根本未曾考慮過的。
以上,可以看出真正「內容空洞」的僵化理論,是反革命只能以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的形式出現,也就是指軍警獨裁。
歷史的經驗和現在歐洲的形勢無可辯駁地展示了,資產階級對抗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根據現實情況變化多樣,而不是事先決定的。資產階級根據階級間的力量對比運用不同的手段,依賴不同的社會階層從而加強或重建其統治。
至於資產階級是否能操縱社會民主黨人,波拿巴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機構,或是如時有發生的那樣,同時運用所有的力量,不僅僅取決於統治階級的主觀意願,或者隨便哪個冒進者的行為,而是取決於客觀條件及國內的階級關系——即任何特定時段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機械地重複金融資本與資產階級民主在現代社會中不兼容這一結論(毋庸置疑,這個結論在某些情況下是正確的),從而推斷出所有(資產階級)政權必定是波拿巴主義政權,是以主觀的、證據不足的歷史經驗推導出的抽像範疇,或是一種對歷史進程狹隘、不完全的理解,替代唯物主義辯證法分析。
要理解今日西歐各政權的性質,我們必須了解它們進化的背景。一戰後的群眾革命運動被社會民主黨人麻痹、背叛了。他們(社會民主黨人)獨自在揮舞著資產階級民主的旗幟下將拯救了資本主義,避免了它的毀滅。資產階級為了生存,被迫依賴於它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構。
無產階級未能奪權只會造成資本主義更深層的敗壞和腐朽。小資產階級在面對無產階級群眾組織時的墮落使他們變成了法西斯主義反動的工具。經由許多過渡階段,一個個國家中被困在自己體系中動彈不得的資產階級投向了公開的獨裁。
革命的浪潮之後就是反革命的浪潮。在義大利,德國,和其他國家,資產階級運用了狂熱小資產階級的力量來摧毀無產階級組織。之後,他們便被迫背叛小資產階級,轉變為波拿巴主義政權,即以軍警組織而非群眾支持維持統治的政權。
這樣做不能解決國內或國際上資產階級體系的矛盾。但是,資產階級狂熱地試圖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圖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根本地影響到資本主義體系的存續。資產階級驚恐地意識到,戰爭將會從群眾的深處釋放出無比的革命能量,重新創造對於推翻整個大陸的資本主義有利的條件。
納粹分子的勝利和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陷落產生了一個副作用,那就是短暫地摧毀了歐洲反動的群眾基礎。資本主義體系與反動直接寄生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刺刀之上。那些招人恨的賣國賊不過是納粹的走狗。當紅軍節節勝利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業已崩潰時,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就成了全歐洲緊要的問題。反動沒有群眾基礎,而且沒有一個強大穩定的軍警機關。同盟國的軍隊無法成為反動和公開軍事獨裁的反動基礎。在多數歐洲國家中,資產階級面臨著群眾起義,而他們無法以自己的力量平息。
希臘是個例外。在一場內戰與血腥的介入後,一個半波拿巴主義或者波拿巴主義的政權才被建立起來。它正在一步步地嘗試在希臘建立一個極權政體。帝國主義者清楚在歐陸範圍上運用此種方式的危險性。另外,希臘的反動性質必須以全力維持,以避免這個英國帝國主義的最後前哨落入史達林主義官僚手中。但即便如此,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也無法被完全摧毀。
沒有什麼能夠阻止資本主義的衰亡在西歐的衰亡,除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背叛。當資產階級為了反革命的目的依仗其社會民主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傾向時,反革命的「內容」是什麼?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威權主義?當然不是!它的內容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當然,資產階級無法在民主反革命的基礎上穩定自身。當資產階級的走狗們的行為引爆革命時,階級力量不會是停滯的。一段時間後(因國內和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式可以很長),資產階級也會轉向波拿巴主義的或是法西斯主義的反革命形式。
這就是義大利在一戰後兩年的革命浪潮中的發展形勢,在德國用了15年。階級關系的變遷反映在政權的轉變中:從民主政權、前波拿巴主義,到法西斯主義、純正的波拿巴主義軍事獨裁。
盡管資產階級民主的經濟與政治基礎每況愈下,工人再一次的奪權失敗也導致了在史達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之操縱下於義大利、法國和其他國家產生的資產階級政府。主張反革命或資產階級現在的統治只能以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弗朗哥式的政府,就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現代社會各種進程的理解。算上這段歷史中眾多的因素,包括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弱勢,可以提前預測出(的確如此)西歐的形勢會如何發展。但是這個進程只有通過民主、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才能被理解,而不僅是它們的外在形式。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同政權
拿破崙一世的經典波拿巴主義源於資本主義的青年和活力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波拿巴主義,亦即刀劍對社會的統治,代表了一種國家政府獲得相對獨立於各階級的狀態,來在各敵對階級之間作平衡、作仲裁。盡管如此,國家仍然是大資本家的工具。通過依靠農民的支持,拿破崙能夠維持一整個歷史階段的統治,得益於法國生產力的發展。
所以,當小拿破崙在1851年的政變中確立了權力,馬克思就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描述了以下的立場:
「國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態,無恥的是刀劍執政、而私法盛行。(作者注:根本不像解放後的法國戴高樂政權!)181851年12月的coup de tete〔輕率行為〕報復了1848年2月的coup de main〔勇敢打擊〕。」
這就是波拿巴主義的本質:赤裸的軍警專政,舉著劍的「仲裁者」。這種政權表明,社會內部的敵對關系已經變得如此之嚴重,以至於「調節」和「命令」這些對抗的國家機器,雖然同時仍然是財產所有者的工具,但是從所有階級中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一個「全國法官」,在他的手中集中權力,獨自「仲裁」國內的矛盾,用一個階級制衡另一個階級,同時卻仍保持為有產者的工具。同時,我們也將如下的情況定位為波拿巴主義:當一個政權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方的基本階級力量保持大致的互相平衡,而使得國家力量得以操縱、平衡相互鬥爭的各陣營,而又再一次給了國家權力相較於社會的某種獨立。
然而,波拿巴主義在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和衰退階段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提供托洛茨基《德國,唯一的道路》中的兩句把這個差異解釋得很清楚的引文:
「在此時,我們把布呂寧政府[6]當作波拿巴主義(『波拿巴主義的縮影』),這就是一個軍警專政的政權。自兩個社會階層間——有產者與無產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到達了最高的張力起,官僚、警察、軍隊主導社會的條件就發生了。政府變成『獨立於社會』。讓我們再度回顧:如果兩把叉子對稱地插入軟木塞,它就可以在大頭針上立穩。這就是波拿巴主義明確的主題。當然,政府還是繼續充當資產者的幫手。但幫手如今騎在老板背上,狠狠磨擦他的脖子,有時更毫不猶豫地一腳踩在老板臉上。
或許可以假定,布呂寧可以堅持到最後解決辦法的到來。然而,在這些發生時,另一層聯系接了進來:帕彭內閣。要准確,我們應該修正老的名稱:布呂寧政府是一個前波拿巴主義政府。布呂寧只是一個先驅。在完美的形式中,波拿巴主義在帕彭——施萊謝爾政府中登上舞台。」(1932年9月)
接著還有:
「然而,盡管出現了集中的權力,但這樣的帕彭政府本身還是比它的前身弱小。波拿巴主義政權只有為革命時代畫上了句號,才能由此獲得比較穩定和持久的性質:各種力量之間的關系已經在戰鬥中經受了考驗;這時革命階級的力量已經消耗殆盡;而占有階級還沒有從恐懼中解脫出來;難道明天不會帶來新的動蕩嗎?沒有這個基本條件,即群眾沒有在戰鬥中耗盡自身的力量,波拿巴主義政權就不可能發展起來。」
資本主義崛起階段的波拿巴主義凌駕於社會之上,壓制和「仲裁」社會內部的公開衝突,調節階級對立。它是強大而自信的。在生產力強大發展的條件下,它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資本主義衰落時期的波拿巴主義受到了衰老的影響。它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中崛起,卻無法解決它所面臨的任何問題。社會的主要危機,即生產力和私有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已經變得如此巨大,它所引發的階級對立如此緊張,以至於僅憑這一點就能使衰老的波拿巴主義崛起,同時也因此使它變得如此軟弱無力,以至於它的整個結構搖搖欲墜,很可能在它所面臨的一系列危機中被推翻。正是波拿巴主義的這種軟弱性導致資產階級和軍事集團將政權拱手讓給法西斯主義,並發動瘋狂的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及其階級組織。
盡管不同的政權類別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至關重要,但它們並不是形而上學的抽像概念,並不表明它們之間存在僵化、固定和永恆的區別。
這其中牽涉到許多因素,因此有必要在明確界定每種制度的地位之前對其進行具體研究。
我們只需指出,即使在每一個粗略的類別中,也可以包含大相徑庭的制度。英國的封建殘餘(上議院和君主制)和對殖民地人民的野蠻壓迫是一種「民主」。瑞士聯邦共和國、法律以《拿破崙法典》為基礎的法國、美國、魏瑪德國和愛爾蘭——盡管差異巨大,但仍然是「民主政體」。那麼,將這些政權歸為一類的主線是什麼呢?
盡管它們的歷史各不相同,這也解釋了它們不同的民族特色,但它們都擁有某些共同的特質。這些特征是決定馬克思主義分類的決定性因素。所有國家都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工會、政黨、俱樂部等,並享有相應的權利。罷工權、組織權、選舉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以及過去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其他權利。(在此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在我們對一個政權進行分析時,林林總總的權利喪失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各種關系的整體。)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內部存在著新社會的要素。或者,正如托洛茨基在《德國,唯一的道路》中回答史達林極左派時所解釋的那樣,在資產階級的政權下,已經存在著工人階級以工人組織的形式進行統治的雛形。
在這些組織存在並發揮強大作用的地方(在法國和義大利,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資產階級通過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和高層進行統治。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某一階段,資產階級甚至通過蘇維埃,或者更正確地說,通過蘇維埃的孟什維克領導層進行統治,這並非沒有意義。
法西斯主義也有其特殊性。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和畢蘇斯基[7]的政權都屬於這一概念的範疇。然而,它們之間又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從根本上說,這一概念的核心是徹底摧毀所有工人階級組織。然而,即使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直到戰爭爆發前,波蘭法西斯主義還遠遠弱於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它並沒有完全成功地摧毀工人組織,可能在最終成功摧毀工人組織之前就已經被推翻了。
波拿巴主義也呈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拿破崙、路易-拿破崙、施萊謝爾和帕彭、貝當以及各個轉變成波拿巴政權的法西斯政府,所有這些都是波拿巴政權。他們有什麼共同點呢?國家的獨立,「個人」權力的集中,直接而公開地依賴於國家機器通過軍事–警察機器的赤裸裸的權力進行的統治,亦即「刀劍之治」。無論政權之間存在何種差異,無論工人組織的存在在某些情況下權利被削弱或受到限制,它們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每個國家的具體特點又取決於該國的歷史、使波拿巴主義得以發展的社會矛盾的發展等等。
因此,在資本主義衰落時期,貝當和施萊謝爾所領導的軟弱無能的波拿巴主義與拿破崙在其上升時期建立的充滿活力和強大的政權相比是大相徑庭的。在從民主到法西斯的轉變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或許是多個過渡階段。因此,將國家劃分為兩個敵對陣營——法西斯小資產階級陣營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陣營,為波拿巴主義鋪路。名義上,國家權力獨立於這兩個陣營,而建立的軍警政權則為將權力移交給法西斯主義鋪平了道路。(資產階級傾向於通過民主手段進行統治。然而,在危機的影響下,他們利用法西斯幫派作為恐怖機構,對無產階級施加壓力,以便推行波拿巴主義獨裁措施。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才不情願地向法西斯交出權力。)至少這就是義大利和德國所發生的過程。根據包括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政策在內的許多因素,如果反動派成功地暫時穩定了自己的局勢,歐洲和其他地方的事態發展可能會有些不同。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德國施萊謝爾和帕彭內閣、法國貝當的政權以及慕尼黑會議後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羅維將軍的政權,都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直接發展起來的(也許經過了中間階段)。杜梅格[8]、拉瓦爾和弗蘭丹的前波拿巴主義甚至波拿巴主義政權為法國的人民陣線鋪平了道路,而人民陣線又為波拿巴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弗朗克同志在下面的引文中稱布盧姆領導下的人民陣線為「波拿巴主義」,這只會在第四國際的隊伍中造成不可估量的混亂:
「……但是,沒落資本主義的波拿巴主義也可以披上其他外衣。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左翼政府,甚至是非常左翼的政府,特別是人民陣線類型的政府中,很難識別它。在那裡,波拿巴主義令人發指地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以至於許多人都被它所迷惑(!)。」
弗朗克同志的話是混淆政權特征的關鍵所在。我們很容易陷入這樣的誤區,因為正如新社會形式的胚胎存在於工人組織中一樣,波拿巴主義的可能性也植根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社會結構中。每個國家內部都反映了社會內部的對立,即使在最自由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中也是如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寫道: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像和現實』。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歸根結底,每個國家都建立在赤裸裸的武力之上。在危機和社會發酵的條件下,為資本主義利益服務而訓練和挑選出來的軍官、總參謀部小集團、警察和公務員官僚機構,為軍事陰謀和陽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皮埃爾·弗朗克在這裡混淆了國家與波拿巴主義的作用。不以武力為基礎、沒有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器的民主,從來沒有存在過,也永遠不會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形成。
但是,由於每個國家都是建立在武裝部隊及其監獄、法院等附屬機構的基礎上,因此,即使在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下,我們也有資本主義的隱蔽專政,這並不意味著每個鎮壓政權都一定是波拿巴主義。當資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脅時,在「正常」條件恢復之前,也就是在群眾沒有積極反抗而接受資本枷鎖之前,每一個政權,包括民主政權,都會在「緊急」條件下鎮壓和壓制工人的權利。資產階級保持著極大的靈活性,根據群眾和階級力量等的反抗來操縱政權。多虧了工人領導層的背叛,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
根據事態發展作出預測
無論英美帝國主義最初有什麼欲望或願望在歐洲強加波拿巴主義政權,他們很快就看到了這是不可能的(希臘除外),因為這將帶來無法估量的危險,於是他們在西歐轉向了以解除武裝的無產階級為基礎的民主政權。
法國和西歐發生的事件證實了皮埃爾·弗朗克的方法是不正確的。自法國「解放」以來,西歐各地的趨勢都是穩步走向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是越來越大的獨裁政權;是增加民主權利,而不是限制民主權利。在稍後階段,這種趨勢將會逆轉,但目前西歐的趨勢是走向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因此,在義大利,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工會等被建立;法國有了選舉、政黨、工會等;在比利時和荷蘭,民主選舉也有了。群眾向社會黨-共產黨的搖擺反映在這些政黨獲得的選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為了動員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與之抗衡,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並沒有依靠法西斯反動勢力(法西斯反動勢力仍有很大的後備力量),而是依靠建立在議會民主基礎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政黨。這給了資產階級喘息的空間,以便在以後的階段和必要的有利條件下,為通過波拿巴主義政權向極權專制過渡做好準備。
顯然,當今的情況與法西斯主義勝利前德國和義大利的情況完全不同,當時德國和義大利組織了法西斯主義群眾政黨,整個局勢使國家有可能在兩個致命的敵對陣營之間周旋。與此相反,在義大利和法國,基督教民主黨正與工人組織合作,組成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聯合內閣。資產階級不能不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會給群眾帶來革命騷亂的危險。
這種情況與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類似。為了阻止革命,資產階級組織了一個由社民黨和天主教中央黨[9]組成的聯合政府。
這是波拿巴主義嗎?顯然不是。但由於社民黨的政策,他們受到了小資產階級向反動搖擺的懲罰,1920 年的卡普政變(Kapp Putsch)[10] 中,波拿巴主義——君主企圖發動政變。眾所周知,波拿巴政變企圖被群眾擊敗,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參加了大罷工。由於共產黨進行了正確的宣傳,警告了這一危險,並結成統一戰線來擊退它,工人們義憤填膺,導致魯爾區的工人試圖奪取政權。反動派隨後與社會民主黨人聯合起來,鎮壓了這場群眾運動。這反過來又為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權鋪路。
關於歐洲政權性質的錯誤立場源於不正確的觀點。美國同志認為,在帝國主義同盟國取得勝利後,歐洲只可能出現佛朗哥式的軍事獨裁政權。皮埃爾·弗朗克贊許地引用了國際書記委在 1940 年采取的錯誤立場:
「如果英國明天在法國建立戴高樂政權,他的政權與貝當的波拿巴主義政府沒有絲毫區別」。
有一點不同,弗朗克同志!對工人來說,這是決定性的不同!誠然,資本家階級在戴高樂統治下繼續統治,就像他們在貝當統治下一樣。但是,在1946年就認為這兩個政權無法區分,這就陷入了德國史達林主義者的宗派主義愚蠢之中,他們無法區分依靠工人組織的資本主義政權和廢除這些組織的法西斯主義政權。
皮埃爾·弗朗克勝利地宣稱貝當政權是波拿巴主義政權,這進一步暴露了他的思想混亂。托洛茨基說過,貝當政權是波拿巴主義的。但弗朗克就是不明白托洛茨基的意思。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權腐朽沒落的時期,托洛茨基把他們的政權稱為波拿巴主義政權。這些政權與貝當政權的唯一區別在於,貝當從未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樣在小資產階級中擁有群眾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不能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而只能被稱為波拿巴主義。因此,他的政權要弱得多,更容易被群眾運動推翻。貝當的統治必須依靠外國的刺刀。否則,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權在其衰敗階段與貝當的政權沒有任何區別。
弗朗克同志宣稱:
「……我們最負責任的國際組織已經預言,在盟軍取得勝利之後,簡單地更換幫派並不意味著政權性質的改變。第四國際多年來一直捍衛自己的立場,反對工人運動中其他傾向和組織散布的所有其他理論和廉價標簽。如果我們犯了錯誤,那將是一個相當大的錯誤,我們必須立即尋找錯誤的原因並加以糾正。至於我們自己,我們認為我們的組織在這一點上沒有錯誤……」
1940年國際書記委的聲明是錯誤的。我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情有可原的。但在 1946 年重複一個在 1943 年就已經很明顯的錯誤是不可原諒的。我們在 1943 年撰寫的一份英國托派決議中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該決議對即將到來的歐洲局勢作了如下分析:
「由於缺乏在群眾中扎根並具有傳統的經驗豐富的托派政黨,歐洲革命鬥爭的最初階段很可能會進入克倫斯基主義或人民陣線主義時期。義大利工人最初的鬥爭以及社民黨和史達林主義者的一再背叛已經預示了這一點。」(工人國際聯盟全國會議主要決議,1943 年 10 月)。
事態的發展證明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弗朗克沒有坦誠地面對觀點上的錯誤,而是罔顧現實,試圖將錯誤轉化為美德。
弗朗克將法國作為其論點的基石。他現在肯定對此感到惋惜。因為首先是法國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進程。法國是歐洲的關鍵,任何關於法國政權性質的錯誤都可能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年輕干部造成致命打擊。
讓我們來看看現今情勢。皮埃爾·弗朗克對當下事態的發展作了如下描述:1934年以來歐洲各國都是波拿巴主義,因為資產階級負擔不起資產階級民主;貝當是波拿巴:戴高樂是波拿巴;人民陣線(布盧姆!)是波拿巴主義;事實上,正如形而上學家所說:「在暮色中,所有的貓都是灰色的」。論點是,所有人都是波拿巴。由此可見,古安就是波拿巴,隨之而來的政府也將是波拿巴主義的。如果法國人染上了這種瘋狂的思想,我們的法國黨就會陷入困境。令人欣慰的是,這種危險顯然並不存在。
馬克思主義式的評估會與皮埃爾·弗朗克的看法有些不同。政權是如何發展的——從什麼發展到什麼?各階級的地位如何?各階級之間的關系如何?對過去兩年的冷靜分析會告訴我們:(a)這裡有一場未完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結果導致了(b)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議會、選舉、制憲、資產階級民主憲法;(c)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候選人波拿巴。真正的權力掌握在主要的工人階級政黨手中。在爭奪權力的希特勒和掌權後的希特勒不是一回事。像戴高樂這樣的未來波拿巴和真正的波拿巴用劍揮舞著真正的個人權力也是兩碼事。戴高樂可能會成為法國的佛朗哥,但我們不會在決戰開始之前就宣布敵人勝利。
現代波拿巴主義就其本質而言,必然是一種過渡政權——向法西斯主義過渡、向民主過渡,甚至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這是一個階級間周旋的時期。不言而喻,歐洲局勢中存在著波拿巴主義的因素。但只有在特定條件下,這些因素才能轉變為主導因素。如果宣布一個政權是波拿巴主義的,那麼就必須指出該政權的具體特征。盡管皮埃爾·弗朗克極力想把戴高樂推上他所向往的位置,但「波拿巴」戴高樂在衡量了各種力量的關系後,不得不黯然退場,等待更有利的時機。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回答史達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宣傳時,有必要警告說,他們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反革命和波拿巴主義的危險:如果無產階級不驅散由總參謀部、警察和文官集團的干部組成的波拿巴主義巢穴,不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會面臨軍警專政的威脅。
同志們決不能重蹈德國共產黨人的覆轍,他們把每一個政權都說成是「法西斯」,直到最後,在他們的忽悠和迷惑下,真正的希特勒來了。當然,如果皮埃爾·弗朗克繼續長期重複這種說法,毫無疑問,現實最終將與他的定義相吻合,我們將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內目睹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建立。但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還不夠。我們必須煞費苦心地分析和解釋政府的每一次更迭。這樣,我們才能為即將發生的事件做好準備。
克倫斯基政權是「波拿巴主義」嗎?
弗朗克在文章中不時提到「類似克倫斯基的波拿巴主義者」,即克倫斯基的波拿巴主義,從而假定波拿巴主義實際上是在克倫斯基政權下建立起來的——這完全不符合對俄國當時情況的了解。
弗朗克摘取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俄國克倫斯基政權的一兩個有條件的提法,並試圖將其轉化為硬性的定義。實際上,歷史記錄不利於他的論點。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俄國革命史》一章的標題不是「波拿巴主義」,而是「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俄國革命中的波拿巴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對定義總是特別謹慎,因此當他說「分子」時,他並不是指事物本身。這是有充分理由的。毫無疑問,克倫斯基本想扮演波拿巴的角色。波拿巴主義的可能性植根於當時的形勢。但波拿巴主義從未實現,因為布爾什維克黨是強大的,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給冒險家留下任何控制的途徑。我們亦能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把克倫斯基政權定性為波拿巴主義是有條件的。托洛茨基在弗朗克同志所引用的章節中摘錄了一句話,稱克倫斯基是「俄國波拿巴主義的一個幾何中心」:
「敵對的雙方都訴諸克倫斯基,每一方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部分影子,雙方都發誓說忠於他,當時身在監獄中的托洛茨基寫道:『由什麼都害怕的政治家所領導的蘇維埃不敢執掌政權。各種私有制的代表立憲民主黨還沒有能力執掌政權。剩下的事情就是尋找個大人物調停者、中間人和仲裁法官。』
在克倫斯基以個人名義發布的告人民書當中宣稱:『我作為政府首腦……並不認為自己有權在變動(政權結構)一事前停下步來……這些變動將擴大我在高層管理事務中的責任。』這是純粹的波拿巴主義用語。盡管得到了左右兩方的支持,後來事態發展還是跟這種語言風格不相符。」(俄國革命史,第三卷,托洛茨基,作者的強調)
托洛茨基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冷靜地評價和權衡他所寫下的每一個字。而如果認真研究列寧的著作,即使是在事件的緊要關頭寫的,也會發現弗朗克混淆病菌和疾病的立場是錯誤的。例如,列寧在「波拿巴主義的開始」一文中寫道:「克倫斯基內閣無疑是波拿巴主義已邁出頭幾步的內閣。」。
從這裡可以看出,列寧和托洛茨基所說的是有條件的。就在弗朗克引用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把克倫斯基政府稱為波拿巴主義,緊接著的幾段話就表明了這種說法的條件性。在談到作為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的國家及其一切形式時(這就是提到波拿巴主義的那一章的標題,也是列寧所要論述的),他接著說: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國中,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頭幾個月裡,也可以說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聯姻的蜜月期間。」
在同一本小冊子隨後描述同一歷史時期的部分,列寧在將蘇維埃與議會機構進行對比時又說:
「『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這正好擊中了現代的議員和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哈巴狗』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裡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後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裡,在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經顯露出來了。」(作者的強調)
如果我們使用皮埃爾·弗朗克的方法,我們就不得不把列寧的申論貶低為一大堆愚蠢的矛盾。對他來說,沒有真正的矛盾,因為他沒有把資產階級民主和波拿巴主義真正地對立起來。如果他把這一觀點貫徹到底,他就不得不說,我們在法國既有資產階級民主,也有波拿巴主義,這樣他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權」一詞的反對就變得完全不可理解了。
弗朗克指出,英國同志把英國的工黨政府稱為克倫斯基政權,然後又說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國家沒有波拿巴主義政權:
「既然我們在這裡談到了我們英國同志的決議,那我們就注意到,它把新的工黨政府定義為『克倫斯基主義』。他們所忽視的波拿巴主義找到了辦法,以一個非常特別的名稱把自己寫進了他們的文件。但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阿特利政府是類似克倫斯基的波拿巴主義。」
這只能說明,弗朗克並不理解克倫斯基政府或波拿巴主義的含義。克倫斯基政府是無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反革命之前的最後一個或「倒數第二屆」左翼政府。在特定條件下,這種時期的社會緊張局勢和階級的尖銳衝突往往會引發波拿巴主義的陰謀和策劃。這正是俄國革命中發生的情況,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提到克倫斯基政權內部的波拿巴主義傾向的原因。然而,為了弗朗克同志需要清楚地理解,這並不意味著克倫斯基政權就是波拿巴主義政權。在這裡,也許我們最好匆忙補充一句,把工黨政府說成是克倫斯基政府,這根本不是一種完備的評價,而是一種類比,我們在這種類比中加入了適當的和必要的保障措施。為了使這個問題不再引起爭議,我們引述我們的決議案:
「在以後的階段,資產階級中最堅決的一部分人將開始尋求以西班牙的普里莫·德里維拉(Primo de Rivera)為榜樣的保皇黨或軍事獨裁或類似的解決辦法。以退役軍人或『愛國』協會為幌子的保皇黨或法西斯團伙將開始湧現。
「事件可能會加速或減緩這些進程,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緊張局勢和階級仇恨將會加劇。反動派獲勝的時期已經結束,一個新的革命時代在英國開啟。革命在起起伏伏中以或大或小的速度開始了。工黨政府是克倫斯基政府。這並不意味著革命的發展速度會與 1917 年 3 月後俄國發生的事件相吻合,相反,革命可能會呈現出曠日持久的特點,但它為群眾革命黨的建立提供了背景」。
幸運的是,為了正確看待這一立場,托洛茨基在論述共產國際對 1931 年西班牙革命的錯誤立場時,給出了克倫斯基主義的定義(他沒有稱之為波拿巴主義!):
「…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中,法西斯主義(作者注:我們可以加上波拿巴主義)絕對不是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現存政權(作者注: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和社會黨的聯合政府,類似於今天義大利和法國的政府)非常符合『克倫斯基政府』(即最後一屆、或『倒數第二屆』左派政府)這一概念,資產階級在反對革命的鬥爭中只能建立起這種政府。但這種政府並不必然意味著虛弱或屈服。在缺乏強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時候,由半改良、左的詞句、更左的手勢和鎮壓所組成的混合體,能比法西斯主義更有效地服務於資產階級(作者注: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赤裸裸的軍事獨裁)。」
弗朗克對民主和波拿巴主義的朦朧概念可以從他散見於文章中的參考文獻中看出。僅舉幾例:
「使用民主口號——結合過渡口號——更確切地說,是有道理的,因為產生民主政權的可能性並不存在……」
「正因為我們目前在歐洲普遍沒有民主政權,因為根本沒有民主政權的立足之地……」
「我們不能把『右派』的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左派』的波拿巴主義與民主主義混為一談。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主義會根據兩個對立陣營所處的條件而采取截然不同的形式;我們還堅持認為,民主自由的存在,即使提供非常大幅度的民主自由,也不足以使一個政權成為民主。波拿巴主義者(即克倫斯基)、人民陣線……甚至因其泛濫的民主自由而臭名昭著,甚至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因此而面臨平衡風險和傾覆危險的地步。民主自由權利並不像人們可以正確定義為民主的政權那樣,是從資本主義內部存在改革餘地出發的,而是相反,是從嚴重危機的形勢出發的,是沒有任何餘地或改革的結果。”
「……人民陣線的政權並不是一個民主政權;它本身就包含著許多波拿巴主義的因素,我們將隨後看到這一點。」
弗朗克同志提出的民主概念在天地間從未存在過。它只存在於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准則中。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總是建立在鎮壓的框架之上。每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或每一個資產階級政權都有其第 48 條,如魏瑪憲法。階級社會的存在以壓迫制度為前提。但是,只有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的人才能將民主等同於波拿巴主義,或者等同於法西斯主義。雖然這些政權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所有這些政權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赤裸裸的軍事統治因素。但是,量變會產生質變。決定政權性質的不是這個或那個因素,而是其基本特征。今天的民主明天可能變成波拿巴主義,後天又會變成法西斯主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法西斯主義可以轉變為民主主義,並重複這一過程。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加區分地把所有政權混為一談。這是簡單的方法,但會導致錯誤和混亂。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在事物的變化和演變過程中加以研究。依次研究每個政府,確定其具體特征和傾向。為突然的變化和過渡做好準備,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從而在必要時糾正和界定我們在每個連續階段的特征。皮埃爾·弗朗克的方法(他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是印像主義)的痛苦局限性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
「『波拿巴主義』一詞並不能完全概括該政權的特征,但在當今的歐洲,如果我們想盡可能少地犯錯誤,就必須使用這個詞。最後,讓我們補充一點,並非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擁有如此重要的一般觀念:所有科學都是如此。因此,化學家稱各種物質為碳化物,它們之間的差異比施萊謝爾的波拿巴主義和克倫斯基的波拿巴主義還要大。化學也不會因此而變得如此糟糕。事實恰恰相反。」
史達林主義者在第三時期使用了同樣的方法,在德國取得了可悲的結果。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法西斯主義的所有政黨都是資本家階級的代理人這一正確的概括開始……他們最後說,因此……它們之間沒有區別——都是不同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者。對於科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問題的起點是弗朗克的終點。化學家可以把某些物質歸類為碳化物。但是,如果一個化學家只停留在這個定義上,那他的研究就不會順利進行!例如,如果一個化學家把碳化硅和碳化鈣都定義在同一個「碳化物」標題下,而試圖用前者而不是後者來點燃自行車上的乙炔燈,那麼就會出現一些非常糟糕的結果。我們將無法照亮前方的道路。弗朗克的方法也無法照亮歐洲政權的本質。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注釋
[1] 原文編者注:在1943-1946年間。德國,美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阿根廷,葡萄牙,愛爾蘭和中國的政府首腦領導的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的政權,都是基於資本主義體制的。
[2] 原文編者注:拿破崙·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崙一世)在霧月十八日 (1799年11月9-10日)的一場政變中奪權,並在1804年稱帝。路易波拿巴 (Louis-Napoleon Bonaparte,拿破崙三世)在1848年贏得(總統)大選。在1851年的一場政變中他解散了立法機構並於1852年稱帝。
[3] 譯者注:英國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是第四國際在1944年至1950年間的英國支部。當時泰德·格蘭特為其首席理論家。英革共捍衛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時常反對第四國際領導層後來越發嚴重的政治錯誤。
[4] 原文編者注:魏瑪是 1919 年制定新憲法的德國城市。帝國國防軍是魏瑪德國的正規軍。有關 1918 年革命和 1919 年 1 月「斯巴達克起義」的完整描述,請參閱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所著的《德國——從革命到反革命》。
[5] 原文編者注:1944年5月,同盟國解放羅馬時,由於害怕激起新一波工人起義,他們違背先前與被流放國王維克多·伊曼紐爾的條約,阻擋了任何重建君主制的企圖。
[6] 原文編者注:海因里希·布呂寧在1930-32年擔任德國總理。1931年末他廢除了幾乎所有勞動合同並限制了媒體。國防軍將領庫爾特·馮·施來謝爾在1932年12月繼任馮·帕彭的總理位置。兩個月內他便被希特勒取代。
[7] 原文編者注:約瑟夫·畢蘇斯基(Josef Pilsudsky)1926年在波蘭領導了一場政變,並成為了獨裁者直到其在1935年過世。
[8] 原文編者注:加斯東·杜梅格,法國的一位前總統,在1934年2月6日的一次企圖的政變後,出任總理,承諾一個『強勢』的政府。皮埃爾·賴伐爾,1935-36年法國總理,1942年任通敵/賣國的維希政權總理。皮埃爾·弗朗丹在1934-35繼任杜梅格的總理職位。
[9] 原文編者注:天主教中央黨(Catholic Centre Party,又名德國中央黨)是一個德國基督教民主黨派。
[10] 原文編者注:卡普政變相關信息詳見請參閱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所著的《德國——從革命到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