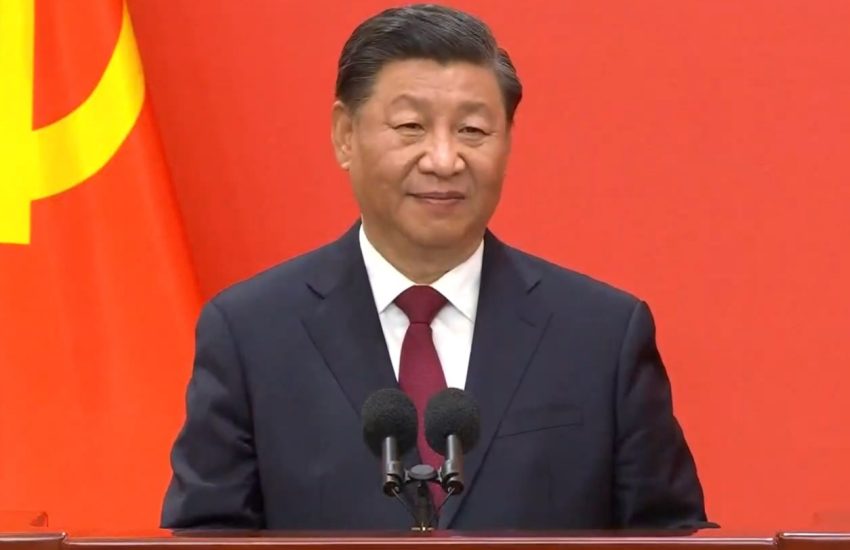托洛茨基: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按:本文原文寫於1934年7月15日。摘自《新國際》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第37-38頁。以下譯文是以收錄於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的版本為基礎。譯者:楊進)
在急劇社會衝突、政治快速動移、情勢突變的時期,一個正確的理論取向的巨大實際重要性最為顯著。在這樣的時期,既有的政治觀念和概括迅速耗盡用途,並需要被完全取代(這比較容易),或者需要具體化、精確化或部分修正(這較為困難)。在這樣的時期裡,各種過渡、中間的情況和組合不可避免地出現,並擾亂了我們先前習慣的判斷思維,因此對於理論問題上的注意就需要更加持續。簡言之,在和平和「有機」的(也就是戰前)時期,我們仍然可以受益於幾個現成的抽像概念,但在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每一次新事件都強烈地驗證了辯證法的最重要規律:真理始終是具體的。
史達林主義者對於法西斯主義所做出的理論分析,無疑是由於在每個具體階段、每個過渡階段,也就是在其逐漸變化以及革命(或反革命)躍遷中,由於基於局部和不足的歷史經驗(或對整體的狹隘和有限視角)而制定的抽像範疇,因而帶來了有害的實際後果。史達林主義者接受了這樣一個觀念:在當代,金融資本無法適應議會民主,因此前者被迫訴諸法西斯主義。他們從這個在一定範圍內是絕對正確的觀念中,純粹以演繹、形式邏輯的方式對所有國家和所有發展階段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對他們來說,普里莫·德·里韋拉、墨索里尼、蔣介石、馬薩里克、布呂寧、多爾福斯、畢蘇斯基[1]、塞爾維亞國王亞歷山大、塞弗林、麥克唐納等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代表。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忘記了:(a)在過去,資本主義也從未適應於「純粹」的民主,有時輔以公開鎮壓,有時用另一種策略取而代之;(b)「純粹」的金融資本到哪裡都是不存在的;(c)即使占據主導地位,金融資本也不能在真空中行動,而是必須考慮到其他階層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抵抗;(d)最後,議會民主和法西斯主義政權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系列過渡形式,它們相繼出現,有時「和平地」,有時通過內戰而產生。而且,如果我們要前進而不落後於事態發展,每一種過渡形式都需要正確的理論評估和相應的無產階級政策。
基於德國的經驗,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首次繪錄了一種過渡性的政府形式(盡管它本該在義大利經驗的基礎上成立),我們稱之為波拿巴主義(布呂寧、帕彭、施萊謝爾政府[2])。後來,我們在奧地利觀察到了更為精確和完善的波拿巴主義政權。這種過渡形式的決定論已經明顯,當然不是以宿命論的意義,而是以辯證法的意義,也就是說,在某個國家和時期內,法西斯主義在沒有遭遇無產階級的抵抗勝利的情況下,越來越成功地攻擊議會民主的立場,並以此來扼殺無產階級。
在布呂寧-施萊謝爾時期,馬努伊爾斯基-庫西寧[3] 宣稱:「法西斯主義已經到來」; 對於我們所提出的中間階段、波拿巴主義階段的理論,他們宣稱我們在掩蓋和掩飾法西斯主義,以便更容易讓社會民主黨采取「較小惡」的政策。當時,社會民主黨人被稱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而齊羅姆斯基-馬索·皮韋爾-朱斯等「左派」法國社會民主黨人在「托派」之後被史達林主義者認定為最危險的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所有這些現在已經改變了。對於今天的法國,史達林主義者不敢重復說:「法西斯主義已經到來」; 相反,他們接受了之前被他們駁斥的聯合陣線政策,以防止法國的法西斯主義獲勝。他們不得不將杜梅爾格政權[4]與法西斯主義政權區分開來。但他們是作為經驗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來做出這種區分的。他們甚至不試圖對杜梅爾格政權給出科學定義。在理論領域中只會運用抽像範疇的人,注定會盲目地向事實認輸。然而,恰恰在法國,從議會制度向波拿巴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的過渡具有特別引人注目和示範性的特征。我們只需回顧一下,杜梅格政府正是在法西斯分子預演內戰(2月6日)和無產階級大罷工(2月12日)之間出現的。一旦不妥協的陣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采取了備戰姿態,議會制度這部精算機很快就會失去其所有重要性。確實,杜梅爾格政府如同當年的布呂寧-施萊謝爾政府,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得到議會的同意下執政。但這是一個已經讓出權力的議會,一個知道在面對抵抗時政府會遺棄它的議會。由於反革命陣營攻擊和革命陣營之間的暫時相互抵消,權力的軸心已經提升到了階級和他們的議會代表之上。他們也必須在議會之外和「黨派之外」尋找政府首腦。政府首腦征召了兩位將軍來幫助自己。這個三人通過其右翼和左翼對稱排列的議會人質來支持自己。政府不是作為議會多數派的執行機構出現,而是作為兩個鬥爭陣營之間的裁判者。
然而,一個將自己提高於國家之上的政府並不是懸空、無支持基礎的。當前政府的真正軸心在於警察、官僚機構和軍事集團。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軍警獨裁制,只是用議會制度的外衣掩飾而已。而以軍刀作為國家的裁判者的政府,正是波拿巴主義的。
軍刀本身沒有獨立的綱領,它只是維持「秩序」的工具。它被召喚來維護現狀。波拿巴主義,正如其前身凱撒主義一樣,在社會意義上,始終代表著剝削者中最強大、最堅定的一部分的政府;因此,當代的波拿巴主義除了能夠是金融資本的政府之外,沒有其他可能,而金融資本則指揮、鼓吹和腐蝕著官僚機構、警察、軍官階層和新聞界的高層人員。
近幾個月來持續有關於「憲法改革」的討論,其唯一任務就是使國家機構適應波拿巴主義政府的要求和便利。金融資本正在尋找合法的途徑,以便每次都能在強迫名存實亡的議會作出同意下,向國家強加一位最合適的仲裁人。很明顯,杜梅爾格政府並不是「強勢政府」的理想典範。備選的波拿巴人選還存在著。如果未來的階級鬥爭的進程給予足夠的時間,這個領域可能會有新的經驗和組合出現。
在進行預測中,我們不得不重復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曾對於德國所做的發言:當前法國波拿巴主義的政治機會並不大;它的穩定性取決於無常的、根本上不穩定的無產階級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臨時平衡。這兩個陣營的力量關系必將迅速發生變化,部分受經濟形勢的影響,但主要取決於無產階級先鋒政策的質量。這兩個陣營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過程的時間尺度將以月份計算,而不是年份。只有在衝突之後,根據結果而定,才能建立起穩定的政權。
法西斯主義執政,和波拿巴主義一樣,只能是金融資本的政權。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它不僅與波拿巴主義相似,甚至與議會民主也無法區分。每一次,史達林主義者都會重新發現這一點,忘記了社會問題終究是在政治領域內解決的。金融資本的力量並不在於其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隨時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權;它並沒有這種能力。它的力量在於非無產階級政府被迫為金融資本服務;或者更准確地說,金融資本具有能力在舊的統治體系衰敗時,替換為更適應變化條件的新體系。然而,從一個體系過渡到另一個體系意味著政治危機,而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活動幫助下,這種危機可能轉化為對資產階級的社會危險。從議會民主制度過渡到波拿巴主義本身,在法國就伴隨著內戰的激發。從波拿巴主義過渡到法西斯主義的前景充滿了更為可怕的動盪,因此也存在著革命的可能性。
直到昨天,史達林主義者認為我們的「主要錯誤」在於將法西斯主義視為小資產階級,而不是金融資本。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抽像的範疇放置在了各階級辯證的位置。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將小資產階級動員和組織起來為金融資本的社會利益服務的特定手段。在民主制度下,資本不可避免地試圖讓工人寄望於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相反,過渡到法西斯主義是在之前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充滿對無產階級的仇恨。在這兩個體系中,同一個上層階級——金融資本的統治建立在直接相反的被壓迫階級的關系之上。
然而,要將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動員起來對抗無產階級,除非使用社會性的煽動,是不可想像的,但這對於大資產階級來說就像玩火一樣危險。最近在德國發生的事件恰恰證實了被發動的小資產階級反動對「秩序」的威脅。因此,盡管法國資產階級支持並積極資助反動暴徒(以其一翼的形式),前者卻不希望將事態推至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勝利。他們的目標只是建立一個「強勢」的政權,最終鞭策兩個極端陣營。
上文所述已足夠證明,將波拿巴主義形式的政權與法西斯主義形式區分開來是多麼重要。然而,陷入相反的極端,即將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視為兩個邏輯上不相容的範疇,也是不可饒恕的。正如波拿巴主義始於將議會制度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因此,得勝的法西斯主義不僅被迫與波拿巴主義者建立聯盟,而且其內部會更加靠近波拿巴主義體系。金融資本不可能通過反動的社會性煽動和小資產階級恐怖手段來維持其長期統治。法西斯主義頭目上台後,被迫通過國家機器來控制追隨他們的群眾。與此同時,他們失去了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支持。其中的一小部分被吸收進官僚機構,另一部分陷入冷漠,第三部分則以各種旗幟轉入反對派。然而,雖然失去了社會大眾基礎,但通過依靠官僚機構並在階級之間搖擺,法西斯主義轉化為波拿巴主義。在這裡,漸進的演變也被暴力和流血事件所打斷。有別於反應著兩個敵對陣營之間的極度不穩定和短暫的平衡的前法西斯主義或預防性波拿巴主義(喬利蒂、布倫寧-施萊謝爾、杜梅爾格等),源自於法西斯主義的波拿巴主義(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也就是源自於兩個陣營群眾的的毀滅、失意和士氣低落,有著更大的穩定性。
關於畢蘇斯基政權「是法西斯主義還是波拿巴主義?」的問題在我們的波蘭同志們之間引發了一些分歧。這種分歧的存在最好地證明了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不可變的邏輯範疇,而是具有極為顯著特點的生動社會形態,這些形態在不同國家和不同階段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畢蘇斯基在一場以小資產階級群眾運動為基礎、直接針對傳統資產階級政黨統治的起義結束時,以建立「強勢政府」的名義上台;這是這股運動和政權的法西斯特征。但是,波蘭法西斯主義的特定政治影響力,也就是群眾基礎,遠遠弱於當時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更不用說德國法西斯主義了;畢蘇斯基更多地必須使用軍事陰謀手段,並且在對待工人組織問題上更加謹慎。只需回想一下,畢蘇斯基的政變得到了史達林主義波蘭黨的同情和支持。烏克蘭和猶太小資產階級對畢蘇斯基政權日益敵對,反過來也使他更難以對工人階級發起全面攻擊。
由於這種情況,畢蘇斯基在階級和國家各個階層之間的搖擺以及占據的地位,與相應時期的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比,大規模恐怖行動的作用較小;在畢蘇斯基政權中存在波拿巴主義因素。然而,將畢蘇斯基與喬利蒂或施萊謝爾相提並論,並期待他被一個新的波蘭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所取代,顯然是錯誤的。鑒於畢蘇斯基政權是在波蘭國家的階級和民族關系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具有當地所有的特殊性和矛盾性,若形成某種「理想的」法西斯主義形像,並將其與這個真實的法西斯政權作出對照,這在方法上是錯誤的。畢蘇斯基能否將對無產階級組織的摧毀行動進行到底呢?——形勢的邏輯無疑將不可避免地推動他走上這條道路——這不取決於對「法西斯主義本身」的形式定義,而取決於真正的力量關系、群眾之間正在發生的政治進程的動態、無產階級先鋒的戰略,最後還有西歐,尤其是法國的事件進展。
歷史可能會成功地展現,波蘭的法西斯主義會在它能夠找到「極權主義」的表達形式之前就被推翻並化為灰燼。
我們前面說過,源自法西斯主義的波拿巴主義比大資產階級為了避免法西斯主義大規模屠殺而采取的預防性波拿巴實驗要穩定得多。然而,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強調法西斯主義轉化為波拿巴主義本身就意味著它的末日開始了。法西斯主義的消亡將持續多長時間,以及它的病情何時變為臨終病榻,取決於許多內外因素。但是,小資產階級反革命活動被扼殺、幻滅、瓦解,它對無產階級的攻擊日益減弱的這份事實,開辟了新的革命可能性。所有的歷史都表明,僅憑警察機構是無法將無產階級束縛起來的。的確,義大利的經驗表明,巨大災難經歷所帶來的心理遺產對工人階級的影響要比引發災難的力量關系更長久。但是,失敗的心理惰性只是一個不穩定的支柱,它可以被一次強大事件衝擊的化解。對於義大利、德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來說,法國無產階級鬥爭的成功很可能造就這樣的衝擊。
影響著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形勢的革命關鍵,現在就是法國!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注釋
[1] 譯者注:約瑟夫·畢蘇斯基(Jozef Piłsudski):波蘭獨裁者和軍事強人,原先為波蘭社會黨成員,但遂轉為著重於改良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而後成為波蘭資產階級共和國內主要政治人物之一。
[2] 譯者注:布呂寧、帕彭、施萊謝爾政府: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uning)、弗朗茨·馮·帕彭(Franz von Papen)、庫爾特·馮·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為德國威爾瑪共和時期的三任總理。此三屆政府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越發趨向於波拿巴主義手段來維持政權。
[3] 譯者注:馬努伊爾斯基-庫西寧:德米特里·曼努伊爾斯基(Dmitry Manuilsky)和奧托·庫西寧(Otto Wille Kuusinen)為當時共產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
[4] 譯者注:杜梅爾格(Gaston Doumergue):法國右翼政治人物。於1924至1931年擔任法國總統。於1934年2月至11月期間擔任法國保守派全國團結政府的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