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說無益:要「左翼敘事」還是要階級鬥爭?
「左翼需要一種新敘事」。這就是當今世界許多左翼人士心中的想法,他們試圖建立一種能替代占主導地位資產階級政黨的方法。這種「新敘事」理念背後的實質是什麼?它能以任何方式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們前進嗎?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奧地利支部成員約拉·基普卡克(Yola Kipcak)解釋說:玩文字遊戲,不能替代階級鬥爭。(按:故事本身並不能替代階級鬥爭。哲學是大眾的、科學的,為灌水和故意「學術化」的怪話術語,不僅無益於階級鬥爭。還更可能是一劑改良主義的迷魂藥。譯者:張大戶家的羊)
左翼需要改進「敘事」的想法,以及我們需要某種「左翼民粹主義」的相關概念,已經占據整個歐洲和其他地區左翼政黨和組織的注意力。舉個例子,德國左翼黨(Die LINKE)總書記約爾格·辛德勒(Jörg Schindler)寫道:「為了讓我們站在氣候運動的最前沿,也即我們本該站到的地方。我們需要一個令人信服的左翼敘事」。
該黨主席卡蒂亞·基平(Katja Kpippers)解釋說:「我認為我們需要一種左翼民粹主義,來表明還存在其他的替代方案。我們必須加強關於『替代性』這一要點的解釋模式,並以不同的敘事方式…對抗來自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敘事」。
最後,「改造歐洲」(Transform Europe。一個由希腊激左盟(SYRIZA)、德國左翼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和左翼集團(Bloco de Esquerda)等組成的歐洲左翼黨項目)組織在19年於維也納(Vienna)舉行了一場活動,受到青年左翼人士、奧地利共產黨和其他組織的參加。在近兩個小時的討論中,「左翼敘事」一詞被隨意使用。這雖然只是一些小例子,但它見證了這些思想在不同國家左翼中扎根的程度。
關於「左翼敘事」的想法,在大學裡流傳已久。然而,隨著激左盟和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等新左翼政黨支持率的突然激增,它才真正開始流行起來,並成為國際上許多左翼人士(政黨)的參照物。這兩個政黨的知名人士,在幾年前的演講中常提及這一概念。事實上,這一想法有其「理論家」。其最突出的人物,是比利時學者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
墨菲與她已故伙伴厄內斯特·拉克勞(Ernest Laclau)一起,試圖發展一種以敘事為基礎的「左翼民粹主義」理論。在她新書《追求一種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的致謝名單中,墨菲熱衷於贊揚我們能黨的伊尼戈·埃雷洪·加爾萬(Íñigo Errejo)和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黨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的貢獻和個人對話。
「敘事」背後隱藏著什麼?
墨菲的理論認為,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基於「新左翼敘事」的「左翼民粹主義」。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現實是由敘事(也即故事)組成的。根據這一概念,如果政治家們能以扣人心弦的語言來描述人民經歷(即有效地「構築敘事」),那麼這將反過來影響人民的行動,從而產生現實本身。
她認為,是意識決定物質,而不是物質決定意識。對於客觀而不依賴於人意識存在的物質世界,其不是認識的對像和源泉。為此,資本主義也就不是一個產生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體系,而是一種敘事,一種建設。墨菲稱她的理論方法為「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t)」。這意味著,按她所說,一個能與我們大腦裡面概念相對應的客觀的、真實的世界(她稱之為「本質」)是不存在的。她認為「社會總是通過霸權主義行為來進行分割和話語建構」,它「從來不是更深層次客觀性的表現」[1]。
由此可見,社會上不存在真正的階級。工人階級只是由敘事、話語和語言創造的眾多身份之一。「集體政治主體(譯者注:即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等)是通過表像人為創造出來的,事先並不存在」[2]。
因此,左翼敘事的目標(左翼民粹主義),是通過告訴人們有共同利益,「精英」是他們的敵人,來構建一種集體身份認同。這是一種「構建政治邊界的話語策略,將社會分為兩個陣營,並呼吁動員『弱者』反對『當權者』」[3]。
朱莉婭·弗里茨切(Julia Fritzsche)在最近出版的《深紅與激進色彩—追求新左翼敘事》一書中告訴我們。這種敘事,「首先必須與人們日常經歷聯系起來,並『接地氣』。人們必須以為這種敘事和他們的共同經歷是相對應的。他們是否真的有這些經歷,則是並不重要的」[4]。
因此,每當左翼敘事捍衛者談到社會變革、實際行動時,階級鬥爭或階級行動的明顯缺席,也就不足為奇了。就算提及,那也只是把它作為某種腳注,或是某種他們認可的多余細節。相反,他們要求我們「闡明、談論、描述、展示」等。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考慮奧地利社民代表人物馬克斯·勒赫(Max Lercher)的評論。他認為社民黨需要一個新成立大會,作為黨的新起點。他寫道:
「一個捷克工業工人和一個施蒂利亞礦工有什麼共同之處?或者說,維也納社會改革家和匈牙利激進社會主義者真的相通嗎?…畢竟,我們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這是一件好事。但在海恩費爾德(Hainfeld,1888年奧地利社會主義民主工人黨成立的地點),我們設法就一些核心的、共同的想法達成一致。並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一個堅持這些思想的政黨。
「新工人階級,都是那些沒有公平機會獲得繁榮的人。這也包括中小型公司。在這裡,我們可以定義一條新的衝突戰線」。(我們的強調)。
首先,對勒赫來說。團結是基於思想「一致」來建立的,而不是基於階級利益基礎之上。其次,對他來說,社會上的衝突分野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可被人為「定義」的。所以,「中小」資本家也是工人階級一部分。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捷克工人和施蒂利亞工人實際上有很多共同點,即都從事雇佣勞動,都被資本家剝削,因此客觀上都屬於工人階級。然而,如果你假設我們的身份是由扣人心弦的情感故事構建的。那麼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資本主義不能通過對資本家的階級鬥爭來推翻,而是只能通過編寫新的故事來推翻。
然後,這個故事在人們心中變得強大(『霸權』)。正如墨菲所寫:
「[每一個]現存秩序,因此都容易受到反霸權做法的挑戰。這些做法試圖分離秩序,建立另一種形式的霸權」[5]。
弗里茨切也表示贊同:
「敘事不會是擺脫當今困擾狀況的最快方式…新左翼敘事會有裂痕和漏洞,但從長遠來看,它是擺脫壓迫性現狀的唯一途徑」[6]。
事實上,這意味著對革命的拒絕,與統治體系決裂的拒絕。左翼敘事擁護者勒赫,自覺或不自覺地采取了明顯的非馬克思主義立場。墨菲是一個自覺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她寫道,「共產主義神話…必須被拋棄」,因為共產主義內的所謂階級還原論,即把一切鬥爭都簡化為階級鬥爭,在實踐中已經失敗了。墨菲和她的同伴們認為,工人階級僅是女性主義、環保主義、LGBT激進主義等眾多運動中的一個。
她進一步指出:「社會將永遠存在對立、鬥爭和部分不透明」。換言之,她認為不平等、壓迫等是不可避免的,且永不可能被完全克服。正是在這種悲觀基礎上,她提出「反霸權主義活動」。這是對共產主義的一種替代。盡管她承認這將「永遠不會實現一個完全解放的社會。解放也不再被設想為國家的消亡」[7]。在她的理論附錄中。她圓滑地指出,「不可能有一個超越分裂和權力的社會」[8]。簡而言之,在她那復雜和看似「激進」的語言掩蓋背後,是她拒絕革命,擁護改良主義的真實面目。她將女性、LGBT人群等運動的鬥爭,與階級鬥爭割裂開來,並試圖進行階級調和。聯合部分資本家和中產階級,為「更公平」的資本主義形式而鬥爭。
「左翼敘事」想法的一些更大膽支持者,可能會討論資本主義。但消除資本主義這一想法,仍然是他們心中最遙遠的事情。勒赫一度表示:「對資本主義的明智批評是適當的,我們必須接受這個問題」。在同一采訪中,他更准確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部分國有的就業市場,它符合市場要求,但不以盈利為導向」。
這些半控制措施與混亂的資本主義的混合產物,和試圖讓老虎吃素一樣,比任何由工人階級控制的國有化、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更具烏托邦主義空想色彩。
我們在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思想的哲學基礎,如何導致了「資本主義本身是不可觸碰的」之結論。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站在堅定的哲學基礎上。揭露改良派的真實面目,用一個革命答案來反擊他們的重要性。
「成為國家」
所謂「左翼敘事」支持者的主要方向,不是推動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而是推動民主訴求。勒赫在他的文章中寫道:「我們必須敢於爭取更多的民主」,為什麼我們今天需要社會民主主義?前任奧地利社會主義青年團主席朱莉婭·赫爾(Julia Herr)也曾表示:「1970年代的社民黨,在為經濟體系的民主化和公平分配社會財富而奮鬥。然後,不知何故,我們就在某個時候失去了信心」。
與德國左翼黨關系密切的智庫「現代團結協會」(Institut Solidarische Moderne)解釋說:「社會問題本質是民主問題」。ISM思想家和左翼黨盧森堡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托馬斯·塞伯特(Thomas Seibert)說,真正的鬥爭是為了爭取「真正的民主」。
而墨菲寫道:
「在我看來,現代民主社會的問題,在於『人人自由平等』的構成原則沒有付諸實踐…因此,我們主張的『激進和多元民主』,可被視為現有民主體制的激進化…」[9]
這裡提出的觀點正是維持現狀!現有「民主」機構的上層建築,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並受其操縱。它不應被廢除,而應被「改進」。與此同時,造成這一不平等和剝削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被排除在問題外。
這裡的一個關鍵分界線,是我們對國家及其所謂民主體制的概念。對於革命者來說,明確認識國家政府的本質是至關重要的。這對革命運動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想通過革命廢除國家,和相信國家可以為了被壓迫者的利益而被改造和塑造,兩者之間存在著決定性的區別。後者的觀點,無一例外地轉為與現有國家合作,與它所服務的階級利益合作。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敘事」倡導者對國家理解的不同吧。墨菲和其他「左翼敘事」者對國家的理解如下:
「[…]是各種力量關系的結晶,也是一個鬥爭的場所。[…]這些公共空間被設想為一個對抗性干預的表面,可以為重要的民主進步提供場所。這就是為什麼霸權戰略應與不同國家機構接觸,以便改造它們,從而使國家成為表達多種民主要求的工具。[…]在某種意義上,革命型和霸權型的政治,都可被稱為『激進』政治,因為它們意味著與現有霸權秩序發生某種形式的斷裂。然而這種斷裂的性質並不相同,不宜一同貼上『極左』標簽,並歸入同一類。因為情況往往與人們常說的相反,左翼民粹主義戰略不是『極左』的化身。它是通過民主的復蘇和激進化,來設想與新自由主義決裂的另一種方式」[10]。
如上所述。墨菲非常清楚地區分了「革命」方法和她自己稱之為「霸權的」自己的方法。對她來說,國家是由非共同利益機構和「職能」網絡所組成的。因此,左翼民粹主義有影響、改造和轉變它們的空間。
相反,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國家不是中立的,它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它需要被粉碎,並由一個工人國家所取代。在壓制了舊資本主義秩序,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掃清了障礙後,這個工人國家將隨階級的逐漸消失而一同與之消亡。這種觀點被墨菲等後現代理論家譏諷為「過於簡單」。但通過分析國家的歷史出現,以及國家發展的目的。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個定義抓住了國家的本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了國家是如何隨階級社會的興起,而歷史性地出現的。階級社會是隨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的,人類第一次有了超越生存最小限度的生產力。歷史上第一次有小部分社會成員不必像以前那樣勞動。但生產力還沒發展到,足以讓整個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這種特權的先進程度。這就為社會階級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因此出現了擁有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和被壓迫、剝削、占有財富的無產階級。
然而這些對立的階級利益,需被加以管理。必須讓被壓迫者相信當前秩序是不可觸碰的,任何敢於質疑它的人都必受懲罰。同時,必須防止壓迫者通過持久戰爭來消耗自己。國家正是因這個目的而誕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解釋說:
「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因此,在最後的例子中,國家是一個由武裝人員(軍隊和警察)、監獄、法院等特殊機構組成的壓迫性機構,看似凌駕於社會之上,但它從根本上捍衛了產生它的經濟體制。隨著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崛起,以及資本主義作為世界範圍內的主導生產方式,資產階級也創造了自己的國家。
墨菲所捍衛的「自由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她和其他「左翼敘事者」一樣,認為這種國家形式是有史以來最終的、最好的和最後的體制,因此絕不能被觸動。這實際上意味著采取一種完全非歷史的觀點,維護當前統治階級工具:資本家。
當然,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工具這一事實,並非總是清晰可見。它的真實特征被資本家有意識地掩蓋了。資本家們明白,只靠武力和鎮壓進行長久統治是不可能的,而且這種行為也是沒效率的。被壓迫者才是社會多數。如果大多數被壓迫者明白這一事實,資本主義社會將面臨被推翻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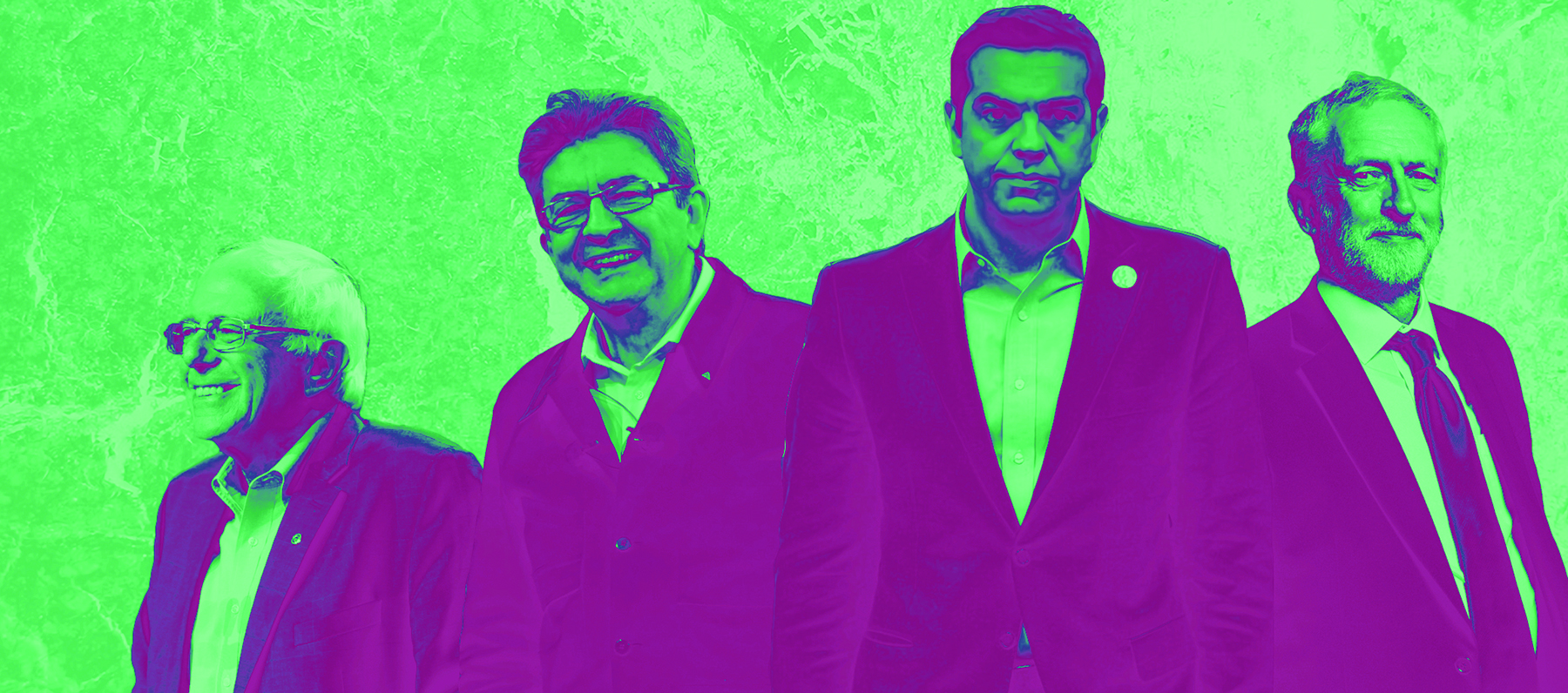
正常情況下,統治階級在能承受的範圍內,試圖保持一種公平、「機會平等」等的姿態。因此,資本家們也通常更喜歡有自由選舉、保證一定新聞自由和幾個政黨等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允許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在任何情況下,統治階級都不會允許其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基本角色受到挑戰。國家的存在,正是為了維護這一角色。
所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中有唯一不被漠視、破壞、和法律充分保護權利的第17條:「人人有權擁有財產」和「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剝奪財產」,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後,這正是國家、法律和整個司法系統的宗旨。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的,必須通過革命來粉碎資產階級國家的原因。因為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有著根本的聯系。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承認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一種在資本主義體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政治上層建築。資本主義產生了不同的政權: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和獨裁政權。然而它們都屬於資本主義,千絲萬縷地與資產階級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當然,一個政權的形式。即國家機器如何具體的表現自己,當然決定了我們的自由程度和人民所擁有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為「一人一票」等民主要求的鬥爭,在革命運動的歷史上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者一貫推進和支持民主要求,它可以動員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反對統治階級,形成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團結,從而為階級鬥爭的發展創造最好的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無視或忽視民主選舉。它可作為社會情緒的一個重要指標,參與它們可以作為階級鬥爭的一種手段。但資本主義核心矛盾是: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不斷的危機和戰爭。它在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政權下,都繼續存在,無論它是多麼的民主。這正是「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內部實施的原因。
對革命者來說,選舉和議會代表可以用來向大眾展示革命的政治思想。它們還可以被用來揭露資產階級及其機構的虛偽。例如,如果議會中的革命者要求通過征用大工業和銀行(即挑戰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建立真正的平等和社會正義,那麼整個機構將被用來反駁這一要求。
如果有必要,正如我們將在下面展示的那樣。他們將無視「民主」和議會多數,並忘記他們過去關於「自由」的所有言論,不惜一切代價拯救資本主義。如果革命者僅停於此,舉起雙手說:「哦,好吧,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我們只是還沒有贏得國家內部的霸權鬥爭」。那麼,他們就根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派。這正是「左翼敘事者」所建議的。通過接受經濟體制(資本主義)及其政治上層建築(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制,他們不能再前進一步。
另一方面,革命者把群眾活動看作是超越這些限制和改變社會的關鍵因素。議會和選舉只是加強和促進他們活動的一個有益因素。列寧指出:「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條經驗」顯示了「把反動議會外的群眾行動和議會內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對派的活動配合起來」的巨大效用。同時,他解釋說。
「因為群眾的行動,例如大罷工,任何時候都比議會活動重要,決不是僅僅在革命時期或在革命形勢下才如此。」。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可被概括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壓迫性工具。它必須被廢除,並由一個工人國家所取代。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後,所有形式的國家和階級都終究會一起消亡。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認為現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是不必要的。相反,我們為這些自由而戰,並加以利用它。但與此同時,我們並沒有播下任何幻想。認為民主可以解決那些導致壓迫、貧窮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這些問題,只能通過廢除資本主義來實現。
「左翼敘事」理論家們果斷地拒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他們的論點主要集中在民主問題上。他們認為,「很明顯,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沒有必然關系。不幸的是,馬克思主義把自由民主說成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助長和加劇了這種混淆」。
實際上,「不幸的混淆」完全在於這些語言哲學家。對他們來說,國家只是「論述性的」建構,是一個可被「新敘事」改變的機構。國家是一個「鬥爭場所」。為「重新闡明」這個大概是中立的、獨立於所有階級的「場所」,人們必須成為它的一部分。「目標不是奪取國家權力,而是成為國家」。
這就再一次說明了,為什麼這種理論如此受改良派歡迎。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最好盡可能減少來自群眾的干擾,是改良派存在的理由。在以國家機器為代表的「鬥爭領域」,目標變成了與資本家在平等條件下建立伙伴關系,以便就改善選民狀況達成協議。
勒赫對此有如下描述:「社民黨必須向資本展示它的地位,並馴服市場。[…]我心中有一個社會福利國家,它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繁榮,並留下一些回旋余地」。
但要注意!在與階級敵人(他們不會用這個詞)的對抗中,重要的是「衝突發生時不采取『對立』(敵人之間的鬥爭)的形式」,相反,「不要把對手看作是要被消滅的敵人,而被認為是合法存在的對手」。
這只是「社會伙伴關系」,以及階級利益的平衡,被翻譯成了學術怪話。如果有可能通過「在新模式上耐心、和平的工作」(參見弗里茨切)來獲得不斷改革和改進,大多數工人階級當然不會有什麼異議。
然而問題是,資本主義由於其自身的矛盾,一再的陷入危機。邪惡的「新自由主義者」殘酷的撙節緊縮政策,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想給人類帶來痛苦而產生的。它是資本主義體制壓力的結果。畢竟在資本主義下,利潤的增加(這畢竟是資本家的唯一目的),只有通過對工人階級更嚴厲和更強烈的壓迫剝削攻擊才能實現。
這並不像赫爾所說的那樣,是社民黨自1970年代來突然的「失去信心」。改良主義已陷入資本主義客觀限制的範圍內。今天,資本主義內部已沒有持久、有意義的改良空間。
領導層的責任
希腊群眾已看到改良主義局限性的痛苦現實。為應對自2012年來,對國家造成沉重打擊的危機。群眾進行了多年激烈抗爭。首先是公共廣場上的大規模靜坐示威,然後是工人階級投入鬥爭並領導多次罷工和大罷工。當未果時(尤其是由於工會領導層的阻撓),希腊群眾通過投票支持激左盟的反緊縮計劃,來表達他們的憤怒。
然而在短時間內,激左盟領導人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將國家置於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強加緊縮政策獨裁統治之下。這是對2015年7月公投的公開背叛,公投以壓倒性優勢拒絕了歐盟「三駕馬車」[11]強加的救助條件,61%的希腊人民投下「反對」票,因為歐盟的條件意味人民生活水平將會遭到破壞。資本主義及其在歐盟的忠實代表們違背了希腊人民的意願,強行將他們的議程通過。
我們看看對於這些挫敗,「左翼民粹主義者」們是如何評價的:
「激左盟鬥爭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只有在歐元區核心國家內部發生大規模抵制,才能強化激左盟的主張。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突破。將希腊經濟和政治的危機,轉化為整個歐盟的危機」。
再者:
「不幸的是,由於野蠻的歐盟以『金融政變』作為回應,迫使該黨接受三駕馬車的指令。激左盟未能實施其反緊縮方案」。
歐盟的「粗暴反應」,一點都不令人驚訝。然而齊普拉斯仍花了幾個月時間,會見教皇和歐洲各國政府的重要首腦,來巧妙的「論證」他們站在自己一邊。當他沒能「說服」他們時,他開始向三駕馬車投降,背叛了絕大多數被動員起來支持激進左盟反緊縮方案的希腊人民。當時作為激左盟中央委員會成員的IMT希腊支部同志,在選舉後立即寫下以下內容:
「不要再與歐洲資本及其機構的談判中抱有幻想」!我們的對手是躲在「三駕馬車」後的本地和外國資本主義利益集團,而不是他們的技術官僚雇員。我們唯一的真正盟友是歐洲工人階級! 激左盟現在必須呼吁一個全歐範圍的大規模群眾行動方案,使歐洲成為一個巨大的『太陽門』![2011-12年在西班牙各地爆發的憤怒者(indignados)運動]」
他們為希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國債和銀行的國有化。這些措施直指問題的核心:是在與資本主義決裂,和屈從於三駕馬車意願之間的選擇。
聲稱各種「不幸」的因素是導致激左盟失敗的罪魁禍首,而不是追究當領導的責任,是典型的改良主義思維。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領導層的作用也是決定性的。領導聽到群眾訴求後,有權提出和組織正確的下一步行動。群眾運動失敗後,仔細研究領導層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有正確的想法嗎,為什麼他們不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我們忽視這些問題,我們就是在掩蓋壞領導人。掩飾他們在失敗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結果是把失敗的責任推給戰鬥的群眾。
例如,弗里茨切對法國黃背心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甚至是對「阿拉伯之春」的失敗做出如下評價:
「[他們失敗了],因為潛在感興趣的人認為他們太學術了,或者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帳篷很好很可愛,但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更好。因為廣場上的占領者為了回去工作而放棄了,或者因為他們占據了沒有人打擾的地方。最後,也是因為如果他們擾亂了秩序,警察和軍隊就會把他們從廣場上趕走,毆打並監禁他們」[12]。
這是純粹的犬儒主義。埃及或突尼斯等國家的群眾,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克服宗教分歧,願為實現自由付出一切。再比如,黃背心運動不僅實現了最初設定的擊敗馬克龍累退式燃油稅上漲的目標,運動中的工人和青年們,在這之中對國家角色和資產階級「民主」的了解,比從那些「左翼敘事」書籍中學到的總和還要多。弗里茨切的觀點,對於那些不想與資本家對抗的政治家來說是非常方便的。對那些希望通過指責「社會缺乏霸權」來解釋自己叛徒式不作為和猶豫不決的人來說,這種觀點也是一種自我安慰。
我們需要革命的思想和革命實踐!
左翼敘事概念,是一個說明了哲學思想和政治實踐之間聯系的好例子。這些看似激進的「敘事」,實際上是對對資本主義不構成任何威脅的改良主義政治的掩飾。由於這一概念假設故事外沒現實。因此它導致了大量空談,如此而已。
新「左翼敘事」的支持者,想通過「談論」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問題,並為改良派政黨帶來選票,但他們很少提出具體的建議或要求。他們提出的少數要求也僅限於民主問題,或只是對社會福利國家能力的一廂情願而已。這種要求本身不一定是錯的。但他們並沒有強調,必須同資本家進行階級鬥爭才能實現這些。當這些措辭平淡的要求,在統治階級的真正反對下被擊碎時。也正如我們在激左盟中清楚看到的那樣。他們不是要求群眾背鍋,就是要求「新自由主義霸權」背鍋。
無論「左翼敘事」捍衛者是有意識地推廣、有宣揚其理論的哲學前提(就像墨菲那樣),還是無意識地接受這個概念,並認為其有助於在行動中為自己辯護,都不重要。革命者的任務,是揭示這種思想和由此產生的實踐,並提出解決資本主義苦難的真正辦法。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如此重視哲學問題的原因。
最後,思想是社會中階級利益的表達,是行動的指南。但我們必須問:這些思想是在幫助統治階級迷惑工人和左翼活動家?還是在幫助我們改變社會的?
讓我們睜開眼睛,面對現實。為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世界–為革命地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注釋
[1] 墨菲(Chantal Mouffe),《追求一種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倫敦和紐約,Verso,2018,P 12
[2] 同上,P. 35
[3] 同上,P. 13
[4] 弗里茨切(Julia Fritzsche),《深紅與激進色彩—追求新左翼敘事》(Tiefrot und Radikal Bunt: Fur eine neue linke Erzählung),漢堡, Edition Nautilus,2019,P 20
[5] 墨菲,《追求一種左翼民粹主義》, P. 49
[6] 弗里茨切,《深紅與激進色彩—追求新左翼敘事》,P. 177-8
[7] 墨菲,《追求一種左翼民粹主義》,P. 9
[8] 同上,P. 49
[9] 同上,P. 27
[10] 同上,P. 30-1
[11] 譯者注:「三駕馬車」(Troika)指的是在歐盟內部實際決策的三個機構:歐盟委員會、歐洲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
[12] 弗里茨切,《深紅與激進色彩—追求新左翼敘事》,P.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