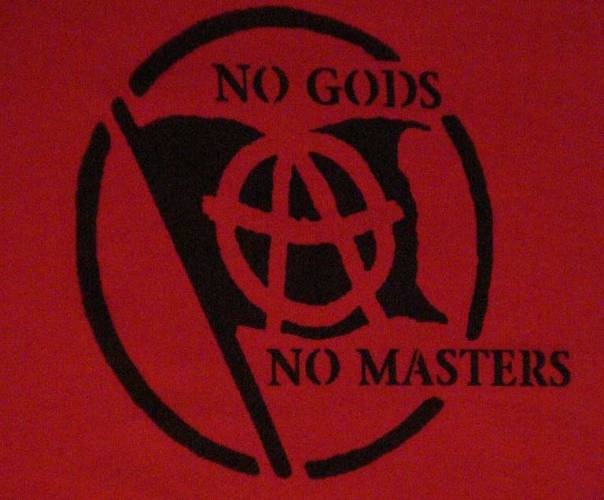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區別是什麼?為什麼是兩種理論?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它們的相對優點是什麼?這兩套理論中的哪一種,或兩者的思想的哪一種組合,是抗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最佳利器?這樣的質疑過程對於任何革命家來說都是必要的,因為這是對革命理論的把握和征服的嘗試。(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1年3月11日)
大多數無政府主義理論都表達了與馬克思主義相同的目標——建立一個無階級、無國家政府的社會。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對抗一切形式的壓迫和不平等的運動內是站在同一陣線的。而往往開始激進的人都會為此而同情這兩種理論。
我們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政府主義理論在解放人類的鬥爭中是一致的,但無政府主義則自相矛盾地拒絕理論,認為理論學習和發展是知識精英主義的幫凶,或只是某種的紙上談兵,而馬克思主義的特點是利用科學的方法和歷史分析的一切發展,使勞工階級可以理解社會,藉以改變社會。
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是理解社會上的不平等和壓迫,理解它們為什麼存在,它們從哪裡來,它們的作用是什麼,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克服它們。而理解它們不僅意味著描述它們,或僅斷言社會的階級劃分是不公正的,國家機器從根本上是壓迫性的,而是意味著要從物質上和歷史上解釋它們的存在。
階級和國家的起源
我們隨處可見極端不平等、苦難和國家壓迫的例子,以至於我們認為它們是理所當然的,似乎是一種天然的狀態。即使是最普通的個人,也生活在金錢力量屈辱的、無窮無盡的枷鎖之下,發現自己不得不圍繞著為別人賺錢的任務,按照老闆的時間表和指示安排自己的人生。
正如盧梭所言,人天生是自由的,然而他處處受枷鎖的束縛,也就是說,我們所受的束縛是人為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束縛是與我們自己根本平等的人的建構——資產階級沒有魔法或是超人的力量。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受苦呢?為什麼絕大多數人在少數人明顯的人為力量面前變得無能為力?社會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我們之所以被少數人利用,一定要基於某種條件。那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我們明白,階級鬥爭不是自己產生的,而是發生在更普遍的生存鬥爭的前提之下;用一個比較粗略的說法,它是人與自然界的鬥爭不可避免的表現。因為在我們被同胞奴役之前,我們就已經被一切強大的自然法則所支配。是的,每個人出生在這個世界上都是自由的,即沒有上帝預先安排的某種社會等級,但同時,每個人出生時都是大自然的囚徒。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是一種苦難的、有限的存在,我們在每一秒鐘的呼吸中,每一次胃部不自主的肌肉迫使我們尋找食物的時候,每一次我們弱小的本質使我們的身體因寒冷而顫抖的時候,都能感受到我們對自然的依賴。如果我們沒有如此迫切的物質需求,我們就不需要去向資本家乞討工作。所以,在我們了解社會缺乏自由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最基本的社會規律——物質環境決定意識。
歷史上發生過各種奇怪的轉變。在我們人類大部分的歷史內,沒有任何壓迫性的國家權威和階級剝削可言,然而不知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下卻產生了剝削和強制。而且,剝削和國家權威的形式也多次發生轉變,文化的相對水平也隨之發生變化。是什麼基本的機製或過程把這一切聯繫在一起?是什麼共同的線索讓我們把它們都歸入同一個範疇:「社會」?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就是爭取勞動的經濟化,發展生產力(或有用的科技),使之為某個階級所掌握,作為與自然鬥爭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發展有用科技的直接目的,總是為了某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可以在與自然的鬥爭中保障自己。但是,這種科技在社會上的發展和使用,會產生計劃外的社會後果,改變社會的結構,使一些人的力量超過另一些人。控制生產力的人控制了社會。
我們已經說過,最初的社會形式缺乏剝削制度和國家機器,是從「自然」中直接產生的,它沒有有什麼正式的社會等級和指揮系統。生產力本來就很低,社會不可能有任何特權階層。雖然在這種條件下的生活無疑是艱難的,但社會內部一定是相對和諧的,因為每個人都必須以大致平等的方式「各盡所能」。但這種和諧僅存在於每個部落的地理勢力範圍內,在這個範圍之外存在著其他的部落。而且,隨著地理上分散的社群發展其生產力,他們也會擴大,並最終與其他類似社群接觸。他們之間的貿易會根據他們能夠生產的不同商品而發展起來,這種貿易被每個社群用來充實自己。雖然在每個社群內部,可能在生產方面有巨大的團結和合作,但社群之間一定很少或根本沒有。各個族群不會有興趣為了對方而生產,而是為了得到一些回報。於是,不僅各共同體之間會形成競爭和對立,而且各共同體的內部生活會愈發從由自身的生產需要主導轉為由與其他社群交換的需要主導。我們可以推測,在這一過程中參與度較高的人,如領導生產並與其他族群接觸的長者,具有優勢地位。此外,在這種地域分散、對立的情況下,一定會出現爭奪資源和控制土地的鬥爭。族群之間為征服土地和利用其他族群的勞動能力而進行的戰爭,就是從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這樣,為發展生產力而進行的共同體鬥爭就導致了共同體的解體,有利於階級的分化。
這就是階級和國家的物質、經濟基礎。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有一個爭論,即究竟是階級分化先產生,然後是以保護統治階級為任務的強制性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還是國家權力及其壓迫工具先發展起來並引起階級分化?有些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是這樣。但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即階級還是國家先產生的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形式和內容上的問題,即國家權力是根本性的,階級不平等只是前者的形式表現,其目的僅僅是維護國家權力(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或者說,一切政治權力、國家權威和強制力的真正內容和基礎是經濟階級關係,正如恩格斯在與(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杜林的論戰中所指出的那樣。
「即使我們暫且認為,杜林先生關於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歸結為人對人的奴役的說法是正確的,那我們還是遠未達到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發生了這樣的問題:魯濱遜為什麼要奴役星期五呢?單是為了取樂嗎?完全不是。相反地,我們看到,星期五“被迫作為奴隸或單純的工具去從事經濟的服役,而且也只是作為工具被養活”。魯濱遜奴役星期五,只不過是要星期五為魯濱遜做工。但是魯濱遜怎樣能夠從星期五的勞動中獲得好處呢?這只是因為星期五以他的勞動所生產的生活資料,多於魯濱遜為使他維持勞動能力而不得不給予他的東西…杜林先生為了證明暴力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而特意編造的天真的例子證明:暴力僅僅是手段,相反地,經濟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礎性”得多;在歷史上,關係的經濟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樣基礎性得多…用杜林先生的優雅詞彙來說,壓迫始終是“達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廣義的糊口目的),但是無論何時何地,它都不是什麼為“達到自己目的”而實行的政治分派…魯濱遜“手持利劍”把星期五變成自己的奴隸。但是魯濱遜為了做到這一點,除利劍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奴隸服役。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一,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一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二章)
那麼,國家權力並不是某種任意的、為了自己而存在的惡。它並不是純粹從自身獲得壓迫和不平等的消極屬性,而是產生於發展中的經濟不平等,並依附於後者來發揮作用。而國家對社會上所有的人的壓迫也並不平等,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資本家與國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他們卻覺得國家很能代表自己的利益。這是因為,歸根結底,國家的權力來自於統治的經濟階級,國家為他們服務,保護他們的財產,總體上維護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
由此可見,有兩件事值得我們注意。如果一個階級能夠掌握經濟權力,那麼它原則上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國家機器,而不是成為國家機器的犧牲品,因為國家權力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關係。如果國家機器是用來鎮壓其他階級的工具,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能夠同意勞工階級領導的革命將面臨資產階級積極的、有組織的反對(這是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承認的事實),那麼勞工階級就可以而且必須掌握這種國家權力,即組織自己的強制機器來保衛自己的革命不受反革命的影響。只要勞工階級能夠通過民主的工人委員會集體地、民主地管理和發展經濟,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那麼只要他們需要國家機器,他們就可以保持對國家機器的控制。對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來說,代議制作為一種政治形式本身就包含著問題的種子,或者說是問題的根源。他們說,每個人不可能被真正的代表,代議士們總是會濫用他們的地位。但問題不在於形式。我們說過,如果是這樣的話,資產階級將永遠受到自己的國家代表的壓迫。資產階級議會永遠不能代表「人民」的原因,不是因為代議制本身是假的,而是因為議會被那個控制經濟、媒體等等的階級所控制,而這個階級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並不一致。
這同樣適用於工人自己的組織。如果工會和工人政黨的領導層出賣勞工階級,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一個領導層,而是因為他們受到統治階級的巨大社會壓力,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支配著社會。解決這樣的問題,決不是要放棄工人運動中的領導概念,而是要對出賣資產階級的領導進行鬥爭。諷刺的是,無政府主義運動儘管宣稱對官僚制和領導權恨之入骨,但卻常常表現出對右翼領導者的迷信而忽視了勞工階級基層——他們往往只把工人政黨的墮落歸咎於官僚制的存在或參加議會,而忽視了官僚向右移的前提條件總是由於公會缺乏公開的階級鬥爭策略,缺乏來自基層的壓力。但是,除了勞工階級的群眾運動和在這些組織內進行革命思想的鬥爭之外,沒有別的補救辦法。這就是我們如何清除一個背叛工人的領導層,並以一個革命的領導層取而代之。如果在工人群眾組織中不進行這樣的鬥爭,那麼,這些組織的上層就不可避免地會與階級疏遠,並將試圖與資本家合作。
但是,工人國家和真正的革命勞工階級領導,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最終目標,我們也看到了無國家社會的必要性。只有當需要國家機器(階級鬥爭)的客觀條件消失了,沒有國家的社會才可能存在。換句話說,當勞工階級通過解散所有的階級,把人類團結在一個全球性的生產計劃中,在階級和國家之間不留下任何持久的物質對立,當生產達到這樣的水平,即工作週充分縮短,使所有人都可以參加教育和管理社會,那麼,強制和征服將沒有客觀作用,變得毫無價值。
領導的客觀作用
俄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擔心,如果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通過政治領導建立起來,並在全國或國際範圍內集中組織起來,那麼領導革命的知識精英就會把自己安插在社會其他成員之上,成為一個新的統治集團。反過來,對於這樣的社會來說,生產的複雜性意味著需要「技術官僚」來指導和規劃這個過程(假設是,這些工作對工人來說太複雜了,他們無法理清頭緒),他們也會對工人進行主宰。
「集體主義需要在工人協會內設立一些權威機構來衡量個人的表現,並相應地監督商品和服務的分配。因此……集體主義秩序包含著不平等和統治的種子。」 (保羅·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The Russian Anarchists),譯者自譯)
但是,蘊含著不平等和統治的種子的東西,並不是大規模而複雜的「集體主義」,而是已經存在的物質不平等和剝削,這就造成了階級社會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化,有些人可以奢侈地學習,而有些人則被告知要做什麼。正是由於階級剝削和長時間的工作,在我們的社會中,工人不能自己計劃和指導生產,一是因為資產階級生產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不能允許工人有控制私利的發言權,二是因為工人沒有時間去民主地計劃社會。克魯泡特金把整個問題說得頭頭是道,所以他的解決方案——地方化主義(localism)、聯邦制和「簡單」經濟,只會在小範圍內重新製造同樣的問題。只有全球化的經濟,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事實的全球分工,在全球範圍內和諧地計劃(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根本沒有計劃,而是充滿了地區性的不平衡和對立),才能解放勞工階級,讓普通人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只有它所創造的高生產力,以及其中的技術複雜性,才能縮短每週的工作時間,讓群眾參與進來,才能消除人與人之間、人與國家之間為爭奪工作崗位、控制資源等而進行的慘烈鬥爭。克魯泡特金最後其實是在藐視工人,暗示人民群眾沒有能力計劃經濟,而實際上,他們只是作為被剝削的工人,才無法計畫經濟。「技術官僚」之所以能夠凌駕於工人之上,是因為在一個以剝削勞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裡,工人被組織學習怎麼計畫經濟。通過經濟國有化來取消這種剝削,這個問題就可以被克服,事實上,這是克服這個問題的唯一途徑。
可以說,「地方化」在1917年後的俄國革命中確實直接發生過,而這恰恰是導致史達林主義的問題之一。
「(於1924年訪問蘇聯的英國工會代表團內的)一名工人代表報告,工人們一夜之間變成了『新的股東集團』。1918年初,一位布爾什維克的評論員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他寫道,(現在由他們控制的工廠裡的)工人認為工具和設備是『他們自己的財產』。掠奪和盜竊的情況並不少見……。個別工廠委員會派『推手』到各省購買燃料和原料,有時價格高得離譜。他們常常拒絕與其他最需要的工廠分享現有的供應品。」(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譯者自譯)

這又該怎麼解釋呢?難道在每個地方工廠內工人控制都是不可行的嗎?不,問題的真正癥結是:是1917年革命後經濟極度混亂和貧困,德國帝國主義奪取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工業的大部分。問題恰恰在於「地方化主義」。這幾組工人表面上的自治(實際上根本不是自治,而是在市場、金錢和他們空虛的肚子的牢牢控制之下),是在革命(革命也是被「地方化」的,因為它被孤立在俄國,因而資源匱乏)無法在一夜之間解決嚴峻的物質問題而產生的。史達林主義的粉碎性重壓不是由集中主義和經濟的複雜性來促成的,而是由經濟解體為地區性的對立、城鄉之間的對立來解釋的,正是因為同樣的貧困條件持續存在,舊沙皇官僚體系才會從中重新獲得控制權和特權。勞工階級革命者忙於為眼前的生存而鬥爭,或深陷內戰的水深火熱之中,因而無法集體和諧地規劃經濟。馬赫諾在俄國內戰期間在烏克蘭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是農村與城鎮之間對立的表現。當時的農村養不起城鎮,無法解決城鎮內發生的問題:
「馬赫諾領導的是一起農民運動, 所以在任何一個城市內都沒有強大的支持基礎。住在馬赫諾控制下的烏克蘭地區的大多數工人,不是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就是站在孟什維克一邊。以下例子說明馬赫諾對勞工階級的態度。當葉卡捷琳諾斯拉夫-西內爾尼科夫(Ekaterinoslav-Sinelnikovo)鐵道的鐵路工人和電報工人在白軍將領鄧尼金(Anton Denikin)的佔領下經歷了長期的飢餓,並仍在受苦受難時,他們要求馬赫諾付給他們工錢。他的回答是:『我們不像布爾什維克那樣養活你們,我們不需要鐵路,如果你們需要錢,就從那些需要你們的鐵路和電報的人那裡拿麵包吧。』在另一次事件中,他對布賴恩斯克(Briansk)的工人說:『由於工人們不願支持馬赫諾運動,並要求我支付裝甲車的修理費,我這就把這輛裝甲車拿走,不付任何費用。』」 (A. Kramer,「馬赫諾無政府主義者、喀琅施塔特和俄國農民在革命後俄國的地位」)
原始人類社群沒有階級和國家,並不是因為「自治」、「地方化主義」或簡單經濟,而實際上是由於他們內部的「集中主義」或物質條件要求的統一。大家必須共同努力才能生存。同樣,要去除克魯泡特金所言的,那些專橫地告訴工人生產和消費多少的技術官僚,就需要把生產發展到使這種指導的必要性消失的程度。
「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應當是人類的經濟力量發展到那樣的高度,使生產勞動不再是一種負擔,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經常都很豐富的生活用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監督,只靠教育、習慣和社會輿論來維持,好像現在一切富裕的家庭或“體面”的公寓裡那樣。」(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希望相反,在我們的社會中,政治領導對勞工階級來說是必要的。如果勞工階級有時間和興趣去集體發展革命理論,集體把握革命的必要性,從而立即組織革命,那麼政治領導就是多餘的,該被拋棄的東西。而馬克思和巴枯寧等著名理論家的存在,確實發揮了領導作用(不管他們喜歡與否),他們發展了理論,用它來教育運動,這就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政治領導並不是多餘的。有些無政府主義者申論,我們不由人領導,而是由思想領導。其實,這就說明了政治領導的客觀必然性是如何一直強行進入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只不過他們給它換了一個名字而已。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們自己通過發展理論來影響社會而充當領導,他們曾不同程度地使用過諸如勞工階級的「幫手」、勞工階級的「代言人」、革命的「探路者」、「工會中自覺的少數人」的必要性等概念,或者巴枯寧關於革命的有紀律的布蘭基主義「指揮部(Directorate)」的概念。他們使用這些術語,但沒有解釋為什麼它們是必要的,以及它們與政治領導的真正區別。為什麼勞工階級需要幫手、探路者、指揮部、發言人或有意識的少數人?這些人又會扮演什麼角色呢?而如果我們僅有一個「思想的領導」,那麼發展這些思想的人(因為這些思想並不是由整個勞工階級集體統一發展起來的),這些大概最能夠解釋這些思想,把這些思想在工會談判中提出來(畢竟工會談判畢竟不可能一下子讓整個勞工階級參與進來),這樣的人又是什麼呢?改變某種東西的名稱,並不意味著改變其本質。
每當無政府主義者發現自己在真正的革命運動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時,他們總是不得不以某種形式重新引入領導權或國家政府。馬赫諾的運動為了抵禦白軍反革命,「投票贊成『自願動員』,實際上意味著直接徵兵,因為所有身體健全的人在被徵召時都必須服役」。有了這樣的軍事權力,他們「把從鄰近貴族莊園沒收的牲畜和農具分配給每個公社」。換句話說,在馬赫諾的領導下,他們組織了一個鎮壓反革命和貴族的國家政府,只是這個國家是地方化的。是的﹐他們是從布爾什維克政府中自治的﹐但在他們的領土內沒有人能夠自治。此外﹐馬赫諾運動具有極大的政治性:
「新的委員會刺激(即領導)城鎮和鄉村的『自由』蘇維埃的選舉,即政黨成員被排除在蘇維埃之外(換句話說,這是馬赫諾黨的實際獨裁!)…權力的統治權牢牢地掌握在馬赫諾和他的指揮官手中…馬赫諾任命了主要官員」。(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譯者自譯)
我們陳述這些,並不是要抹黑馬赫諾的政權,而是要指出: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內戰中,客觀環境的壓迫性需要,迫使馬赫諾發揮政治和個人領導的作用。
工團無政府主義者提出,有絕大多數勞工階級參加的總罷工,足以推翻資本主義,而且更具有不需要黨的領導就能推翻資本主義的優勢。但是,總罷工的歷史卻告訴我們,情況並非如此——既因為總罷工本身不足以推翻資本主義(歷史上有多次發動過的總罷工,但資本主義仍然存在),也因為工會在其中確實有政治領導。不幸的是,這種領導很少有堅定的革命使命,而且往往會出賣總罷工。所以要求總罷工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政治鬥爭,反對改良派工會領導的思想。但歷史已經證明,這種鬥爭並不會純粹自動出現的,當然也不會自動成功。在總罷工中,一些有組織的政治團體必須提出:我們必須以罷工為跳板,推翻資本主義,使勞工階級能夠建設社會主義。而這樣的組織將因此而發揮領導作用。它的任務必須是贏得鬥爭的勝利,通過說服勞工階級的群眾相信它的思想是正確的、必要的,換句話說,它的任務就是領導勞工階級奪取政權,推翻資本主義。
對理論的排斥
如上所述,無政府主義有一種強烈拒絕把理論作為對社會的科學研究的傾向,因為他們把這與知識精英和清談混為一談。為此,他們傾向於把所有關於社會中的「歷史規律」和各階級的客觀作用的申論都看作是知識分子的江湖騙術,看作是一種理想主義(指把思想或理論放在社會之前或之上)的發明,用它迷惑群眾來接受我們的領導。
「『只有感情、激情和慾望已經並將促使人們採取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行為;只有在激情生活的領域,感情生活中,英雄和烈士才會汲取力量…我們不承認社會現象的必然性;我們對許多所謂社會學規律的科學價值持懷疑態度。』」(作者不詳,摘自俄國無政府主義雜誌《Burevestnik》上的文章,引自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
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必須要問——哪樣的激情?誰的激情?這些激情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幫助什麼工作?他們說的是一個俄國貴族與他情婦的激情,是一位沮喪的俄國知識分子激情地把炸彈扔進擁擠的咖啡館,還是一名罷工的工人的激情?又該如何利用這份激情來幫助革命而不是浪費它呢?只有在社會規律是任意發明的世界內,馬克思主義才會是理想主義的。但無政府主義者也有義務證明「馬克思主義是理想主義」的申論,而證明它的唯一途徑就是在社會上,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際歷史進行比較。僅僅因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他在大英圖書館裡想出來的,而不是在激情四射的街頭上想出來的,就宣布馬克思的理論對運動不利,是不夠的。遺憾的是,20世紀的歷史以及其內產生的工業化和群眾工人政黨,以及所有無政府主義趨勢的式微,都表明馬克思歸納出的法則並非是如此隨意、武斷的。
由於駁斥理論,許多無政府主義者訴諸於簡單地描述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問題,並提出解藥,如簡單地顛倒資本主義壓迫的名稱那樣膚淺:
「戈爾丁派(The Gordins,20世紀初俄國一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派系)提出了一種被他們稱為『泛無政府主義』的哲學,它為現代社會內被五種有害體制的五種被壓迫者開出了五種解方。他們解決國家和資本主義的方法,就是無政府和共產主義;然而,對其餘三個壓迫者的解救措施則更為新穎:『宇宙主義』(用以普遍消除民族迫害)、『女性人性主義』(用以解放婦女並給予她們人性)和『兒童主義』(用以把年輕人從『奴隸教育的惡習』中解放出來)。」(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是把持自己願景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很少注意迅速變化的世界的實際需要;他們一般避免對社會和經濟條件進行仔細分析。他們提出簡單的行動綱領,而不是複雜的意識形態。」 (阿夫里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不會研究所有這些社會問題的成因,而會把這些問題當作是任意的,要克服這些問題,只需要社會以某種方式集體認識到它是在某種任意的不公正下受苦,然後集體解放自己。政治思想如果說是複雜的(實際上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並不那麼複雜,也不那麼難以了解),之所以複雜,是因為社會本身極其複雜,歷史悠久,如果要按照我們的意願改變它,就需要認真細心關注它。
無政府主義者誤稱巴枯寧預言了史達林主義,他認為,如果革命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那麼革命將不可避免地淪為對勞工階級的專政。但由於巴枯寧缺乏理論和唯物主義、歷史分析,他實際上沒有理解他所痛恨的國家的物質基礎。他只是點出了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國家壓迫的確存在的事實,並得出了未來也可能再次存在的簡單結論,卻不明白為什麼。他的理論無法解釋史達林主義。同樣的,我可能今天目睹了一場暴風雨,並預測它在未來會再次出現,卻絲毫不知道造就暴風雨的成癮。一個停擺的鐘每天有兩次是「對」的,但我們不能用它來判斷時間。
在筆者執筆之際,利比亞的叛亂軍正在與一個反革命國家政府發動戰爭。但儘管這場運動具有明顯的國際影響和淵源,他們卻在孤立地進行鬥爭。在世界上缺乏一個有能力對此參與和提供革命援助的國際革命組織下,帝國主義現在已乘虛而入。但「西方」的干預只是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利比亞群眾的利益。因此,國際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有責任提供援助,這將符合利比亞人民的利益。這最終意味著帝國主義必須要在其核心內推翻,使利比亞人永遠不會再受到它的壓迫。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發動一場協調的、世界性的鬥爭,並將鬥爭進行到底。只有一個國際革命領導層,把全世界的工人召集起來,才能承擔這項任務。
巴枯寧申論:「只要政治權力存在,就永遠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我們則回應:「只要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主人和奴隸存在,就永遠有政治權力、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