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1991年至1992年分裂真相的一些澄清
(按:本文原文于2019年8月12日发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In Defence of Marxism)。 当时正值另一国际组织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爆发全球性的公开分裂。目前运作《卫马网》的组织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由于在1990年代被工国委官僚性地开除,认为有必要针对今次工国委的分裂和各方说词做出评论和分析,为任何诚心立志于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的有志之士们提供重要澄清。工国委当时的分裂在本文发表后已成定局。自称「工国委多数派」的人士随后于2020年2月5日对外宣布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此组织在东亚具有一个「中港台」支部,其旗下的分支分别为「社会主义行动(香港)」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台湾)」,并运作《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
近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随后简称英国社会党)总书记彼得.塔夫(Peter Taaffe)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内推动了一系列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分裂,如今在全世界的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尽管以塔夫为首的派系与另一方争吵不休,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围绕在「威望政治」的一场争端。「威望政治」是一种高度有害的政治趋势,它在革命组织中总是致命的。
当某人将自己的威望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威望政治与个人野心、自我拉抬和自大妄想的特质是息息相关的。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塔夫的特质。最初,这些特征通常没有被他身旁的人注意到。大部分从前曾在「战斗趋势」(Militant Tendency)[1]内认识塔夫的人,在当时都没有察觉这些特质的存在。但是,对于像笔者这样每天与他密切共事多年的人来说,这些特征逐渐变得明显。
不同于泰德.格兰特(Ted Grant)这样具有可观的才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塔夫是一位非常肤浅的思想家,完全没有自己产生的理念。他所表达的思想全都从格兰特那边来的。然而塔夫对格兰特的观感不是感激,而是嫉妒。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系统性地挖格兰特的墙角,不时地私下对他身旁的跟班们低声抱怨说,与格兰特共事是多么的「不可能」。
塔夫诉求建立一个由无条件对他唯命是从的支持者们所构成的组织,永远不会忤逆他。列宁曾经警告过布哈林:「如果你(只要求)服从,就会得到一批听话的蠢材。」这番话有如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墓志铭。在一段时期内,「战斗趋势」内部开始累积了一班子这样唯命是从的人。他们都是年轻生涩的仕途主义者,对政治理论问题一无所知,但对于个人升迁却是贪婪的。他们集结成了一个集团,并背着组织内所有民主产生的机构做出所有决定。
这些是工人国际委员会在1991年至1992年间分裂的真正基础。其余说法的纯属谎言。在分裂将近30年之后的今天,该是我们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时候了。
官僚领导
在1991年到1992年间工国委内部的最后一次大冲突中,我们亲身经历了塔夫及其官僚领导团队的欺凌、阴谋和卑鄙的手腕,当中包括诽谤、人格抹杀、骚扰反对派内的年轻女性成员、开除会籍、拒付全职成员的工资,以及许多其他被他们称为「民主流程」的流氓手段。这样的方法是来自史达林主义的学派。
塔夫在危机爆发多年前就已经对格兰特怀恨在心。他觉得自己被格兰特的能力掩盖著,让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的欣赏。塔夫在整个国际组织间也相当顾忌艾伦.伍兹(Alan Woods),并采取行动将他孤立起来。为了排挤伍兹,塔夫的支持者们通过向伍兹的妻子,当时也在国际中心工作的安娜(Ana Muñoz)施压。正是由于她不断受到这种旨在制造挫折感和破坏的骚扰,让安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并最终经历一场精神崩溃。这就是这个领导集团的行事作风。
安娜在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曾参与过地下革命工作。在极权体制下,她一度被警察拘捕,并在牢内惨遭毒打。但她却说,她在塔夫集团手下的经历要痛苦得多,因为她从未预料过,自己所谓的同志们,会以这种方式对待她。而在这场卑鄙的事件中扮演了最恶毒角色,也是塔夫最卑鄙的心腹之一,如今以科洛(Vincent Kolo)为笔名。他是工国委多数派内的主要人物。但是,对于任何能够容忍拥有如此「出色战绩」的人的国际组织,人们可以抱有怎样的信心呢?当他们系统性地掩盖领导者在这些事情中的可耻角色时,又有谁能相信这些同志们真的从过去汲取了教训?
塔夫成功地加强了他对英国支部的控制,并希望进一步掌控整个国际组织。塔夫排挤格兰特和伍兹的尝试,最终于1991年4月爆发。格兰特与伍兹两人对塔夫权威的公开挑战,使塔夫集团开始全面戒备,并加速了统治圈子的堕落。在暗中运作的所有事物此时都已充分发展。该集团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声望,并竭尽全力捍卫了这些利益和声望。结果,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战斗趋势」的创始人格兰特,以及自1960年加入的重要同志伍兹。他们的谣言工厂此刻开始全面运作。
实际上,危机是在组织的最高层之间爆发的,而基层的同志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在1991年4月国际书记委员会(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一次会议上,格兰特和伍兹指责塔夫在国际内部组织了一个集团。他们声称:
a)国际组织组织的最高层内存在一个集团,该集团在我们趋势组织的正式机构之外运作,并篡夺了各民主产生机构的职能。
b)通过这些季诺维也夫主义的行径,包括以某人对此集团忠诚度为基础来提拔其地位,对组织造成了巨大伤害。
c)他们系统性地保护某些人免于遭受批评,并隐瞒霸凌事件。
d)(他们)系统性地剔除了任何在党内提出批评,有独立思想或「持不同意见」,并阻挠此集团的手段及其运作的同志。
批斗大会
塔夫对此发起了反攻,希望利用他在英国支部中的统治地位,来抹黑格兰特和伍兹。这开启了一场全面大战。当年五月预定的欧洲学习营突然被取消,组织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他们需要时间来准备迎战。作战计划的第一部分,是让塔夫召开一次英国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用以谴责格兰特和伍兹,而该会议于1991年5月17日举行。塔夫在该会议上得到的热烈支持,将帮助他说服国际再度召开一次国际执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会议。
在那次英国支部中委会的「辩论」中,伍兹和格兰特提交的决议,总结了当时组织内的怪异气氛:
「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针对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这两位党龄加起来有八十余年的同志们所发起的抹黑运动。」
「我们特别驳斥对于伍兹和格兰特自行将讨论带到国际书记委之外的指控。实际上,在书记委结束后,塔夫立刻与沃尔什(Lynn Walsh)和迪金逊(Keith Dickinson)私下讨论了会议内容,随后这两人四处散布谎言,声称格兰特曾威胁要发动分裂。」
「我们还谴责伦敦地区书记,在过去三天中,他违反了先前各地区书记小组会议上周所表达的立场的文字和精神,持续利用伦敦的全职成员机构来开办反对格兰特和伍兹的派系会议。」
「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提出异议的同志们,受到了旨在抹黑和消音他们的诽谤。」
当时笔者是「战斗趋势」的全国组织者,但我支持伍兹和格兰特将英国组织的情况,描述为「不健康的领导」的指控。在被塔夫当成橡皮图章的中委会会议上,同志们都被施压来遵循他的路线。中委会表决驳回集团形成的指控,仅有格兰特和伍兹反对这项驳回,而笔者本人则是弃权。
伍兹和格兰特被迫要撰文来反击这些攻击,以揭发整个领导层,这些文献我们近来也有重新发表。这份「罪行」则让他们遭到另一波恶意攻击和谴责。反对组织高层的官僚集团的斗争,很快被卷入了「战斗趋势」是否应「公开转向」(the “Open Turn”)[2]的辩论中,以及组织是否该脱离工党,并从苏格兰开始,建立一个公开的独立组织,。

这些斗争随后也渗入了关于是否应以「真正工党」(“Real Labour”)的名义,在1991年夏季沃尔顿(Walton)选举内与工党角逐。在一个健康的组织中,这种分歧本来可以透过辩论和正常方式处理,而无需诉诸官僚主义式的威胁、报复或镇压。那些恶劣手段对我们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塔夫派系正是使用了这些方法。对总书记(塔夫)来说,笔者对沃尔顿选举和「公开转向」的反对立场,决定了我的命运。作为英国支部执行委员和全国组织者,塔夫及其手下们将我视为「叛徒」,因此随后给了我「特殊待遇」。
当笔者准备前往沃尔顿时,我的家人不幸罹患严重疾病,尤其是我的儿子,那时他还是个婴儿。领导层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因我的缺席而对我施加人身攻击。我的那次缺席,以及其他他们所发明的「过错」,包括「严重不当行为」,都一起被包装成当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题,而伍兹将那次中委会比喻成作家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1984年》中的「批斗大会」(the “hate session”)。在歇斯底里的猎巫氛围中,我遭到了残酷的责骂和诽谤。很明显的,中委会委员们都事先被安排好来率领这些攻击。
作为回应,格兰特做了他一生中最短的讲话。他起身走到前头,胳膊下夹着报纸,说道:
「你们做的一切,我以前都看过。这是希利主义、季诺维也夫主义、史达林主义。用这些手段,你们什么都建立不起来。用这些手段,你们现在有的所有设备、印刷机、办公室等都会付之一炬。」
语毕,他在一批震惊的听众前坐了下来。但是塔夫政权决心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以42票对2票通过了对我个人的谴责动议。一名同志被指派来「跟监」我,而我所有的地方责任都被取消了。
肮脏的把戏
那时,英国支部有大约200名全职成员,其中100名在全国中心内工作。他们全数被动员起来「保卫组织,反对攻击」,亦即打倒反对派。有少数人鼓起勇气拒绝参与这个肮脏的权力游戏。全国中心内也有少数反对派的同志,其中一名当时正在休产假。我们立即被多数派孤立起来,几乎没有人愿意和我们说话,连一声「你好」都没有。即使是最新的全职成员,也被教导要跟其他人一起和我们作对,借此来赢得声望。
反对派的全职同志不时遭到骚扰。而那些抵抗这些骚扰的同志们,则会被移送执行委员会前被要求自我检讨,并受到纪律处分的威胁。我们被剥夺了所有职责,有人也直接表明他们不再能相信我们。但是我们在被剥夺职责后,又被谴责为渎职!这些把戏开始在整个组织内蔓延。我们在少数派经常在执委会和中委会上,遭到不信任票谴责。这样的做法成了一种仪式。即使是个别部门,例如财务、印刷编辑部门,也都在笔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我一致通过「谴责」动议。讽刺的是,当时正是我们要求工党,为我们被开除党籍的同志们维护程序正义的时候。
同情反对派的年轻女性全职成员哈里森(Stephanie Harrison),由于无法忍受她被骚扰的程度而于8月初辞职。她写道:
「我确实有理由感到被骚扰。整个组织,特别是全国中心的气氛恶化,领导同志们用相当下流的方式迫害他人。任何具有不同观点或意见的同志,都会自动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一部分,或者是支持该派系的。我看到领导同志们对这些同志都施予某种个人骚扰。」
这种有毒的气氛,是塔夫和他的领导集团系统性地培养出来的。反对派全职人员甚至被免去了夜班,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安全隐患」。隶属「多数派」的全职成员,都被鼓励去监视反对派成员的活动并上报领导。反对派同志的电话通讯纪录,甚至时常被多数派列印出来研究我们在和谁交谈。我们在塔夫秘书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份格兰特的电话通讯的纪录。当然,一般成员对这一切完全不知情,因为他们若听到这些手段势必会感到非常震惊。因此基层完全被蒙在鼓里。
史达林主义的手段被应用在地方各分会上。反对派为多数的各分会,都被强行关闭或与其他分会「合并」。任何被视为有同情反对派嫌疑的成员被一一列出,而这些人则经常被灌输关于反对派领导人的谎言和八卦。这样做如果不能说服他们变节,至少可以锐减他们的士气。反对派的支持者因不断被抓去「讨论」而疲惫不堪。在伯明翰市的一位同志,他被迫与多数派中委会成员们进行了一共17个小时的「讨论」。这些行为导致了一整阶层的同志们愤而退出组织。
塔夫的胜利不是他理念的胜利,而是他官僚机器的胜利。没有「民主」辩论,只是试图粉碎反对派。过去我们趋势组织把持着干净的旗帜,而完全拒绝了这种恶劣方法。现在,它们已成为塔夫政权下的普遍手段。在9月的苏格兰总会上,来自佩斯利市的一位同志,亲自询问塔夫是否有解决这场组织内危机的办法时,他被告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少数派领导人公开并在书面上放弃他们(对多数派)的指控。」
多数派全职人员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捍卫自己的主张,且无需担心费用,但我们少数派的每项工作都受到严格限制,并不断受到挑战。他们想让我们隔离在全国中心内,让他们在地方有空间(施展他们的工作)。
最初,当整个组织就我们提出集团存在的指控做出讨论时,国际书记委的多数派制定了一条规则,即只有国际书记委员,才能就此议题在会议上发言。由于格兰特当时病了,只有伍兹可以到不同地区参与讨论,(要他一人参与所有分会)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任务。多数派借此达到了扼杀讨论的效果。
在「公开转向」争议中,多数派得以派遣代表到全国各地。而科特里尔(Dave Cotterill,利物浦分会)、麦库姆贝斯(Alan McCoombes,格拉斯哥分会)、瓦克(Nick Wrack)、劳伦斯(Soraya Lawrence),萨努瓦(Tony Saunois)和塔夫本人则代表「多数派」赴西班牙发言。但当反对派同意派遣布朗(Davy Brown)前往德国代表反对派参与仅仅一场辩论时,他就被拖到了执行委之前,并因「擅离职守」而被谴责,尽管他们已被适当告知布朗预先的行程。
反对派同志多次被限制出差,但多数派代表则可以参加各地的会议,并且同时「捍卫」两派的立场!
他们尤其对笔者的日常动作进行严密的监控,甚至连我的休假也受到审查。当然,没有其他执行委成员受到这种方式的监视,并且可以自由活动。我附上由迪金森草拟的对于笔者个人的「报告」影本,这份文件被以英国执行委的名义,寄给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以「供他们参考」。这是他们对反对派进行类似警察监视的范例:https://www.marxist.com/images/stories/other/Report_on_RS.pdf
全职成员们被用作打击反对派的重锤。许多人抵制这些行动的人,都显然付出了代价。组织内气氛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尤其是在全国中心内。我们要求检查委员会调查对反对派专职人员的恐吓指控。但这当然被拒绝了。
如何操纵会议
所谓的「公开转向」的辩论,与真正的辩论没有共同之处。在我自己的分会内,就像在许多其他分会一样,都有(多数派的人)开始公开挑衅,借此降低了分会的政治程度并毒化讨论。当然,部分这些听命扮演肮脏角色的人,在我们被开除不久后也经历灰心丧志而黯然离开组织。
塔夫在1991年11月的特别大会上,组织了自己的「压倒性多数」,在那场会议上,他利用全职成员向与会者施压而获得了93%的支持。与会的代表们本应是各分会内按得票比例选举出来的,这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正常程序,也是反对派所要求的行事准则。然而领导层则决定让各分会「自行决定」大会代表选举办法。当然,在98%的全职成员都支持多数派,而每个分会内都有一名全职成员的情况下,让各分会「自行决定」代表选举办法的后果也不难预料到。
在一个支持多数派的分会内的全职人员,会主张「赢者通吃」所有分会的大会代表席次。而在偏向支持少数派的分会内,全职人员则会主张比例制。结果,尽管反对派的确是少数,但大会代表的组成并没有代表组织内部真正的力量平衡。例如,反对派在伦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伦敦各分会选举出的43名大会代表中只有一人支持反对派!格兰特在得悉这些发展时相当震惊。「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说,「他(塔夫)居然这么诡计多端。他一定认为这就是政治的全部意义。这意味着他只是个粗浅的政客。」这句话简短扼要地概括了塔夫的整个人格。
预先安排好的会议动议出现在特别大会的议程上,而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的全职成员遭到了各式各样的谴责。例如,来自北希尔兹(North Shields)的一位代表做出以下总结:「我们要求执行委对这些执迷不悟的同志们做出停职停薪处分,直到他们愿意承诺会完全履行他们身为全职人员的职责为止。」
在塔夫领导集团的鼓励下,这些威胁变得司空见惯。(多数派)对政治分歧的排斥,反映在他们在大会上对反对派发言人们,来自台下的嘶吼、嘘声和嘲弄,包括对国际同志也受到这样的待遇。尽管大会召集了许多来自苏格兰的代表,但没有一个在苏格兰的反对派同志被允许参加讨论。也没有来自默西塞德郡的反对派同志被邀请就沃尔顿选举问题发言。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是事先布置好的。在历时七个小时的荒谬「公平辩论」中,只有四个反对派同志得以发言,其中两名需要提交决议案才得到发言权!
全职人员们被动员来控制投票结果。塔夫与所有缺乏安全感的人一样,需要证明他拥有「压倒性多数」支持。托洛茨基在《史达林评传》内揭示了类似的心理现象。史达林经常在选举中「产生」大约98到99%的「多数」,特别是在对抗左翼反对派的情况下。在最近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党大会中,塔夫只获得了84%的选票。年老的他手段大不如前了。
但不管是84%,还是之前的93%得票率,都没有办法救赎他。在反对派被驱逐之后,「战斗趋势」(后来的社会党)的情况每况愈下。1992年后,该组织经历了大规模崩解,失去了包括默西塞德郡和苏格兰等整个地区的势力。现在,塔夫派将要经历另一次更大的崩盘。
1991年大会之后,领导集团加强了对反对派的攻击。全国中心的气氛充满了毒雾。当我们来上班时,就被其他人避讳。我们被当成瘟神一般的对待。当然也被排除在所有会议之外。他们反锁了我们的办公室,拿走了我们的电脑、电话等,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不可能。他们还试图更改我们在组织银行帐户上的签名,明显为分裂做准备。但是我们拒绝顺从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上班」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毫无意义。1991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周,我们的出勤频率降低了。不久,我们收到我们被无偿解雇的通知。有些人得到当月的薪水,但也有人一毛都没拿到,尽管他们有孩子要照顾。威尔逊(Alastair Wilson)被迫寻求法律途径以收回他被扣押的工资。他威胁要把「战斗趋势」上告工业法庭来夺回他应得的薪水。在开庭之前,塔夫终于决定支付这笔钱,以避免整个组织蒙羞。
扣发工资也影响了国际中心的伍兹和安娜。由于他们都是全职人员,没有其他收入,薪资断流也造成了个人生活的困难。当他们被解雇时,他们在办公室里拥有的一些私人物品也很快就「消失了」。格兰特也遭遇了同样的待遇。
没有下限的塔夫,甚至一度扬言要停止向一名女性反对派全职成员支付产假补贴。 11月28日,正在休产假的琳达.道格拉斯(Linda Douglas)前往全国中心,希望讨论她日后重返全职工作的情况,却遭到威胁恐吓。琳达当时是会龄已有12年的成员,也做了八年半的全职工作,并且还担任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有史以来第一名黑人委员。
她的伴侣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琳达已经怀胎八个半月,预产期是一月份。我们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我们依靠自己作为全职人员的工资生存,我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组织。」
「两个月前,大家一致同意琳达应该休产假并领取产假补贴……但在11月28日,琳达和我本人照原先计划去全国中心索取组织已经欠琳达的工资,并订定她将要收到的产假补贴,以及她重新开始全职工作的日期。」
「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被瓦克(Nick Wrack)同志拦截,他要求我们到柯伦(Francis Curran)的办公室参加一场讨论。出席会议的有瓦克、柯伦和执行委员英厄姆(Brian Ingham)。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获悉,除非苏沃尔同志签署一系列辞去组织内职务的文件(而除非我们向苏沃尔施压让他就范),组织将不再支付琳达补贴。」
「他们准备提供的,只是截至11月30日积欠琳达的薪水,但在基本的产假补贴问题上,他们不仅不会支付,连讨论的余地也没有。 」
琳达在休产假时被解雇并开除会籍。少数派同志们为她积攒了一点钱,来帮助她和她的伴侣度过难关,但是我们的资源仍然非常薄弱。
「很多知情的人,当时都一声不吭」,琳达最近解释道。
「关于我的处境,有很多谎言在流传,但是只有一个人联络我来查证:西加尔(Robbie Seagal),我诚心祝福她。实际上,当时我不得不继续前进,从未真正反思过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当时发生太多事情了,难怪大家都受到这么大的创伤。」
「许多人拒绝相信我的故事。我随后被我的分会开除,尽管我当时才刚生了孩子而无法参加会议,也没有人支持我!」
「那时我并没有感到太沮丧!除了对于一些参与这些动作的『好友们』以外。」
在上述的情况中,这些「捍卫女权」的骗子们,充分展现他们愿意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
「腹背受敌心态」
同年11月29日,在迪金森的督导下,组织管理部通过一项递交执行委的决议案。它提议:
「立即停职隶属少数派的所有全职人员,但保留他们向中央委员会上诉的权利。在停职期间,除非有中央委员陪同,否则他们无权进入全国中心,或者我们组织拥有的任何其他办公室。中委会应立即开会调查停职情况。如果中委会认定少数派全职人员在大会后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那组织应立即停止支付他们的薪水,并不再将他们视为全职人员。」
一种「腹背受敌心态」俨然被树立在全国中心内,作为加深骚扰反对派的手段。当我试图从全国中心带回我的书本(这些是我的个人财产)时,我却被阻止了。11月25日,执行委发布了一份通函,指出任何人未经事先同意,都不得从办公室内带走个人财产。我拥有的几百本书都被一一搜查,以防我试图将文献走私到外部。两位执行委员狄金森和瓦克轮流搜查每页,逐卷查找可疑的东西。这起像警方稽查一样的行动,花费了大量时间。当我把书本从办公室一箱箱搬到外面时,我不得不经过大约15到20名全职成员的纠察队,他们站在中心出口附近,希望借此恫吓我。通常在周六早上,只有两名全职员工会在前台执勤。我搬东西的那天,却有大批人站在那监视我。恐吓是塔夫囊中的关键手段,而这个「欢迎大会」势必是他组织的。这是多数派领导人暴行的典型表现。
为了进一步挑衅,塔夫总书记建议印刷部,将反对派全职成员布朗和威尔逊调到那里,并应该在那里让他们「做最卑微的工作,直到他们离开为止」。
12月2日星期一,执行委召开了一场会议来讨论反对派人士的「工作绩效」,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寄了以下的信:
执行委员会日前已开会讨论了您在全国中心内的缺席记录,以及您作为全职人员,却持续未能履行职责情况。
我们要求您回答以下问题:
1,请您解释您为何持续不来全国中心上班?
2,请您解释您为何没有联络我们来报备您的缺席?
3,您是否会坚决否认自己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一直在其他的场所内工作?
4,您是否认为您在抵制全国中心并且仅从事派系活动时,仍应继续获得薪资?
5,您今天离开全国中心的原因是什么(1991年12月2日),您从事了什么活动呢?狄金森,谨此代表执行委员会。
尽管我们做出了完整的答复,但执行委员会却仍决定需要在12月11日以类似的方式再次发送信函,要求我们对相同和其他问题做出回应。这是为他们日后「按规则」解雇我们借口铺路。

当格兰特于12月3日前往全国中心,为他的秘书威尔逊所遭到的待遇申诉时,执行委多数派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作为一次伏击:格兰特反而遭到他们盘问。他们随后在下周将此次盘问的纪录发函致所有分会。这再次显示了塔夫旗下官僚机器的本质:
塔夫:「那么,你不承认中委会的决定就是中委会做出的吗?」
格兰特:「不,那仅是多数派的决定。」
沃丁顿(Mike Waddington):「那么中委会已经不存在了吗?」
格兰特:「不,因为中委会(虽然)开会,但多数派在中委会开会前已经决定好一切。」
塔夫:「好,让我们澄清一下。对你来说,中委会并不存在。」
格兰特:「不。多数派会在中委会开会之前就已经做出所有决定。中委会只不过是橡皮图章。」
塔夫:「我再问一遍:你是说中委会不存在吗?」
格兰特:「我没那么说。」
塔夫:「明明就是。」
格兰特:「我没有这样说。」
塔夫:「你的供词都被录下来了。」
格兰特:「什么时候?」
塔夫:「全部都录在磁带上。」
格兰特:「我说了中委会不存在?」
塔夫:「是的。」
格兰特:「现在?」
塔夫:「我们问过你:你是说中委会不存在吗?」
格兰特:「我没那么说。」
(摘自于1991年12月10日发布的全国通信《总书记答格兰特》)
更多的挑衅
所有全国中心人员都被指示不准跟我们交谈。认识我们多年的同志们连一声「早安」都不说。这是一次系统性的、有组织的骚扰运动,旨在摧毁我们的意志并破坏我们的士气。虽然我们过的很辛苦,但他们终究未能得逞。
执行委不断通过新的「安全准则」决议,要求所有全职人员的个人背包在他们离开全国中心时,必须要接受搜查,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格兰特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显然是针对反对派全职成员的措施,而后来也的确是如此。当格兰特和威尔逊离开大楼时,他们的背包就会被搜查,但其他人就得以自由进出而不需要被搜身。他们随后阻扰(恼怒的)格兰特离开全国中心。格兰特解释道:「当我试着开门离开中心时,一名全职人员立即把门摔上并挡在我和门之间,肢体性地阻止我离开办公室。」
尽管他们在格兰特的背包中也没发现什么,但格兰特还是被迫等待「直到一名执委会委员到场并允许他离开为止。」这是一种胆小而无礼的举动。这并不是前台的全职人员的错,因为他只是在总书记的指示下行事。塔夫应为这种罪恶的行为负上全部责任。但是,我们拒绝臣服于这种希利才做得出来的霸凌和恐吓手段。
格兰特写道:「此刻,我感到自己无法前往全国中心,因为执行委多数派故意创造了对反对派的仇恨气氛,这意味着我的人身安全和个人尊严无法被受到保障。我进一步向其他同样遭到系统性骚扰的反对派同志们建议:他们应避免去全国中心,直到执行委多数派可以向我们保证他们会终止这些挑衅行为。」
反对派是如何被开除的
塔夫无法容忍与反对派提出的各个问题进行民主辩论。尽管格兰特遭到了各式诽谤,但他在组织内仍然享有极大的威信和敬重,而(在这个前提下同反对派进行辩论)塔夫对其后果没有信心。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迫将这场斗争带进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在当年6月的国际执行委会议中,有40%的委员支持关于塔夫运作集团的指控。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国际反对派,塔夫和他的同伙们将这场斗争视为一场决战。与今年工人国际委员会内的争端一样,他们那时愿意分裂整个国际组织。
然而,在整个国际组织内或世界大会上,进行一场民主辩论来决定事情,在那时已不可能发生。实际上,塔夫集团的第一个行动是取消五月的欧洲学习营。他们确保反对派失去平台,而大多数成员仍然处于无知状态的同时,伦敦的组织机器不断对大家输送谎言和诽谤。
诽谤如雪崩般地接踵而来。有人不断声称格兰特当时已经「老态龙钟」,用这样的言词形容在最困难的几年里从零开始建立和打造我们趋势组织的首席理论家,更是英国和国际组织世界大会被讨论和表决的各份主要综观文件的作者。许多先前曾与塔夫狼狈为奸的人,现在形成了当今的「反塔夫派」的领导层。
顺带一提,那些试图伪造历史的人至少应该要把日期弄清楚。对抗塔夫集团的斗争不是于1992年开始,而是在1991年4月开始的。反对派领导人格兰特、伍兹和笔者本人并没有离开「战斗趋势」和工人国际委员会,也没有闹分裂。1992年1月16日,我们在赫普斯科特路(「战斗趋势」全国中心地址)的一次会议上,被指控「在党内建党」而遭到开除。该决定在1月20日的中委会紧急会议上获得批准。这从而开始了组织内部的大肃清。

让我们清楚地声明:当时是塔夫的派系主动拆裂了工人国际委员会。
1991年圣诞节前几天,塔夫派以挂号信通知我本人和另外两名全职成员:我们已被停职。一月份,笔者、格兰特和伍兹被传唤到执行委面前。他们并以一名匿名告密者提供的「证据」将我们开除。这位「吹哨人」是组织机器派进反对派,来收集可以我们被驱逐的证据的,完全符合这帮人的作风。被窜改过的文件也被用来陷害我们。
这些被多数派称为「抛弃组织」的开除消息,被多数派送交给资产阶级新闻界。我们显然已经「将自己置于趋势组织之外」,这是一种不诚实的开除方法,被开除者没有上诉权。《战斗报》犬儒地报导: 「我们很遗憾格兰特以这种方式分裂」,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所有成员们,不管他们的意见如何,都必须面对这起先斩后奏的发展。
在被开除的那天,花了数十年时间建立这个趋势组织的同志们,被禁止进入全国中心,并在中心后门前等著被开除。塔夫集团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小气、仇恨和挑衅态度。格兰特,作为一位78岁的老人,以及这个趋势团体的创始人,居然被前台人员禁止使用洗手间,除非他们得到塔夫亲自许可。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所谓组织中心令人作恶的本质。
随后,组织内部发生了肃清,反对派的同志们不是被开除,就是被逼走。
例如,伦敦兰贝斯区(Lambeth)的反对派同志费南德斯(Kevin Fernandes)收到兰贝斯分会委员会的一封信(日期为1992年1月30日),要求他参与一场会谈。该信的内容如下:
本分会委员会希望与作为我们分会中支持少数派的您进行面谈,给予您机会澄清您是否有参与建立或支持这个新出现的组织。这是给您一个与这个新组织及其支持者划清界线的机会。您将被问到以下一系列问题:
1,您准备好成为我们趋势组织的忠实支持者吗?
2,您会继续兜售我们组织的刊物吗?
3,您愿意支付我们组织定期的会费吗?
4,你会为我们组织募款吗?
5,你会为我们趋势组织招募新成员吗?
6,您会公开倡导我们趋势组织内多数派的政治主张吗?
7,您对当下这个新成立的组织有何看法?
8,在(这个新组织的)建立过程中您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有)?
9,您是否支持另外设置一份刊物?
10,您会兜售(上述这样的另类)刊物吗?
11,您会为(如此另类的刊物)提供财务支持吗?
12,您会参加(上述)新组织的内部会议吗?本分会委员会不会驱逐您。您给出的答案,将让分会委员会得以确定您是否离开了本趋势组织。本分会委员会将相应地向整个分会报告。
这种麦卡锡式的侦办手段遍布全国。腐化已经完成。到目前为止,塔夫和他的助手们都牢牢地站在上风。
其实,(在此肃清行动中)最狂热和最恶毒的猎巫人,是名为特隆(John Throne)的爱尔兰人[3]。如今,他否认了这些过去(他们不都这样吗?),但当时在场的人不会苟同他虚伪的否认。后来,这位曾在反对派内被称为「笑里藏刀」的同志,在被塔夫利用来攻击和驱逐格兰特及其支持者后,却反而被塔夫背叛,自食其果。这起开除案反而是非常正当的。
以往,(塔夫)集团都在暗中运作。现在,他们官僚主义的手段公诸于世。塔夫只不过是一个粗浅的政客,精确地反映了整个组织机器的观点。他们不断地称自己为「多数」,这个称谓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正确。这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人不能接受自己身为少数。他们忘记了,捍卫自己思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涯内绝大部分都是少数派。而列宁,更别说我们运动的创始人托洛茨基,也是如此。
当然,塔夫派无法澄清关于我们被驱逐的真相。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被视为「将自己置于组织之外」,这是塔夫在驱逐人时的法宝,剥夺了任何被开除的反对派任何上诉权。如今这种说法是否听起来有点耳熟?是的,这就是如今他们驱逐他们爱尔兰支部与其他同志所使用的肮脏手段。
(今天受到同样待遇的人)真的对此像空穴来风一般感到惊讶吗?当然,这已经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由是完全相同的集团,由或多或少由同一个人领导的一批人主导的。唯一的区别是,这些方法对今天被赶出去的人来说,在那时似乎恰当,但今天他们变成受害者时,就变得不可容忍了!
国王的新衣
在伊索寓言里面,有则故事提到了一只爱膨风的青蛙,借此吹嘘他跟一头牛一样壮大。众所周知,青蛙最终走到了不幸的尽头。在将近三十年后,塔夫的泡沫已经完全破灭,露出了吹嘘背后总是存在的空洞。总书记大爷,诚如另一个悲惨的故事,最终成为穿着「新衣」的国王。
在英国,他们经常重复的「超过两千名成员」的宏伟宣告是虚构的。现实情况是,英国社会党已成为只有几百个活跃成员的式微势力。参加最近的全体会议的人数表明了这一点。其余的说辞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塔夫一直以来都是名表演家,急于吸引大批观众。麻烦的是,表演家没戏唱了。除了破坏自己的组织之外,他在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建树。更不用谈他有什么理论发展了,在这个领域内他从来没有什么值得贡献的东西:这三十年来,他们没有产生出任何值得注意的著作或文章。
由于他没有什么新鲜事要报告,因此他必须重申有关利物浦市议会和反人头税运动[4]的旧话(「你不知道吗?我们推翻了柴契尔夫人政权!」)。但是,在将这些古老的故事卖弄了四分之一世纪后,他发现它们不再有任何价值。这些故事已经像一张旧唱片一样乏善可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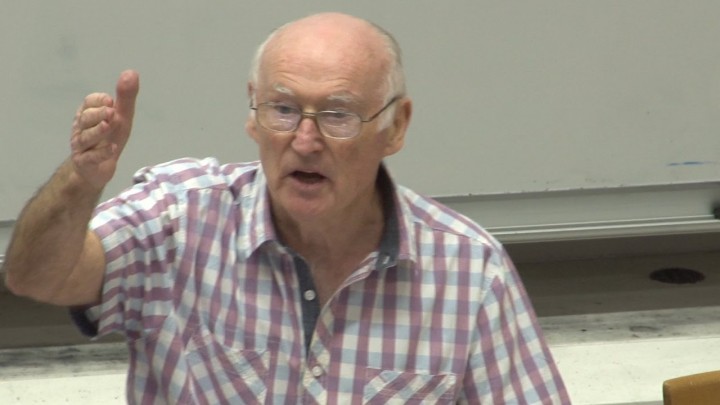
他试图透过工人国际委员会的爱尔兰和美国支部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国西雅图市选上的市议员和在爱尔兰选上的三名国会议员以及一些市议员),来掩盖自己的空虚。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增强这位日益缺乏安全感的总书记他那下降中的权威,反而对他构成了威胁。
塔夫以及英国社会党领导们,今天赫然「发现」这些「成果」是基于某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尽管这些路线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发展。无论如何,塔夫本人都非常知晓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直到最近,这种「罪行」都被悄悄地,方便地扫到了地毯下,因为担心它们会损害总书记的形象。
现在,塔夫和他的集团(如今工国委的少数派)已经方便地利用「机会主义」、「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es)等骂名,驱逐了工国委多数派。没错,少数派居然驱逐了多数派!多么创新的点子啊!但这并不新颖。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分裂。但是塔夫并不称其为分裂,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少数派。
这种本质上胆小和官僚主义的心态,与过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行径完全相反。恩格斯晚年写道:「马克思和我一生都是少数派,我们以身为少数派而感到自豪。」托洛茨基不惧怕反对史达林巨大的谋杀机器的力量,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全世界。但对塔夫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必须继续成为掌权的、不可动摇的、无所不能的总书记。永远占多数!
此外,控制工国委涉及一个原则问题: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原则。通过摆脱真正的多数派,塔夫派控制了工国委的资金以及他们前任同志们的网站。他也坚持使用(工国委)这个名字。然后,他驱逐了英国社会党内部的少数反对派。当然,根据塔夫的说法,被开除的人根本没有被开除,而只是「将自己置于组织之外」。英国社会党的威尔士书记亚历克.萨里夫斯(Alec Thraves)对他前同志们的「不朽名言」最可以概括这个情势:「再见,好自为之吧!」
在采取这种手段之前,塔夫已经从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中踢出了两名反对派成员,并试图扣留他们的工资。同样,支持「多数派」的两名工国委全职成员被排斥在外,而他们的工资也被扣留。在这些被驱逐的成员之中,有一人有一个新生儿要抚养。这些同志亲身经历了塔夫机器的全面攻势,系统地被排挤,然后毫不客气地被解职。
借此,少数派夺得了踢走多数派的能力。面对以前的同志们对多数派表现出的痛恨和仇视的强烈程度,导致多数派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的「背叛」罪行将会面对子弹的制裁!
一定要透过「吃一堑,长一智」才能习得教训吗?
工国委当前的危机不足为奇。唯一让人吃惊的是它没有更早出现。有了足够的物质资源,一个腐烂的政权可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像我们从希利派那所看到的一样[5]。但是最后,它还是崩溃了。这将是工国委的命运。
塔夫的方法与希利派可怕的行径如出一彻。一旦统治集团的声望受到威胁,他们就准备屈从于这种方法。他们表明了,他们与我们运动的真正方法和民主制度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1991到1992年的危机绝不是偶然的,当前工国委的危机也不是破坏它的根本原因。
该组织早已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所以当下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现在它已经死了,无法复活。如果我们要从这场戏码中获得正面的教训,首先需要对过去进行诚实的思考。没有这样的反思,就不能向前迈进。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话来说:「不向历史学习的人将注定要重蹈覆辙。」

如今工国委多数派都尝过了塔夫及其党羽的粗暴方法。现在,他们亢奋地抗议这些行径,并将发生的事情描述为「官僚政变」。很好。但是我们有权问他们:您学到了什么?那些今天声称坚持工国委的「民主传统」的人应该想到自己过去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们目前试图掩盖其真实历史的尝试,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不愿履行这一责任。
如今的工国委多数派并不想要给出一个诚实的回顾,而是希望美化过去,并冲洗自己的记录。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将这些官僚主义的方法,介绍为近来才发生的偏差。例如,在他们于2019年7月26日发表的题为《官僚政变不会阻止工国委多数派建立强大的革命社会主义国际》(Bureaucratic Coup Will Not Stop CWI Majority from Building a Strong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声明中,他们断言工国委以前是基于「民主传统」,而不是基于官僚集中制。
如此的童话故事是很方便的。但是童话故事是给小孩子听的,而工国委的成员们也非儿孩之辈。他们也想知道真相。但是,此派系的领导们给予他们的不是事实,而是粉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他们的说辞大不相同,因为许多工国委的老成员可以作证(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因为现在(「多数派」这些人)正试图通过散布各种荒谬的歪曲)塔夫的手段,在90年代得到了当今工国委多数派内的许多领导人物的全力支持,而这些人大声抱怨这些如今被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待遇。塔夫对待他们的方式只不过是让他们自食其果罢了。
多年来,科洛(Vincent Kolo)、韦斯特伦(Per-Ake Westerlund)、比尔(Eric Byl)、佩亚亚索斯(Andros Payiatsos)等人,以及他们在爱尔兰和美国的同伙,都是塔夫政权腐烂的同好。在1991年到1992年间,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对反对派)喊打喊杀。他们乐于参加这场令人恶心的奇观,将托洛茨基主义的干净旗帜拖入泥潭。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在系统性地重复关于格兰特、伍兹和当时反对派的谎言。如今,这些塔夫的受害者们,这个自称「工国委多数派」的领导们,正在歪曲历史,掩盖他们过去的角色,从捏造对格兰特的新诽谤开始。
例如,工国委的多数派声明解释道:
「在我们组织存在45年来,我们不得不在各个层面上与这种现象(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在不造成太大损害的情况下纠正它们。但是,有时为了保护工国委,需要有政治意识的基层成员干预,以反对堕落的中央领导。 1992年,当绝大多数工国委成员起义反对格兰特周围的领导人时,就是这种情况。不幸的是,今年围绕在塔夫周围的领导层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们的重点,6)
这句话完全将事实本末倒置了。把工国委基层形容成在「1992年…反对格兰特周围的领导人」的说法是完全捏造的。当时当然有一种「起义」,即塔夫机器的起义,用史达林主义学派下流的流氓手段来压制和粉碎反对派。签署上述声明的人(自称「临时委员会」)完全理解我们的论述,因为他们自己参与了这些行动,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当时可能很不情愿,多数还是全心全意的(塔夫)帮凶。
让我们建立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
当格兰特和伍兹谴责塔夫集团行为时,塔夫以对前两者宣战作出反应。他立即动员他机器的全部力量隔离并摧毁他们。这就是所谓「起义」的真正含义,这样的「起义」与拥护当今北韩平壤统治者们所发起的「群众运动」内涵不相上下。基层成员不可能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起义」。这一切发展让基层感到惊讶。但是塔夫的「干部们」已经准备好,等待着「起义」。这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战斗趋势」的反对派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国际间都被驱逐。这些同志们面对塔夫的异样手段和官僚堕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随后建立了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面对迫害,我们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则和遗产。面临逆境和克服了巨大的障碍,我们仍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毅基础上重建了这样的趋势组织。
我们在我们最近举办的国际学习营上庆祝了共产国际创建一百周年,来自世界各地四百名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参加,并让此活动成为巨大的成功。我们在此活动上募集了近136,000欧元(4,520,000余台币)的破纪录募款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国马趋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我们主张工国委和英国「战斗趋势」的初衷,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我们的创始人格兰特同志的思想为向导。
国马趋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可以宣称承袭这一伟大遗产的组织。敬请提防山寨版!
正如托洛茨基解释道:
「许多从第四国际桌子上偶然捡些面包屑来滋养一下的教派主义团体和派系,过著一种『独立』的组织生活,他们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胜利机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平心静气地让这些团体自生自灭。」
后记:
本文是对工国委1991-92年危机以及我们趋势同官僚集中制党政权的斗争的简短概述。我们将适时随后发布更多文献。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注释
[1]译注:英国「战斗趋势」(Militant Tendency)是由格兰特创建和提供理论领导的组织,于1980年代成为英国最大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其名为「趋势」(Tendency,亦有中文译者翻为「倾向」),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其不拘泥于组织形式,能够参与任何群众的团体、政党、运动,来在基层之内主导一个散播马克思主义理念的趋势,而次要原因则是形式上「战斗趋势」隶属于英国工党之内,形成一个党内派系。塔夫后来领导「战斗趋势」脱离工党而自行成立「英国社会党」(而后因苏格兰支部分裂而更名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以一个公开政党的姿态面对群众。我们组织认为,在我方势力还不够壮大之前,形成一个小党来等待群众加入不仅不会迎来新支持者,反而会丧失了组织能够主动参与群众组织和运动的灵活性。
[2]译注:「公开转向」是指当时主张「战斗趋势」公开脱离工党,自行成立公开政党的路线主张。
[3]译注:在本文原文发表后,特隆逝世于2019年九月底。
[4]译注:当保守党柴契尔政府企图于1989年颁布伤害劳工阶级利益的人头税(Poll Tax)时,「战斗趋势」率先成立「全英反人头税大联盟」,并成功组织百万余人抗税,并引领数十万人上街示威。这场成功的运动直接导致柴契尔下台。而此反人头税运动的全国组织者,正是本文作者苏沃尔。
[5]译注:希利(Gerry Healy)原为史达林主义英共成员,后被英国托派领袖Jock Haston说服加入托派。然而其政治行径仍然不失史达林主义色彩,专注于透过组织手法暗算和铲除异己。透过这样的手法,希利逐渐变成正在腐化的第四国际领袖之一,后创建「工人革命党」(Workers Revolution Party),但于1985年因被指控长期对女性党员进行性侵害而被自己建立的政党开除。
[6]译注:在此引用的声明「Bureaucratic coup will not stop CWI majority from building a strong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仍载于隶属于今「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组织中港台支部所运作的「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英文版下,却仍未发表相应的中文翻译。故本文译者需自译。原文如下:
In our 45 years of existence we have had to fight this phenomena at various levels, and mostly we were able to correct them without too much damage. However, at times it has required the intervention of a politically conscious membership against a degenerated central leadership to safeguard the CWI’s programme. This was the case when the big majority of the CWI rose up against the leadership around Ted Grant in 1992, and has unfortunately had to be the case with the leadership around Peter Taaffe this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