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达尔文和古尔德:进化论的革命
十年前,伟大的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因癌症在纽约去世。这是古尔德第二次面对这种可怕的疾病,这一次他被它打败了。古尔德的名字将永远与他的「间断均衡理论」联系在一起,该理论于 1977 年与他的同事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一起发表。(按:本文原文于2012年8月31日发表。译者:幻宏逸)
化石记录中的许多突破是真实的 – 古尔德
这一理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进化生物学:现代综合论(Modern Synthesis)(20世纪30年代以来进化生物学传统范式的名称)的总体背景被彻底打破。间断均衡理论并没有打破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核心——变异和自然选择——但它完全颠覆了我们理解自然历史的框架,从进化的节奏到自然选择所扮演的角色。
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物质是我们理解的最终基础,它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但变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量的缓慢积累,到了某个点,就会产生质的飞跃。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在物理和生物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中起作用。革命是罕见的事件,似乎不知从何而来,但实际上它们是由长期积累的、看似次要的事件所准备的突然飞跃。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方式意味着,为了有效地分析自然和人类历史,我们不能依赖对被割裂的事实们进行静态研究的方法。相反,我们必须立足于辩证法,理解任何单个事件的动态变化过程。
古尔德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了解并使用马克思主义,而他的敌人总是指责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打破了缓慢、渐进演变的传统观点,这与捍卫资本主义作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吻合。
主流理论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科学家无法将自己与社会上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隔离开来。思想的斗争总是反映出,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对立的社会利益和观点的冲突。因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然是如何演变的,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被迫打破传统的范式,这也是一种关于社会的隐含政治声明,这并非偶然。「间断平衡」理论借鉴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最重要的是,它极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它不仅对理解智人的生活,而且对理解地球上每一种生命形式的重要性。
《物种起源》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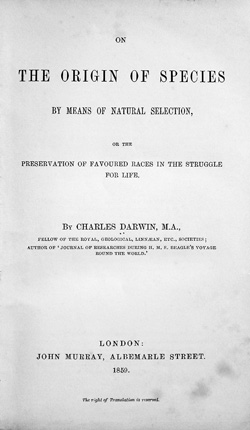 《物种起源》书籍的封面。//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物种起源》书籍的封面。//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这种生命观中自有一种伟大 ——查尔斯·达尔文
当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他的杰作《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the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时,狄德罗(Diderot)、莫佩尔图瓦(Maupertuis)、布冯(Buffon)等人已经多次尝试引入进化论的生命观,但都是基于推测。这些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观察和实验证据来支持进化论的观点。只有伟大的动物学家让-巴蒂斯特·德·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发展了一种适当的自然进化模型,其基础是有机物的使用和废弃,以及推动生命形式向前发展的形而上学的 “生命力”。
事实上,上帝在诞生之初就创造了一个物种繁多的世界,这一观点仍旧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阶梯论(Scala naturae),即上帝将所有动物和植物置于从低级到高级形式的固定尺度上的想法,是对生命多样性的公认解释。
1836 年,达尔文结束了「小猎犬」号为期5年的环球航行,回来后,他以送往伦敦的动植物收藏品而闻名,但更重要的是,他收集了用于发展自然选择理论的主要数据。即使只是肤浅地阅读他的著名笔记本,也能证明达尔文不是一步到位得出自然选择的想法,而是通过连续的逼近得出的。
1838 年,达尔文读了著名的《人口原理论》一文,马尔萨斯在书中解释说:「人口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以几何比例增长。生存只会以算术比率增加」,这是一条迫使动物和人类为生命而战的铁律。这个想法与认为工人和农民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是不自然的意识形态非常吻合。如果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因饥荒而遭受毁灭性打击,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又有什么意义呢?根据这一学派,是大自然注定了大多数人的死亡或饥饿,而不是社会。任何试图改变这个简单事实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虽然马尔萨斯的思想对英国统治阶级非常有用,但它也帮助达尔文制定了自然选择理论。事实上,达尔文在每一代产生的大量后代和达到生育年龄的少数成年人之间建立了一个密切的类比。该理论的完成,通过的是将自然用于选择个体的力量与驯化过程中人类的选择能力之间进行类比。
《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是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正如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所写:「生物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除非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达尔文理论的核心非常简单:一个种群的个体在形态、生理或行为特征方面存在自然差异;这些性状是可遗传的;具有促进繁殖特征的个体在几代人中得以保存。结果是整个人口的渐进进化。用达尔文的话来说:
「由于这种斗争,不管怎样轻微的、也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所发生的变异,只要在一个物种的一些个体同其他生物的、以及同生活的物理条件的无限复杂关系中多少有利于它们,这些变异就会使这样的个体保存下来,并且一般会遗传给后代。」[1]
这些结论不是来自推测,而是来自化石、植物学、动物学和其他领域的仔细观察和证据。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已被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观察所证实。生命形式的进化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最成熟和最重要的特征。
达尔文理论的核心非常简单,但该理论的后果是革命性的。如果说哥白尼和伽利略将人类从物质世界的中心移开,那么达尔文的理论则打破了人类作为生物世界顶峰的观念。此外,他的理论摒弃了任何最终论和目的论的自然观。进化背后没有「智能设计」,也没有神圣的计划。它只是发生了。是环境在个体随机变异的基础上默默地塑造了个体。适应是生命的结果,也就是在动植物的生存斗争中出现的。正如达尔文所写:
“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所谓同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普通已经绝灭的物种的直系后裔,正如任何一个物种的世所公认的变种乃是那个物种的后裔一样”(同上,绪论[2])。
因此,同一理论解释了两个看似矛盾的过程:一方面,一代又一代地保存最有利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即具有最有用的繁殖特征的个体),一个共同祖先的多样性激增。从大量后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不平衡中出现了生存斗争。这就是自然选择的来源。在这种观点中,物种的形成和灭绝之间具有辩证性的关系:具有较弱特征的物种注定要逐渐消失,来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释放环境中的空间。这个空间将被前者灭绝后出现的新物种所填补。在达尔文看来,灭绝是新兴物种存在的条件。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这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整个物种逐渐成为一个新物种。史蒂夫·古尔德(Steve Gould)最终将这种渐进而缓慢的进化观定义为「系统渐进主义」。
尽管它很伟大,但《起源》有两个主要弱点。首先,达尔文对物种是如何产生的保持模棱可的解释。事实上,达尔文解释说,通过自然选择选择的个体种群通过缓慢、持续、难以察觉的变化成为新物种。达尔文承认,小群体与种群的地理分离可以在创造新物种方面发挥作用,但只是微不足道。
这种渐进主义的进化论观受到生活各个领域渐进主义的一般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然不会突飞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s)是所有时代任何政治、社会、文化和科学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试图否认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在自然进化论中,渐进主义要求在化石记录中存在不间断的中间阶段,而这永远不会实现。达尔文本人将中间化石的缺乏归因于化石化过程中的困难,但我们所拥有的实际真实化石记录显示,物种在数百万年内没有变化。此外,变异之间有什么区别,新物种是如何产生的?新物种似乎在变异的海洋中消失了:一个明显的变异就是一个早
期的新物种。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范式具有革命性的特征,但也受到渐进主义自然历史观的意识形态强加的阻碍。
达尔文在下一版中修改了他的书,以回答这些批评。例如,我们可以阅读这些词来解释在自然选择的逐渐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眼睛的发育是如何形成的:
「理性告诉我,如果能够示明从简单而不完全的眼睛到复杂而完全的眼睛之间有无数各级存在,并且像实际情形那样地每级对于它的所有者都有用处;进而如果眼睛也像实际情形那样地曾经发生过变异,并且这些变异是能够遗传的;同时如果这些变异对于处在变化著的外界条件下的任何动物是有用的;那末,相信完善而复杂的眼睛能够由自然选择而形成的难点,虽然在我们想像中是难以克服的,却不能被认为能够颠覆我的学说。」(同上,第六章,理论上的困难[3])
再者:
「但我可以指出,有些最低级的生物,在它们体内并不能找到神经,也能够感光,因此,在它们原生质(sarcode)里有某些元素聚集起来」(同上,第六章)
第二个问题是,达尔文在建立他的理论时,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些特征是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的。这对于基于自然选择的理论至关重要,因为该理论的主要要素之一是个体之间存在变异以及将变异传递给下一代的可能性。没有这两点,就不可能有进化。
在《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几年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驯化下动植物的变异》的文章,其中他谈到了「临时学说泛生论」。根据这一理论,特征来自身体的每一个点,并积累在性腺中:后代只是混合父母双方特征的产物,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生殖细胞融合前随机遗传改造的产物。很明显,根据泛生的临时学说,随机出现的有利变异不能被后代完全继承,而是通过混合来稀释。自然选择将没有什么可保存的。
我们对遗传机制的理解基本上取决于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工作。今天,我们知道有精确的机制可以遗传特征。孟德尔的著作发表于1865年,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达尔文收到了孟德尔的著作,但他从未打开过它。但是,从孟德尔著作的出版来看,特别是随着1959年DNA结构的发现,《起源》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今天,在进化研究的计划中,仍有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它们都始于以自然选择为主导的达尔文进化论为核心。人们已经对最合适的科学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定义某一物种,某一系统发生学关系,用来理解化石记录,以及解释地球自然历史的节奏和模式,尤其是人类自然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今天这使我们可以说进化是一个事实。
如果没有进化论所代表的巨大飞跃,就不可能理解地球上所有门类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当然,除非有人相信一个高级生物创造了与今天完全相同的所有动物,并且同一个至高无上者埋葬了大量恐龙化石,只是为了与人类玩游戏!
自从《起源》出版以来,生物学和科学就变得不一样了。自然选择进化论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意义:通过多样性进行保护是自然界运转的辩证特征的绝妙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承认了这一理论的革命性含义,同时指出了它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局限性。
进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达尔文绝对是伟大的——恩格斯
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与旧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使用了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和功绩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之所以应该统治,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好、更聪明。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会变得更好,并改善整个社会。竞争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在中世纪,贵族之间的竞争虽然经常基于经济原因,但在意识形态上总是以道德为依据(骑士精神等)得到支持。现在,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竞争只是人类可以做得更好的手段,即变得富有和强大。古老的悲观主义哲学「人对同胞来说是狼」(人是狼)有了新的含义:即每个商人都有粉碎竞争对手的道德权利。通过这样做,他帮助人类进步。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为生命而斗争」的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而是相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点被强加给自然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进化是可以接受的,正如古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它确实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自然选择理论是把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学创造性地向生物学转换:自然的平衡和规则并不是由于外在的、更高(神)的控制,也不是由于规则性直接作用于所有生物,而是生物个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搏斗」[4]
因此,竞争产生了社会的逐步改善。对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宣传工具!适者生存的法则在丛林中和在社会中一样有效。
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这对于帮助新生的工人运动变得清晰是绝对必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发现,评估新思想的科学和政治意义。达尔文的新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达尔文的重要性和他的局限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他们甚至在达尔文之前就意识到进化论已经成为现实。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写道:
「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对个别人讲讲亚理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所生;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个人的性的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所以,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5]
毋庸置疑,当时的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激进的哲学家,对进化论的争论有着粗略的理解。但它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1859 年,《物种起源》出版了数百本,其中一本被恩格斯买下。在短短几天内,他就明白了科学已经永远改变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也能够立即发现达尔文主义的弱点。他写道: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6]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识到,达尔文在许多方面使用的方法在许多方面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序言中说,从他的观点来看:「……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被看作是自然历史的过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总结了他一生的朋友和同志的成就时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7]。达尔文则被马克思对他的思想的兴趣吓坏了,我们从他如何回复马克思、感谢他寄自己一本《资本论》[8]中可以看出。
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为达尔文辩护,反对他的批评者。但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达尔文主义的弱点被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例如,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像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9]。
至少可以说,达尔文不是一个激进分子,这一事实对他的理论是有害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进化论发展的桎梏。这在渐进主义中尤为明显。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渐进主义显然与进化论无关。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引用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位小有名气科学家的话,正是因为他拒绝了渐进主义:
「有一本很好的书,一旦我做好必要的摘记就寄给你(但是以寄还我作为条件,因为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的),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它的两个基本论点是:异种交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产生差别,而是产生种的典型的统一。反之,地质的构成(不光是它本身,而是作为主要的基础)造成差别。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达尔文不能解释的退化,在这里解释得很简单;同样,纯过渡类型迅速消失而种的发展缓慢的问题,也解释得很简单,因此,那些对达尔文有妨碍的古生物学上的空白,在这里是必然的。」[10]。
那些「专家」们,即专业的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要再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个想法,正如我们将在讨论古尔德时看到的那样。这并非偶然。渐进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可不小。进化论只有在被迫进入渐进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达尔文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后代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达尔文的理论与以前关于自然生命的观念完全决裂。我们将谈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特别重要的两点。首先是科学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11]
渐进主义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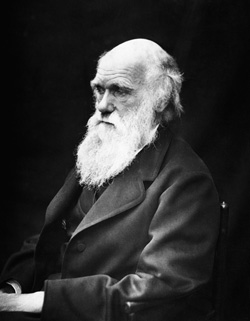 达尔文肖像。//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达尔文肖像。//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难以置信的复杂结构和行为并不是有意识努力的结果。不再需要上帝来理解生命的奇迹。一方面,这意味着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特殊品种,而是动物中的动物,例如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中指出,强调人类胚胎与猿类非常相似等。这意味着宗教永远失去了「解释」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信仰的牧师都憎恨达尔文。
然而,另一方面,达尔文主义被用来支撑资本主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起作用。因此,任何人为干预都是无用的。然而,这种换位是毫无根据的。所有动物都在利用进化赋予它们的工具努力求生。碰巧的是,为了让人类生存,我们的祖先发展了语言、意识、合作,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去计划。第一批人类开始与其他双足类人猿区分开来,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计划:他们计划狩猎,他们计划如何建造自己的住所,他们提前计划。为了生存,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在看到目标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正是人类特有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像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2]
因此,达尔文在驳斥某只可见的手是自然界变化的原因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注定要走向一个无政府社会,即资本主义。我们了解生产规律。这与其他动物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点是事物在变化。动物在变化,物种诞生又消失。这一方面也被引入社会分析,因为它有助于巩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进步制度的思想。然而,问题在于,如果社会在发展,没有什么是永恒的,那么资本主义也注定要失败。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进化论有着矛盾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提出了一种历史观念,即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进化甚至革命都是好的,但一旦资本主义建立起来,就不再是好事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规律] 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3]。
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进化的终结。问题是进化永无止境。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也允许人类生活进化,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对现实的细微之处进行了渐进的、难以察觉的修改,因为社会的基本支柱,即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都应该被视为永恒的。渐进论不是进化论的一个次要方面,一些科学家接受而另一些科学家则不接受。这是调和进化论和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古尔德理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是唯一曲解达尔文主义的人。关于「为生命而斗争」的思想,极左派哲学家潘内库克(Pannekoek)写道:「达尔文主义是不平等性的科学证据」。因此对他来说,达尔文主义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14]。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使他做如下说:「社会主义要废除竞争和生存斗争。但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整个有机世界的自然法则。这种斗争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有益的」。实际上,他所反对的是马尔萨斯,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顺便说一句,意识形态上为阶级不平等辩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可以追溯到著名的梅内尼奥·阿格里帕(Menenio Agrippa)的辩护,甚至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写就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相反,潘内库克没有一句话提到斗争也意味着阶级斗争,进化可能需要克服当今的自然和社会结构这一小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达尔文、赫胥黎等人试图利用进化论来获益——但他们却仍被他们那个时代的反动集团所憎恨。
至于渐进主义,社会党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接受了渐进主义,因为它符合他自己的改良主义社会进化观。这并非偶然。正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能在渐进主义的束缚下接受进化一样,改良主义也是如此,即资产阶级掌权在工人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反映。因此,慢慢地,渐渐地,在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就像一个物种转变为另一个物种一样。实际上,这不会发生在物种或社会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对渐进主义的科学反驳是多么重要,而古尔德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
范式的兴起
二十世纪主导自然科学的达尔文研究计划在被定义为「现代综合论」,这个名字暗示了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偶然变异和自然选择——与 1930年代出现的遗传种群知识的融合。
进化第一次通过对变异和遗传出现的机制的充分理解而得到丰富。在《物种起源》的出版与《现代综合》的兴起之间,生物学最终明白,父母双方的特征都是根据现代遗传学之父格雷戈尔·孟德尔阐述的精确数学定律来传递的。此机制的后果是巨大的:父母在其一生中形成的特征没有遗传,动植物的进化不是基于器官的使用或废弃从而简单适应环境需求的结果。相反,它证实了该机制的工作方式相反:环境选择的是那些随机产生的变异。
在此基础上,达尔文理论成为一种全能的自然选择范式:性状、适应性和行为都是自然选择直接塑造的。现代综合理论体现了这一范式: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苏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狄奥多西·多布占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和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是这一卓有成效的研究计划的主要人物,在 40 年的时间里,他们把进化论从一个可行的假说变成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科学事实。每一位科学家都在进化论的不同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费舍尔在他的著名著作《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The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中证明了进化的遗传基础可以扩展到那些似乎没有以孟德尔方式传播的特征,例如身高。事实上,在那之前,科学家们认为身高等特征并不像头发颜色等那样取决于特定的基因。费舍尔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编码身高的基因与其他基因一样,遵循相同的定律。我们可以预测基因的传输频率。这是现代综合论的第一次成功。
赖特通过发现遗传漂变发展了费舍尔的理论。这种机制通过自然选择得到丰富,并显示出随着世代的流逝,给定特征的随机出现(或消失)的可能性。在赖特看来,一个种群可以分为多个亚种群,这些亚种群通过遗传漂变,逐渐可以在新的地区定居,并因其它们具有「积极」的特征而被传播。换句话说,赖特的理论是现代综合中体现的缓慢而渐进的变化的预测数学模型。
伟大的遗传学家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在我们对物种的理解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他1937年写成的最著名的著作《物种起源的遗传学》(Genetic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进化生物学首次获得了物种的统一定义。这种观点被称为「物种的生物学定义」,它基于繁殖机制:物种是一组个体,每个个体都具有生育能力,并且在生殖上彼此隔离。用多布赞斯基的话来说:
「物种是最小的离散生物群,它们与其他群体的自由杂交被一些生理隔离机制所阻止。」[15]
不同物种的个体通过特定的隔离机制分开,如生殖器、配子、生育期、后代不育等的不相容性。然而,用多布赞斯基的话来说:
“(…)两个离散群体之间的杂交后代的产生可能受到不同个体之间性吸引的缺乏、生殖器官(生殖器或花器结构)的物理不兼容、性细胞结构或生理、交配季节和父母的生态差异的影响。如果杂种产生,它可能由于无法达到性成熟,或由于功能性配子的不产生而变得不育」(引文出处)。」(同上)
这一理论极大地强化了现代综合论的核心:即进化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正如达尔文多年前所表明的那样。基因和遗传学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数学基础,物种的形成方式相同:
「只有通过发展隔离机制,不同的生物体才能在同一地区共存,才能产生新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进化,或者分化和专业化,以利用自然经济中的不同『壁龛』。」(同上)
从这些思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综合的核心是将微观进化的机制外推到宏观进化的机制:换句话说,基因频率在世代中的逐渐变化,即新物种形成的基础,也是优等类群形成的基础,如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现代综合只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在化石记录中没有发现的一切,仅仅是因为化石化过程中的困难所致。
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于1944年出版的《进化中的节奏和模式》(Tempo and Mode in Evolution)是解释如何以渐进论诠释进化的主要著作。在这项工作中,辛普森总结了微观进化在宏观进化中的外推,并强调大多数进化是通过整个谱系的稳定和渐进的系统转变进行的。这种解释被命名为「前进进化」(anagenesis)或「种系渐变论」(phyletic gradualism)。
现代综合论是达尔文理论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它对物种的生物学定义在今天仍然有效,即使科学家正在提出和分析新的物种形成方式。然而,综合论中的第一个裂缝并不直接来自物种形成的遗传和生物学机制,而是来自古生物学数据和物种地理分布机制。
范式的第一个裂缝
在被普遍接受为正确之后,一个理论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质疑。现代综合论和间断平衡理论也是如此。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遗传学的发现加强了主导范式:基于逐渐变化的基因频率的进化范式得到了费舍尔和多布赞斯基的著作和分析的加强。
然而,随着胜利的到来,问题也随之而来,一种新的解释开始出现。在前面提到的辛普森速度和进化模式的著作中,虽然它是综合论古生物学的正统杰出著作,但它也提出了进化进行的速度和模式不是一回事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辛普森承认,化石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进化节奏。然而,这个想法多年来一直被主流科学家忽视。
最终,范式中第一个真正的裂缝是由鸟类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于 1963 年出版的《进化的动物物种》(Animal Species of Evolution)所代表的。迈尔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他是一位动物学家,一位热带鸟类学家,最重要的是,他是「异域种化理论」的发现者,该理论基于他作为鸟类学家多年收集的数据。这是我们考虑物种形成方式的一次革命。迈尔意识到了综合论的局限性:
「因此,遗传学家将进化简单地描述为种群中基因频率的变化,完全忽略了进化由两种同时但完全独立的适应和多样化现像组成的事实。」[16]
在迈尔看来,一个新物种是由一小部分种群与母种群在地理上分离而形成的:这个小的创始种群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定居,它可以更快地进化。经过足够的时间后,如果创始种群和母种群再次相遇,它们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用迈尔的话来说:
「我的理论的主要新颖之处在于,它声称最快速的进化变化并不像大多数遗传学家所说的那样,发生在广布的、人口众多的物种中,而是发生在小规模的创始种群中。」(同上)
再者:
「(…)我的结论是,在少数创始族群中,基因库的剧烈重组比其他种类的群体更容易完成」(同上)。
这是对辛普森阐述的系统渐进主义的隐含否定。异种物种形成并没有否定布赞斯基基于生殖隔离机制和种群通过互育结合的物种生物学概念,而是将其纳入了一种新的观点,从而引发了一场辩论:新物种是来自变化的种群还是来自小的创始族群?
间断平衡:生物学的革命
当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在1972年出版《间断平衡:系统渐进主义的替代方案》时,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迈尔的地理物种形成是正确的,那么对进化速度的后果是什么?这就像一颗炸弹在科学辩论中爆炸。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推翻了综合论的观点,将迈尔的地理物种形成应用于化石记录的解释。正如他们所解释的:
「异域(或地理)物种形成理论提出了对古生物学数据的不同解释。如果新物种在小型、外围、孤立的当地种群中非常迅速地出现,那么对不知不觉间逐渐形成的化石序列的巨大期望就是一种幻想。新物种不会在其祖先的区域内进化。」[17]
这种进化论观点没有遗漏任何环节。化石记录的中断反映了数代中的实际地理物种形成。化石记录还显示了创始种群在适应新环境后所处的停滞状态。正如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所强调的:
「异种物种形成的核心概念是,只有当一个小的本地种群在其亲本物种的地理范围的边缘被隔离时,新物种才会出现。这种本地群被称为『外围分离株』。如果分离机制进化,则外围分离株会发展成新物种,如果新形式在未来某个时间重新遇到其祖先,则该分离株将阻止基因流的重新启动。由于同种异体理论,新的化石物种并非起源于其祖先居住的地方「(同上)
在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的理论中,进化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正如化石记录清楚地记录的那样。这是阅读我们星球自然历史的一种新方式:换句话说,它为进化提供了新的节奏和新的模式。此外,间断平衡包括先前的生物物种和地理物种理论,不是通过完全否定它们,而是通过对这些概念应用辩证的观点。较小的创始人群体和以化石记录为标志的不同节奏:这些是这一革命性理论的组成部分。
用两位科学家的话说:
「总而言之,我们将同种异体物种形成的原则和预测与先前给出的相应的系统渐进主义陈述进行了对比:1)新物种通过谱系分裂而产生; 2)新物种发展迅速; 3)祖先形式的小亚群产生了新物种; 4)新物种起源于祖先物种地理范围的一小部分——在领域外围的孤立区域。这四种说法再次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后果:1)在任何包含祖先物种的地方部分,后代起源的化石记录应该包括两种形式之间的急剧形态断裂。断裂标志着祖先领域的迁移。(…) 2)化石记录中的许多中断是真实的:它们表达了进化发生的方式,而不是不完美记录的片段。」(同上)
在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经常被指责拒绝达尔文主义的核心。相反,他们为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间断平衡理论是基于自然选择的,因为地理物种形成和物种生物学理论是基于自然选择的。一小部分创始人群体发现自己所处的新条件(例如新环境中可能缺乏捕食者)促进了变化的节奏。
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解释说,化石记录实际上可以反映自然选择加速的情节以及物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许多年后,在进化机制的新发现的基础上,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核心从种群扩展到物种。事实上,间断平衡与现代综合法将微观进化外推到宏观进化是不相容的:从植物到哺乳动物的分类群形成需要不同的机制,而这些机制不能简化为对种群起作用的微观进化。这些机制包括自然选择,但它们不能归结为自然选择。它是一种基于涌现属性原理的多元进化观。
辩证法与科学
我们中的一个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学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这可能与我们的个人喜好也不无关系——古尔德
在短短几年内,间断平衡理论在古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中引发了许多争论,并被证明是对化石记录的有效解释。例如,对现代综合的传统解释为不同门类的发展分配了太多时间。古尔德讽刺地强调了这一点:
「因此,达勒姆(Durham)试图通过将物种首尾相连地堆叠在系统渐进主义的谱系中来估计后口动物共同祖先的年龄。他将6百万年指定为平均「物种持续时间」,并估计有100-600 个持续时间串在一条线上,以抵达在早寒武纪和中寒武纪棘皮动物的共同祖先。再往下看,他将后口动物的共同祖先置于『寒武纪开始前十多亿年』——这个年龄比现在对真核细胞起源的最慷慨的估计要早得多」[18]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所有科学家都有一种驱动他们工作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意识到,如果没有特定的社会概念,他们永远无法提出他们的理论。确实,多年来,在左翼知识分子普遍紧缩的情况下,古尔德减少了他的理论的政治后果。然而,凭借这一理论,这两位科学家以辩证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进化论观点。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总是讨论主流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 1981年,古尔德写了一部完全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杰作(《人的错误测量》)。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扭曲科学家的思想。但早在 1977 年,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就强调:
「林奈的那句名言——自然界中无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可能反映了一些生物学知识,但它也代表了欧洲统治者希望在一个已经受到根本性社会变革呼声攻击的社会中保持的秩序、和谐和连续性在生物学中的转化」(同上)
1977 年,他们直接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致敬,值得全文引用:
「卡尔·马克思非常钦佩达尔文,曾经说过《起源》包含着『我们所有观点在自然史上的基础』,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著名的信(1862 年)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像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我们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以任何方式诋毁达尔文,而只是指出,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也植根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认为渐进主义是文化背景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
「变化的另类概念在哲学上有着令人尊敬的渊源。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唯物主义背景下已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国家哲学』。这些变化规律连标点符号都是明确的,这符合人类社会革命变革的理论。恩格斯特别强调的一条定律认为,随着量变的缓慢积累,长期受到稳定体系的抵制,最终迫使其迅速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一种新的质量会突然出现(量变质变定律) 。缓慢加热水,最终转化为蒸汽;越来越压迫无产阶级,保证革命。」 (同上。)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角色
古尔德作为科学家的整个一生都花在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上,并用辩证法丰富了它们。在这里,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来论述他对科学的全部贡献,但我们想指出,他成功地揭露了自然的辩证性,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是通过以自然的具体方式发现这种特征。马克思批评拉萨尔作为理论家的糟糕结果,他说:「但是使他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像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间断均衡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成就,这种理论没有将辩证法强加于自然,而是诚实地得出结论,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理解进化论。
科学家无法将自己与社会隔离开来。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以一种虽然粗糙但却健康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存著,但他们很容易受到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显而易见:在阶级社会中,科学的控制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这涉及到对资金、教育计划、招聘和职业、信息和媒体的控制。最近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被用来谈论上帝(「上帝粒子的发现」),似乎这两件事有某种联系,这并非偶然。同样,基于基因频率渐变的进化论观点也被用来推动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切都是由基因决定的:社会差异、贫困、失业、文盲等等。富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是最适合统治的人,就像自然界的幸存者物种一样!
然而,虽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可以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而另一些人则接受现状,但也有一些思想家通过他们的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多年前所指出的,科学是以辩证的方式进行的。统治阶级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辩证法意味着自然界和社会的革命。间断均衡理论,从根本上重视突然的变化,即革命,本质上是对统治意识形态的直接攻击。对于那些试图淡化其重要性并诋毁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这是绝对清楚的。
革命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是罕见的事件,但它们标志着整个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对革命的分析是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地球、动物还是人类。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优点是理解这一点,并且不被革命吓倒。
多亏了他,我们对动物进化的了解有了巨大的飞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正是因为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勇敢的知识分子在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方面很重要。需要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来改变它。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参考书目
- 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
- 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什么是物种?》,《科学》(Scientia),1937年
-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间断平衡:系统渐进主义的替代方案》,Models in Paleobiology, 1972年
-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间断平衡:重新思考进化的速度和模式》,Paleobiology,1977年
-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熊猫的拇指》,1980
- 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反抗中的理性,1995
- 恩斯特迈尔,《物种进化或间断平衡》,载于《进化动力学》,1992 年
-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6年
-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
- 阿尔伯特索米特,史蒂文·A·彼得森,《进化动力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间断平衡辩论》,1992年
注释
[1]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3章:为生存而斗争,https://www.99csw.com/book/1131/32905.htm
[2] 达尔文,《物种起源》,绪论,https://www.99csw.com/book/1131/32902.htm
[3]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6章:理论上的困难,https://www.plob.org/article/2471.html
[4] 古尔德,《熊猫的拇指》,海南出版社,2024年1月,第二部分,达尔文的中间道路
[5]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4.htm#18
[6]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9/254.htm
[7]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 1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830317.htm
[8] 达尔文致马克思,1873 年 10 月。
[9]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 年 6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0/141.htm
[10]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8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1/124.htm
[11] 马克思致拉萨尔,1861 年 1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0/294.htm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 7 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raverman/braverman-1974book03.htm
[13] 马克思,原文出自《哲学的贫困》,译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07.htm
[14] 安东尼·潘涅库克,《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15] 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什么是物种?》,1937年
[16] 恩斯特·迈尔,《物种进化或间断平衡》,引自阿尔伯特·索米特和史蒂文·A·彼得森,《进化的动力学》,1992年。
[17]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间断平衡:系统渐进主义的替代方案》,1972年。
[18]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间断平衡:重新思考进化的速度和模式》,1977年。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9/1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