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經濟學派: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狂熱信徒
在20世紀初的動蕩年代,資本主義受到革命劇變的衝擊,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歐洲工人運動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一群維也納的知識分子也在企圖反擊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方面,他們試圖「反駁」馬克思理論核心的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他們試圖「證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理論上是不可行的。在本文中,亞當·布斯(Adam Booth)不僅回應了他們的論據,也描繪他們從這兩方面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意圖如何代表了從科學的唯物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方法的倒退。(譯者:Xinsuo)
在撰寫本文時,全球經濟正處於混亂和危機之中。需求劇烈波動、多年的長期投資不足以及肺炎流行引發的生產和流通困難等一系列易燃易爆因素混合物的結果。
一些專家預測,清除積壓、解決勞動力短缺、穩定物價還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與此同時,普通家庭面臨著食物和燃料等基本必需品的短缺,家庭的實際收入正遭到瘋狂的通貨膨脹的侵蝕。
尖銳的矛盾無處不在。例如,在英國,由於缺乏熟練的屠夫,10萬頭豬將被屠宰並作為廢物丟棄。換句話說,利潤導向的冷酷邏輯導致了大量動物無辜的死去,而超市貨架上卻是空蕩蕩的。
英國房地產市場上也有類似的惡心場景。數十萬套空置房屋被當作投機手段的同時,還有數以萬計的人露宿街頭,等待議會提供住宿的名單還很長,可怕的住房危機也來臨。
在全球範圍內,由於氣候問題,人類現在正面臨著生存危機。很明顯,資本主義正在毀滅地球。但大企業口袋裡的政客們對這場迫在眉睫的災難束手無策。
所有這些事情都揭穿了自由市場所謂的「高效」和「活力」,以及競爭的「嚴酷性」。他們共同揭示了,以利潤而不是需要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破產。也表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基於計劃經濟、公有制和工人專政的真正社會主義方案,。
面對這種無政府狀態和瘋狂現狀,不論是媒體還是網絡、街頭極端的自由市場主義分子,最近肯定要安靜一些了。
盡管如此,大學經濟學教科書中仍然存在關於市場高效的基本觀點,學生們接受「有效市場假說」的「填鴨式」教育。
按照這些「理論」來說,經濟不過是由一系列圖表、方程式和數學模型所構建的理想化系統,如果不是討厭的工會主義者要求提高工資;如果不是央行行長印制太多的錢,吹大經濟泡沫;如果不是政客們無恥的為自由貿易設置了壁壘,那麼這個系統就會處於完美的平衡與和諧之中。
實際上,這些想法與資本主義本身一樣古老。它們可以追溯到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 Baptiste Say,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法國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薩伊定律」,薩伊曾斷言供應能創造其本身的需求;每個賣家都會將買家帶到市場上。
這個所謂的「定律」的結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平衡,不應當阻礙和限制市場。只要有足夠長的時間,允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魔力,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從不去考慮社會後果和人力成本。
這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在過去幾十年裡雷打不動的堅持這一原則。
古典學派
現代自由意志主義者們其實很清楚自己的歷史,他們的理論根源來自於「奧地利學派」(The Austrian School),該學派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數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他的導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反過來,這些公開的反動派又宣揚自己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的真正繼承者,該學派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物而聞名。
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成長的。其中,古典經濟學便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古典經濟學派產生了許多試圖以科學方式理解經濟的思想家,他們希望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具有自身規律和動力的系統來研究。
雖然,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家們依靠抽像的力量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但他們沒有陷入與現實無關的理想數學「模型」,而這恰恰是今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思想家的特征。
古典經濟學家是推動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一份子。這場啟蒙運動中知識分子們以唯物主義思想為基礎,試圖用「理智」與「理性」為自然、社會中的現像找到答案。
斯密和李嘉圖等英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資本主義體制的重要問題,其中包括價值、貿易、工資、租金和勞動分工等概念,他們把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推向巔峰。
反過來,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為英國的資產階級創造和支配世界市場,推行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支持,深刻反映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堅持用科學的理論分析資本主義,有意識地延續了李嘉圖沒有完成的工作。也正因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是建立在對歷史和經濟的唯物主義分析之上的,而不是對社會空想而成的烏托邦藍圖。
然而,與李嘉圖不同的是,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代表的不是資產階級利益,而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理論武器。
馬克思從李嘉圖等優秀的古典經濟學家的假設出發,在《資本論》以及許多其他經濟學著作均展現了資本主義如何充滿矛盾,並且天生就容易發生危機。
馬克思運用這種方法,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理論,並得出其中隱含的邏輯結論,馬克思力圖「從理論上打擊資產階級,使之永遠無法從中恢復」[1]。
馬克思以一貫的唯物主義觀點在科學的基礎上證明並發展了斯密和李嘉圖的思想成果。他向人們揭示了資本主義如何依照古典經濟學已然發現的規律運轉,孕育著自我毀滅的種子。
因此,追隨李嘉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被迫退卻:放棄了古典學派的科學方法;回歸唯心主義,將資本主義神秘化。
正是如此,馬克思稱這些人為「庸俗」經濟學家。這些反動的思想家沒有試圖真正地解釋和理解資本主義體制,而是成為了它的「辯護士」。
維也納攻勢
到19世紀末,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開始遊行。大規模的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地儼然成立。1889年,第二國際被創始,致力於協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這些組織認同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思想,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統治階級察覺到工人運動興起的威脅,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威脅,由此開始了全面的意識形態反攻。他們的進攻中心來自奧地利,尤其是維也納大學。
維也納不僅是奧匈帝國的主要首都,也是一系列文化、知識和科學運動的發源地,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藝術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精神分析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城市的咖啡館中擦肩而過。
與此同時,維也納大學成了反動思想的溫床,是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主觀唯心主義溫床,這種唯心主義甚至在沙俄知識分子階層和社會主義運動中變得時髦。
因而,列寧認為有必要對馬赫及其擁躉發動尖銳的反擊,他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形式出色地達到這一目標,這場大論戰既暴露了主觀主義思想的貧瘠,又徹底的捍衛了唯物主義。
然而,馬赫的思想仍對後來的哲學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維也納學派所倡導的邏輯實證主義。這又進一步深刻的影響了奧地利思想家,比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他就明確地向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宣戰。
勞動價值論
在經濟學方面,資產階級的奧地利的攻勢是由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和他們的導師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等人物領導的,他們也受到維也納大學及其周邊地區盛行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
他們的第一槍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LTV)」,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解釋了商品(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貨物和服務)交換的基本價值規律,從而解釋了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
奧地利學派用自己的邊際效用理論(Marginal utility theory,MUT)來代替LTV。
MUT基於個人消費者偏好,而不是客觀的社會因素,是一個完全不科學的主觀主義「理論」。MUT是由歐洲各地的庸俗經濟學家同時期發展起來,其中包括英國的威廉·斯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法國/瑞士的萊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和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
MUT與LTV形成了鮮明的對比:LTV是唯物主義的理論,可以上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LTV解釋到,從本質上來說,正是在生產中付出的勞動和勞動時間使事物變得有價值。
勞動價值論的觀念被斯密和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接受和發展,形成了他們經濟理論的重要支柱。同樣的,馬克思也以LTV為基礎,同時賦予了它一種古典主義所欠缺的辯證深度。
斯密和李嘉圖的問題在於,盡管他們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尋求「理性」,但他們都被他們和啟蒙運動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所浸染。
他們試圖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系統來分析,並可以發現、理解和利用運動規律,這一點值得稱贊。但對他們來說,這個系統是一個簡單的機械系統。

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經濟只不過是個體間直接相互交換和勞動;如同,孤島上的孤獨男人,在自己的頭腦中比較各種生產任務的勞動時間。
在這種「魯濱遜漂流記」式的模型中,個體既是唯一的生產者,也是唯一的消費者。在考察交換規律的時候,它又簡單的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視為物物交換的放大版。
例如,我們想像中的孤島難民可能會花四個小時來砍樹制造木筏,再花四個小時可以收獲一百個椰子;他們因此得出結論,一只木筏的價值相當於一百個椰子。
這種抽像的假設情景很顯然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相去甚遠大相徑庭。我們生存的經濟體系不是由孤立的個體而組成的,而是由各個階級組成——必須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來維持生計的工人,以及雇佣和剝削工人以獲取利潤的資本家。
同樣的,貿易和交換不是以物易物的形式直接發生在個體生產者之間,而是通過企業和消費者;也就是說,通過貨幣和市場的非個人交易。當下則是越來越多地利用亞馬遜等巨型壟斷企業提供的平台交易。
馬克思和價值
正因如此,馬克思把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前提,即勞動創造價值勞動是價值的源泉,進一步發展。
他解釋說,使商品有價值的不是個人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一定的技術和歷史條件下,為市場生產商品所需的平均時間。
這種洞見反過來又成為馬克思剝削理論的基礎,從而揭開了古典經濟學家所未能解決的利潤來源之謎。
總之,馬克思概述了資本家的利潤來自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就是工人階級的無償勞動。
馬克思說,資本家從工人那裡購買的不是他們的勞動,而是他們的勞動力(在一定時間能勞動的能力),他們獲得工資作為補償。
然而,在勞動中,工人生產的價值超過了工資形式所補償的價值;換句話說,工人階級只需要一小段時間的勞動,就能生產出維持和進行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商品。
除開工人階級再生產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外,工作日中剩下的時間就構成了剩餘勞動時間,從而形成了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餘價值。
因此,價值規律是一切資本主義表像背後的動因:驅使資本家們增加勞動強度,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驅使資本家們超越競爭對手投資技術來推動提高生產率,以超越競爭對手攫取超額利潤;以及造成積累、擴張和增長的內在動力。
最重要的是,價值規律同樣也解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會週期性地陷入危機——生產過剩危機是源於資本主義產生追求利潤:工人階級只得到他們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永遠無法買回他們生產的所有商品。或者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生產力不斷超過市場的極限。
價格與價值
奧地利學派也意識到勞動價值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因此,他們明確地把火力集中在他們認定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軟肋上。
他們相信,如果能夠破壞這個基礎,其余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土崩瓦解,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也會隨之瓦解。
卡爾·門格爾的弟子歐根·馮·龐巴維克成為奧地利新古典主義者,堅持反對馬克思主義。作者雅內克·瓦瑟曼(Janek Wasserman)在奧地利學派的傳記《邊際革命者》(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一書中寫道:「他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在政治和經濟的威脅,並試圖用邊際效用理論來削弱它」[2]。
龐巴維克對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各種批評,其中大部分是對勞動和勞動力間差異的誤解(可能是故意的),特別重要的是他混淆了價值和價格的區別。
馬克思本人已經非常清楚地區分了這價值和價格。馬克思沒有否認市場力量,透過供求關系變化決定價格的作用。但馬克思解釋說,這就像是圍繞潛在信號的模糊噪音。
他解釋道,在看似隨機和混亂的價格背後,隱藏著一種秩序,一種合乎規律的、一種客觀的東西。換句話說,在這些波動和 「偶然」中,存在一種「必然性」,即價值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釋說:
「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3]
繼續馬克思與萬有引力定律的類比:我們從行星運動中呈現出來的只是現像。表像背後卻蘊藏著無形的、摸不著的又可以被認知的客觀規律。
這些規律不是脫離自然或社會而獨立存在的;它們沒有被編碼到夜空中,也沒有編織成人類意識和行為的結構。相反,它們產生於辯證的、運動的系統內部復雜的相互作用。
同樣,價值規律也不是永恆的、外在的,而是一種只有在商品生產和交換變得龐雜、普遍且占主導地位的歷史時期才會應驗的規律。這樣的生產會失去所有的個人或特定的特征,市場上的相互競爭的不再是商品,而是價格。
一般來說,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它們的價值決定的,也就是說,交換價值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SNLT)所決定的。這包括在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工具、機器等所體現和轉移的「死勞動」;還包括有工人創造了新價值的「活勞動」。
市場力量推動價格高於或低於價值。例如,當對某種商品的需求超過供應時,其價格將高於其價值。反之,當供大於求時,價格便會低於價值。
實際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各種「扭曲」——比如壟斷的存在——阻礙了供求關系的完美平衡。因此,價格將趨於波動。
事實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但壟斷等各種各樣 「扭曲」的存在,都阻止了供求達到平衡。因此,價格往往會波動。
但這些波動通常會在一個平均值附近發生。有的商品總是能換到更多的其他商品。除非你有一輛非常破爛的汽車,或者一支非常花哨的筆,否則一輛車的價格抵得上成百上千的筆。
馬克思解釋說,當供求關系被假定為處於「均衡」狀態時,正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為什麼有的商品要比其他商品更有價值。
另外,邊際效用理論只關心價格;停留在事物表面,而不關注潛在的運動規律。就像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筆下的憤世嫉俗者一樣,邊緣主義者們「知道所有物品的價格,卻不知道任何東西的價值」。
邊際主義和主觀主義
在反對LTV的同時,MUT的支持者有意識地與古典學派的傳統決裂,古典學派將其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建立在生產的基礎上。而現在的MUT依靠消費者來確定商品的價值。
「邊際主義者顛覆了古典經濟學」瓦瑟曼在《邊際革命者》一書中寫道,「他們沒有把重點放在經濟的生產方面,而是轉向了消費。真正有價值的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不是生產所需的勞動。」[4]
換句話說,MUT的支持者說價值是基於商品的「效用」,是一種純粹主觀的東西。也就是說價值是一件商品與其他商品相比,在「邊際」情況下對消費者的有用性。

在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所著的小冊子《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思想、代表人物和組織的歷史》中,門格爾說到 「價值是…個別商品或商品數量對我們來說的重要性,因為我們意識到得依賴它們來滿足自己的需要」。[5]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Institute)在網上免費提供這本小冊子,默認了這些想法對社會沒有任何「效用」。
瓦瑟曼和維塞爾一樣給邊際效用做出了簡明的定義:
「簡單地說,一個單位(商品)的價值是由該單位在一定經濟條件下所能使用的最低價值決定。」[6]
然而,馬克思也理解商品有效用、對社會有「使用價值」的重要性。如果一種商品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那麼它就不能被售出。結果就是這樣的商品沒有「交換價值」,更不會有價格,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這個回答同樣也駁斥了所謂的「泥餅悖論(mud pie paradox)」,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反對者試圖譏諷勞動價值理論的觀點,於是他們問道「要是我花了幾個小時做一個泥餅,那這應該是非常有價值的嗎?」
顯然,泥餅悖論是錯誤的。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如上所述,所有商品都必須具有使用價值(有用性)才能被交換,從而具有交換價值。
其次,即使泥餅對人有用,但決定其價值的不是生產中投入的個人或個別勞動時間,而是一定歷史和技術條件下制造這種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也就是說,我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並不是主觀的直接將自己的勞動成果與他人相比較。相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在市場上看到一個客觀的價格。
如前所述,我們並不像在《魯濱遜漂流記》中的荒島上那樣,以物物交換為基礎進行交換,而是通過貨幣和市場等媒介進行交換。
回到前面的例子,當你在亞馬遜或谷歌上搜索要購買的東西時,你不會遇到分散的小生產者,你可以與他們討價還價。相反,你(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選擇供應商,他們相互競爭以提供最便宜的價格;對於任何相對可復刻的商品而言,價格都將趨向於一定水平。
那麼,如何才能將這些眾多的商品相互比較呢?是什麼最終決定了他的交換價值或價格(價值的貨幣化表現形式)?
顯然,這樣的比較不能基於它們的效用,這是主觀的和定性的。每一類商品都有自己的物理性質和特點;獨特的特性,有特定的預期用途。此外,商品的有用性在不同的消費者之間會有很大差異。
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生產者的角度還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那些希望在網上銷售商品的人並不根據它們的「效用」來定價。
供應商也很少與客戶有可以確定商品主觀用途的個人聯系。
此外,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重點是商品對他們沒用處;他們生產只是為了交換從而賺取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個體需求。
因此,不能根據商品的「效用」來任意比較商品。就衡量價值而言,需要的是一種相對的、可量化的和客觀的共同特點。馬克思解釋說,所有商品最普遍共同特點是商品是勞動的產物,尤其是社會勞動,使得商品可以進行比較、交換。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最後,邊際主義者最終把自己搞得狼狽不堪。例如,他們聲稱,價值是由獨立個人的主觀偏好決定的。但反過來,又是什麼決定了這些主觀偏好呢?
顯然,我們對各種商品和服務價值的評估並不是天然固定在頭腦中的。相反,它們是經驗和社會規範的產物。我們對事物該花多少的預期,是建立在對商品價格的歷史認識的基礎上。
然而,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脫離了社會背景,把人置於孤立的情景中。他們把資本主義的運動簡化為抽像的、非歷史的買家和賣家的行為,沒有意識到整體遠大於部分之和。對他們來說,價值純粹是根據個人的主觀衝動來決定的。
但真正科學的經濟學方法必須建立在客觀規律之上,而不是分析主觀的衝動。它必須設法從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發生的數百萬次相互作用裡尋找規律,揭示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而不是簡化這些相互作用。事實上,基本法則支配著市場上眾多的互動。
像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一樣,奧地利學派也認為自己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規律。但對他們來說,這些規律被視為基於「人性」的「永恆真理」,而不是生產方式隨歷史演變的辯證產物,或者是社會在某個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規律是一定現像或制度內潛在的一般動力。資本主義的規律不是永恆的和絕對的。它們不存在於一個獨立的、理想的領域,從外部強加給社會。但是,像唯心的奧地利學派之流正是這樣認識經濟規律的。
「一個蘋果從樹上落下和天體的運動,都要共同遵照萬有引力定律」與門格爾同時代,畢業於維也納大學的埃米爾·薩克斯說道。「對於經濟活動」他繼續說道,「魯濱遜和一個擁有一億人口的帝國都要遵循同一條價值規律。」[7]
事實上,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甚至認為經濟規律是永恆的,可以先驗地得出,完全脫離任何社會背景或經驗證據。米塞斯將基於對「理性」經濟主體及其「有目的行為」的研究思路命名為人類行為學。
非歷史的、抽像和唯心主義的方法並不是奧地利學派發明的。而是奧地利學派從他們的自由主義前輩繼承而來的,這些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認為資本主義及其法則是永恆的,是天生 「人性」的產物。
正如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討論古典學派的局限性時所分析的那樣:
「李嘉圖還把勞動的資產階級形式看成是社會勞動的永恆的自然形式。」
「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馬克思說道,「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交換魚和野味。」
「在這裡他犯了時代錯誤」馬克思苦笑道,「他竟讓原始的漁夫和獵人在計算他們的勞動工具時去查看1817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8]
就像斯密和李嘉圖的「魯濱遜漂流記」和「原始漁夫」一樣,邊際主義者選擇的所有假設場景都完全脫離了資本主義的現實。
馮·龐巴維克和門格爾的作品充斥著對這種抽像例子的引用,例如:「一個人坐在一個水源旁邊,水源洶湧」、「沙漠中的旅行者」、「一個殖民者,他的小木屋孤獨地矗立在原始森林中」、「綠洲中的居民」、「一個孤島上近視的人」、「一個孤立的農民」和「海難的人」。
同時,邊際主義者也不斷用鑽石或藝術品等特殊商品,以「證明」MUT的正確性。
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部分並不致力於生產稀有物品,如鑽石戒指、珍珠項鏈或精美藝術品,而是致力於生產大量的日常商品,其價格往往趨向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平均值。
在奧地利學派看來,整個世界都圍繞著個人主觀意志。這種主觀唯心主義與當時倒退的哲學思潮有共同的特點,比如馬赫的實證主義和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
然而,基於這樣的基礎,統治階級還不可能真正挑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的「理論」顯然只是為資本主義詭辯,而不是在闡釋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經濟計算論戰
盡管奧地利學派處心積慮機關算盡,但社會主義運動仍在繼續發展。
這個進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短短幾年內,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卻在整個歐洲引發了一波革命浪潮,群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被憤怒和激進化取代,最明顯的是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領導的革命,以及近12個月後的德國。
統治階級對這些革命的發展感到恐懼。與此同時,自由放任主義的支持者也對國家計劃、壟斷、遠離私有制和競爭加劇感到擔憂。
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某些資產階級的階層也被計劃經濟思想所吸引。面對贏得戰爭的緊迫任務,各國政府並沒有轉向市場來生產軍備和其他必需品,而是將經濟集中到國家手中。
雅內克·瓦瑟曼在《邊際革命者》中敘述道,「在德國和奧地利,政府建立了戰爭計劃委員會以分配資源,被稱為 ‘戰爭社會主義’。」
傳記作者繼續說,「這是第一次,國有化和社會化成為可以施行的政策立場。」[9]
這引發了奧地利學派年輕一代的新一輪攻擊。從1920年左右開始,米塞斯等人領導了後來被稱為 「社會主義計算論戰」的運動。
用米塞斯話來說他旨在表明社會主義,不是「理論上正確,但實踐上錯誤」,而是「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總之,米塞斯斷言,由於經濟的復雜性,社會主義計劃是不可能的。他認為,所需的計算量對於任何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來說都太大了。
米塞斯聲稱,有這麼多東西需要生產和分配,只有貨幣價格信號提供的信息,通過市場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和勞動力。
此外,他說,任何國家的參與或監管都會導致價格被扭曲,阻礙市場的力量。因此,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讓完全自由、競爭激烈的市場發揮作用。
米塞斯在他的《社會主義》一書中斷言,「社會一旦放棄了產品的自由定價,理性生產就不可能了。」
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總結道:「每遠離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貨幣一步,就遠離理性經濟活動一步。」[10]
但蘇聯和大蕭條這兩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對這個極其抽像和唯心的論點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正如列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評論蘇聯在計劃經濟下取得的巨大經濟進步時所寫的那樣:
「工業的巨大成就,農業的大有希望的開端,舊工業城市的急劇發展和新工業城市的興建,工人人數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無可懷疑的成果,但舊世界的預言家們曾把這次革命當作是人類文明的墳墓。
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爭辯的。社會主義已經證明有權取得勝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
與此同時,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導致了1929年的華爾街崩盤,以及隨後的1930年代大蕭條: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的危機。對此,奧地利學派對此既沒有一個真正的解釋,也沒有解決方案。
事實上,奧地利經濟學家提出的治療方案,在許多當權派看來似乎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穩定金本位、平衡預算、自由貿易,所有這些都冒著加深通貨緊縮、加劇失業、延長危機的風險。
簡而言之,奧地利人建議政府後退一步,扯開安全網,勒緊腰帶,讓經濟「自我調節」。
「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獲」是他們的座右銘。毋庸置疑,這種極端的緊縮政策對尋求選舉的政客來說不是特別受歡迎。
於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試圖改變目標來應對這些事。
海耶克在1935-40年間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社會主義計劃並非不可能,而是在技術上很困難、更低的經濟效率、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可取。
然而,從本質上講,海耶克與米塞斯或者亞當·斯密的論點並無不同。換句話說,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麼通過市場的「看不見的手」,這將為社會帶來最好的經濟結果,從而為所有人帶來最好的經濟結果。

海耶克認為,沒有一個中央規劃機構能夠跟蹤不確定的、不斷變化的個人偏好和優先事項。只有自由市場,通過價格信息,才能處理這種動態和復雜的計算。
然而,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海耶克主要攻擊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對當時蘇聯自上而下的史達林主義扭曲官僚計劃。
反過來,海耶克並沒有證明他自己觀點的正確性,而是攻擊那些捍衛各種形式社會主義計劃的人。
這些人主要分為兩大陣營:要麼是史達林主義官僚主義的辯護者——比如英國共產黨人和劍橋大學經濟學家莫里斯·多布斯(Maurice Dobbs);要麼是像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和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這樣的改良主義者和學者。
由於官僚主義的窒息效應,前者對蘇聯發生的經濟災難基本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後者則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的支持者:一種烏托邦式的混合經濟,建立在共同所有權、中央計劃和資本主義市場混亂和永久的混合上。
盡管海耶克本人也不乏學術缺陷,但他卻毫不費力地將這些笨蛋們撕成碎片。這些人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來進行反駁,只能在同海耶克的論戰中掙扎。
托洛茨基談計劃
唯一能夠真正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辯護以及對官僚主義的危險做出適當解釋的,只有列夫·托洛茨基。他在《被背叛的革命》和一篇題為《蘇俄的經濟危機》的精彩文章中做到了這一點。
在這些文章中,托洛茨基概述了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就,以及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的癌症生長如何扼殺了這種潛力。
然而,重要的是,托洛茨基還討論了官僚主義的本質,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解釋了官僚主義是如何給十月革命的勝利蒙上陰影使之偏離軌道。
簡而言之,官僚機構的崛起並不像海耶克和奧地利學派理想主義所堅持的那樣,是社會主義計劃的必然產物,而是試圖在經濟落後和孤立的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的結果,正如在俄國所看到的那樣:
「官僚統治乃是建立在社會缺乏消費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鬥爭這個基礎之上。若是店鋪裡的貨物很充足,那麼購買者要什麼時候去,就可以什麼時候去。若是貨物很少,那麼購買者就不能不排隊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長,就必須派一個警察去維持秩序。這就是蘇維埃官僚權力之起點。它「知道」什麼人可以得到東西,而什麼人必須等待。」[1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耶克唯一一次接觸托洛茨基的論點,是在他方便的時候選擇性的從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引用,為諷刺他的對手而完全斷章取義。
例如,在《蘇俄的經濟危機》一書中,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完全正確的論斷,他說:
「構成經濟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並且沒有「在拉普拉斯之科學的幻想中,其所描畫的普遍的睿智存在的話,亦即將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過程同時記錄的,將其運動之動態測定的,將其相互關系之結果預見的睿智存在的話,則這個睿智…能夠作成一個先天的,正確而完滿的經濟計劃吧!」。
然而,海耶克沒有提到的後面的內容,托洛茨基繼續解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成功規劃經濟最重要的是,工人民主以及必要性的控制和管理。
托洛茨基解釋說:
「蘇聯經濟的效果,是只有於實行過程中,從事計劃之常時的調整,和基於實驗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體的改造,才能獲得其保障。」
「社會主義計劃化的技巧,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是一個既成品,隨著政權的獲得便被付與了。這技巧不能單獨的獲得,它屬於新經濟和新文化之一構成部分,只有隨著鬥爭的進展,一步一步的,依據數百萬大眾而才能獲得。」[12]
此外,托洛茨基繼續解釋說,這樣的工人國家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從稀缺過渡到豐饒, 必須利用市場價格信號提供的信息,以確定哪裡的短缺最大,哪裡最需要投資。
托洛茨基解釋說:
「直接參加經濟的國家和個人,集團和單獨的參加者,不僅有助於計劃委員會之統計的計算,而且有助於需要和供給之直接的影響,其必要和相對力是必須發表的。計劃經過檢討,並於其顯著的程度上,以市場為媒介而實現。市場自身的調節,依存於經過中介而顯現的趨勢。事務室的預定,必須經過商業的計算,才能證明其經濟的合同的性。過渡的經濟綱領,不從事盧布的統制而來思考是不可得的。不單是要統制盧布,便是盧布自身的安定也要預想一下的。商業的決算,若沒有確實的貨幣,則只能助長其混亂之增大。」[13]
托洛茨基後來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重申了同樣的觀點。「計劃經濟不能單靠知識資料。」他評論道:「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長時期以內仍然是必要的物質基礎和不可缺少的矯正者。」[14]
事實上,托洛茨基早就預見到了這些問題。早在1922年,他就強調,純粹的社會主義計劃方法「不能通過先驗的創造,也不能是閉門造車」[15]

他解釋說,在資本主義和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富足社會之間,將存在若干過渡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市場方法不能完全被拋棄。
政治和經濟
托洛茨基同意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是行不通的。他也接受價格信號的必要性,但只是作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一個暫時的指引,要隨著貨幣、市場、國家和階級的消亡而消亡;或者,用恩格斯的話說,「管理人的政府被管理事物和控制生產所取代」。
當然,海耶克和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在形式上的相似之處完全是膚淺的。實際上,這兩位理論家來自完全相反的階級觀點。海耶克從右翼批評蘇聯官僚主義的計劃;而托洛茨基則是從左翼批判它。
在這方面,自由主義者(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用托洛茨基來支持他們的反動思想是非常虛偽的,托洛茨基始終堅決的維護蘇聯和十月革命的勝利。
托洛茨基在評論俄羅斯墮落的工人國家時說:「盡管它繼承了糟粕、飢餓和蕭條,盡管官僚主義錯誤,令人憎惡,但全世界的工人必須竭盡全力捍衛這個國家所代表的未來的社會主義祖國。」[16]
與此同時,當海耶克和蘭格等人對唯心主義藍圖進行抽像爭論時,我們看到了托洛茨基是如何用辯證唯物主義地看待經濟計劃問題的。
他強調,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按照官僚集團所設想的計劃從上而下實施,而應該在工人階級掌權後,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物質條件中產生。
因此,托洛茨基強調,利用市場力量和價格信號指導社會主義計劃的前提條件是,革命消滅了資本主義,奪取了經濟的主杠杆,並把它們交到了工人國家手中。
換句話說,不是史達林式的官僚計劃經濟,也不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需要一個真正理性的社會主義計劃,包括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制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發展,共同所有制擴大,經濟對立減少,工人的民主系統將逐漸取代對貨幣價格信號的需要。
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不再由市場力量引導,而是自己決定什麼可以、什麼應該被生產;投資應優先考慮的領域;勞動和物質資源應該如何分配。
與此同時,負責任和可召回的代表將利用所有繼承自現代資本主義的最新最好的科學、技術、工藝、計劃、數據、物流和會計方法。
托洛茨基強調,重要的一點是,社會主義計劃的「問題」不是海耶克和米塞斯斷言的「經濟計算」。類似地,像蘭格這樣的知識分子關注這個細節是錯誤的,這不是制造更大更好的計算機的問題。我們不能計算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經濟不是一組待解的聯立方程,也不是一個可以從上編程的計算機模型。它也不是假想荒島上抽像、孤立、原子化個體的集合。
相反,經濟是由血肉組成的有生命的、會呼吸的系統。是普通人試圖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是努力維持生計。
首先,它是對立階級和物質利益之間的鬥爭: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資本家尋求利潤最大化,而工人尋求保護自己的生活和生計。
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強調的那樣,真正的問題不是「經濟計算」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不是一個計算問題,而是一個階級問題。一個權力問題,由哪個階級擁有並經營生產資料?根據什麼法律?為了需求或利潤?
正如托洛茨基雄辯地總結:
「作為計劃最基礎的因素,即活生生的社會利益之間的鬥爭,也帶我們走近了政治的領域(它也不過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蘇維埃社會內各個群體的工具是,也應該是:蘇維埃,工會,合作社和最首要的執政黨。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數年來的矛盾和不均衡,並非要完全的克服(這是夢想!),而是將這種情勢緩和下來,根據這個,則新而真實的革命,將社會主義計劃化的戰線擴大,直到改造其綱領,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才能取得保障吧!」[17]
資本主義計劃
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看到了大量的計劃,但這不是由政府或國家制定的,而是由主導全球經濟的大型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內部制定的。
從馬克思時代起,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大規模工業和世界市場,大型跨國公司和公司內部在組織生產。
今天,大多數經濟活動不是在市場上進行的,而是在這些公司的老闆的指導下進行的。他們不會讓「看不見的手」在企業內部做出與生產相關的決策。相反,從農場和工廠,到商店和超市,他們計劃著一切。
正如社會主義作家雷·菲利普斯(Leigh Phillips)和麥克·羅斯沃爾斯基(Michal Rozworski)在他們有趣的「社會主義計算辯論史」中解釋,他們幽默地將其命名為「沃爾瑪人民共和國」:
「沃爾瑪也許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證據,雖然計劃在米塞斯的理論中似乎不起作用,但在實踐中肯定起作用。不僅如此…」
「如果沃爾瑪是一個國家,讓我們稱它為沃爾瑪人民共和國,它的經濟規模大致相當於瑞典或瑞士……」
「然而,雖然該公司在市場上運作,但在內部,就像在任何其他公司一樣,一切都在計劃之中。沒有內部市場。不同的部門,商店,卡車和供應商在市場上不會相互競爭;一切都是協調的。」
「沃爾瑪不僅是一個計劃經濟,而且是一個與冷戰期間的蘇聯規模相當的計劃經濟。(1970年,蘇聯的GDP按今天的貨幣計算約為8000億美元,當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沃爾瑪2017年的營收為4850億美元)。」[18]
在重復海耶克式的關於資本主義保護「自由」和「自由選擇」的胡言亂語時,老闆們實際上是工作場所內最大的獨裁者,讓他們的員工別無選擇,沒有自由,沒有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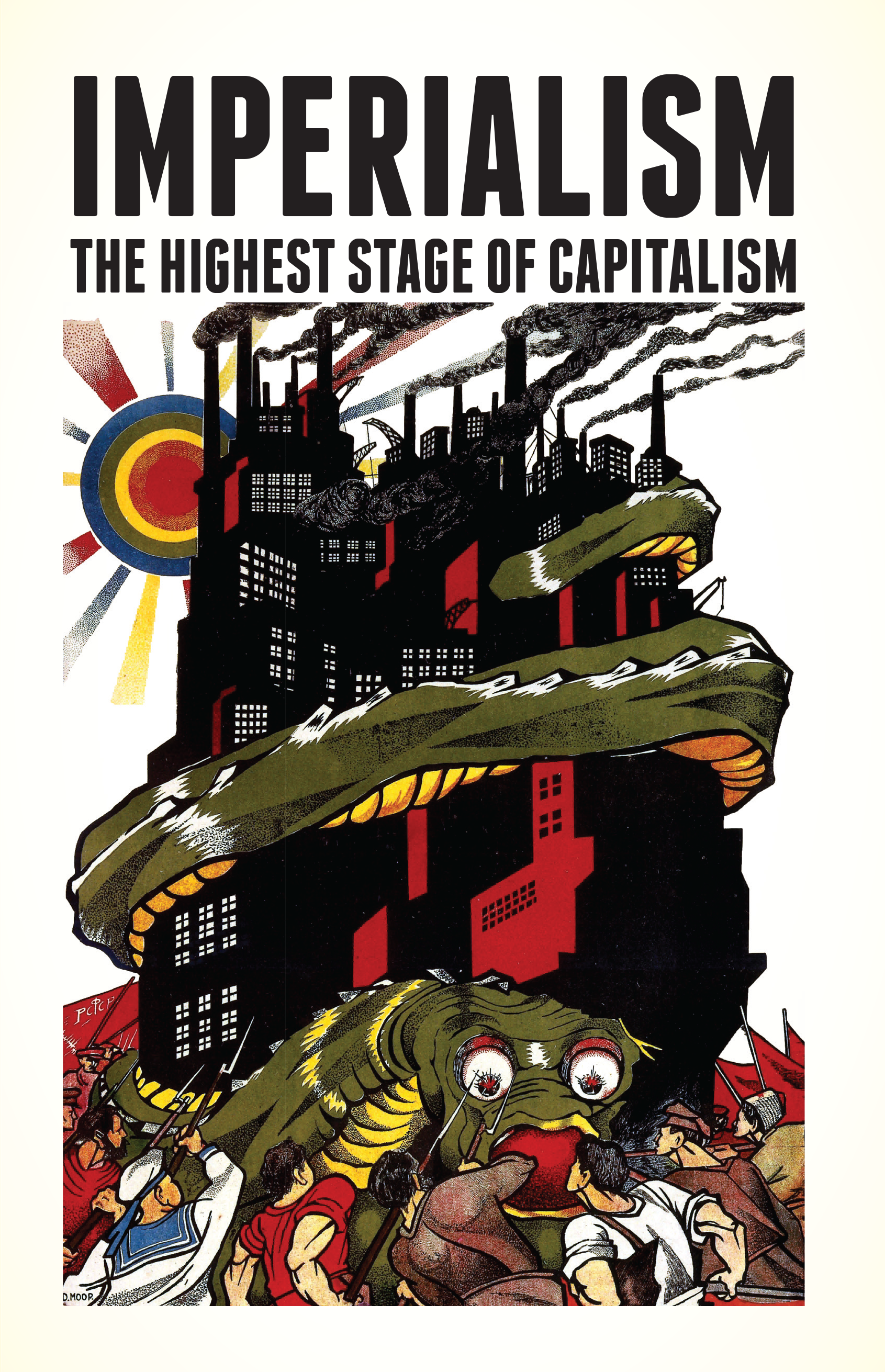
但是,盡管企業內部的計劃水平令人難以置信,但企業間仍然存在無政府狀態。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每個公司都盲目地為未知市場而生產;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是根據社會需求制定共同計劃。
其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資本主義的混亂,追逐利潤的投資者的從眾心理導致了,世界在短缺和過剩之間瘋狂波動。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鮮明地表現出來。」[19]
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我們看到了計劃的巨大潛力。例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最近的一期封面突出了「實時」經濟的出現,大型科技公司每小時、每分鐘收集了海量的數據,了解我們購買了什麼,我們去了哪裡,我們在尋找什麼。[20]
但在私人壟斷企業如谷歌、臉書、亞馬遜等的所有權下,所有這些信息都被用來控制我們,而不是給予我們控制權。就像我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看到的所有技術、創新和計劃一樣,它們被用來實現利潤最大化,而不是滿足我們的需求。
因此,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體制下計劃經濟的局限性。歸根結底,你無法真正計劃你不能控制的事;你不能控制你不擁有的東西。
競爭與壟斷
海耶克和米塞斯不僅強烈反對社會主義,而且反對一切形式的計劃。事實上,海耶克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想法合法化,政府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正在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播鋪平道路;將公眾引向所謂的威權主義和被奴役的「奴役之路」。
但是,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所解釋的那樣,計劃是由於資本主義規律而產生的一個事實:壟斷、集中和生產集中的趨勢。
然而,對於像海耶克這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壟斷並不被視為一種客觀趨勢,它源於私有制和以營利為目的的生產,而是主觀決定的產物;這是由於政治錯誤造成的反常現像。
但是,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闡述的那樣,計劃是由於資本主義趨向於壟斷、集中和生產集中化規律而產生的。
然而,對於海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壟斷並不被視為一種客觀趨勢,它不是源於私有制和逐利生產,而是主觀決定的產物,政治失誤造成的失常。
海耶克在《通往農奴之路》一書中聲稱:
「壟斷和計劃的趨勢不是我們無法控制的 ‘客觀事實’的結果,而是半個世紀以來所培育和傳播的觀點的產物,直到它們開始主導我們的政策。」[21]
這種論斷再一次顯露了奧地利學派的唯心主義思想。同樣,海耶克和他的前輩們並沒有為資本主義體制提供科學的解釋,而是躲在神秘主義和蒙昧主義的表面後面,只是為了為現狀辯護。
不管海耶克怎麼否認,壟斷的過程是一個客觀事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非常清楚地解釋了這一動態過程。
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企業為了競爭被迫投資新技術,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將價格降至行業平均水平以下,並將競爭對手逐出市場。從本質上說,這就是價值規律發揮作用。
結果是,我們看到整個社會的勞動分工水平令人難以置信,同時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幾個巨大的壟斷企業及其資本主義所有者手中。
最強、最有競爭力的公司會吞並最弱的公司。反過來又使它們進一步擴張,實現「規模經濟」,建立更大的准入壁壘。桌游《大富翁》恰如其分地展示了這一過程。
其結果是,我們看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分工水平,也看到了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壟斷者及其資本所有者手中。
恩格斯解釋說:
「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22]
資本主義的矛盾
重要的是,正是這些同樣的資本主義競爭、私有制和為利潤而生產的法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個體系週期性地陷入危機。
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行不通。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地選擇了與斯密和李嘉圖相同的假設。他想從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出發,運用他們自己的觀點,來展示內資本主義的矛盾。
其中包括這樣的假設,即商品都按其價值出售(即價格=價值),沒有壟斷或對資本流動的其他限制。同樣,至少在第一卷中,馬克思假設貨幣是金屬的,沒有任何形式的信用。
馬克思這樣做是為了以最純粹的形式審視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體制的運動,從而解釋我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中看到的各種經濟現像背後的一般原因。
事實上,這些假設與海耶克和自由意志主義者所呼吁的理想資本主義完全相同:一個自由市場,充分的競爭,沒有價格扭曲,沒有泡沫。
然而,即使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也表明,由於利潤制度的性質,資本主義本質上會導致生產過剩的危機。
總而言之,這種危機是資本主義固有的,因為利潤的起源:工人階級的無償勞動。
如前所述,工人創造的價值遠高於他們以工資形式得到的回報。因此,作為一個整體,工人階級永遠買不起他們生產的所有商品。但是,如果商品賣不出去,那些只為了賺錢而生產的資本家就會關門大吉。需求下降和投資下降的惡性循環隨之而來,經濟陷入停滯。
資本家可以利用各種手段來防止或延緩一場危機。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准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因此,矛盾的最終結果不是「效率」,而是以大規模失業的形式出現的巨大浪費;閑置的工廠、普遍貧困;這是破壞生產力,而不是發展。
「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飢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23]
因此,關於「經濟計算」和如何最有效地分配稀缺資源的辯論具有誤導性。
人類面臨的任務不是計算如何分配稀缺的資源,而是將巨大的生產力和過剩的社會資源轉化為共同所有制和工人控制;並進一步發展這些力量,使它們能夠理性地、民主地加以利用,以滿足我們的需要,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強調: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罪惡,並不在於有產階級的奢侈(盡管奢侈本身是多麼可惡),而是在於資產階級為了保障自己奢侈的權利而維持它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這樣就使經濟制度陷於無政府和衰朽狀態。」[24]
正如奧地利學派所宣稱的那樣,這一切都不是由於糟糕的政策決定,而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產物。
即使像斯密、海耶克和其他自由主義者或自由意志主義者所建議的那樣,每個人的那樣都在 「理性地」行事,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極不理性的。
換句話說,即使資本主義(或確切地說是什麼時候)正在發揮作用,這也恰恰是它根本不起作用的時候。
海耶克vs凱恩斯
這是任何一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都無法真正解釋的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會陷入危機。
例如,在海耶克和米塞斯看來,華爾街崩盤和大蕭條都是不負責任的政府和中央銀行家們在信貸投放上過於粗心,導致資產泡沫形成的過錯。
與此類似,現代自由主義者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進行了同樣的分析。他們告訴我們,那些掌舵人不應該用人為的低利率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助長次貸醜聞,而應該後退一步,讓市場發揮魔力。
但這樣的行動(或不行動)不會導致經濟「均衡」和平衡。相反,如果政治家和決策者沒有在1920年代,以及19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再次注入信貸,那麼隨後的衰退就會提前到來,生產過剩的危機會更早地顯現出來。
由於這些原因,統治階級從來沒有被海耶克說服。

甚至可以說海耶克自己都不信服。由於未能在「社會主義計算辯論」中給予其對手致命一擊,他放棄了他的觀點。
他轉向為自由意志主義做政治辯護,正如《通往奴役之路》中所呈現的那樣:從道德上抱怨計劃主義經濟不可避免地導致極權主義,並說只有競爭性市場才能提供真正的「自由」、「選擇」和「個性」。
然而,在晚年他和他的虛偽的追隨者,公開支持皮諾切特獨裁政權的鐵拳,以粉碎阿連德在智利的社會主義政府,強行引入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
面對大蕭條,1930年代的統治階級(至少在美國)轉向了凱恩斯主義的所謂「實用主義」, 而不是海耶克的烏托邦自由主義,其中最著名的是羅斯福政府刺激重大公共工程項目的新政。
這本身就是默認了計劃的必要性,市場已經失敗了。為了將資本主義從泥潭中拉出來,需要國家的干預。即使在那時,這些凱恩斯主義政策也沒有奏效,危機持續了十年,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統治階級無法承受奧地利學派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也就是,通過緊縮、大規模失業以及對工資、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攻擊,讓工人階級立即為危機買單。
海耶克及其同僚一再保證,這種巨大的痛苦和苦難是暫時的,而且「從長遠來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這沒有帶來什麼安慰。正如凱恩斯曾經說過的那樣:
「從長遠來看,這是對時事的誤導。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如果在暴風雨季節,經濟學家只能告訴我們,當風暴很久過去時,海洋又是平靜的。那經濟學家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太容易,太無用了。」[25]
統治階級對證明自由市場的合理性不感興趣,因為自由市場顯然沒有發揮作用。相反,他們想要拯救資本主義,利用國家來拯救資本主義。
這似乎就是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所提供的:一個基於管理和修補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而不需要冒著社會崩潰和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向工人階級發起進攻。
同樣,如今自由市場最積極的捍衛者也在疫情期間卑躬屈膝。很少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反對為應對冠狀病毒危機而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國家干預,與17萬億美元的直接財政支持和刺激,以及另外10萬億美元注入經濟的中央銀行——所有支撐系統和防止全面崩潰。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資產階級為那些被認為「大到不能倒」的大型金融壟斷企業提供救助。但當談到為此買單時,這些老闆和銀行家卻不見蹤影。相反,在過去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裡,是工人在為裁員買單。
由於戰後的繁榮,凱恩斯主義在政治家和學術界的流行了幾十年,直到這些政府刺激、國家監管、需求側管理和赤字融資等政策在上世紀70年代崩潰,為轉向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鋪平了道路。
但我們必須清楚:盡管崇拜「好的」凱恩斯、懲罰「壞的」海耶克的改良派制造了混亂,但凱恩斯主義和海耶克主義是同一枚自由資本主義硬幣的兩面。
事實上,雖然凱恩斯和海耶克因20世紀30年代的學術爭論而聞名,但他們的共同點比他們願意承認的要多得多。
兩者都是堅決地反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都是站在資本主義和統治階級一邊的。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古典經濟學家和啟蒙運動的真正繼承者。兩人都出身於特權階層,都對維多利亞時代和鍍金時代的回歸充滿了懷舊之情。
兩者都充滿了烏托邦主義和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特有的唯心主義。兩者對經濟都有機械和抽像的觀點,而不是唯物主義和辯證的視角。最重要的是,兩個人以及他們的思想,從根本上接受並捍衛了資本主義體制。
他們的分歧更多地在於經濟制度的形式,資本主義國家干預與資本主義市場自由的程度,而不是階級內容。
凱恩斯顯然支持市場,但只是擔心自由放任原則和食利資本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占據了上風。與此同時,海耶克雖然反對計劃取代競爭,但原則上並不反對國家干預和政府福利計劃。
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沒有為工人階級提供前進的道路,凱恩斯主義管理資本主義的嘗試是行不通的。與此同時,把我們的生活和未來交到市場手中,是一條通往痛苦和災難的道路。
自由和必然性
今天,大多數自由意志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在經濟上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嘗試。相反,自由意志主義大多被簡化為一系列關於「自由」和「選擇」的道德主義、個人主義偏見,正如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概述的那樣。
與此同時,海耶克的思想和觀點以及大多數大學經濟學的主要內容,被各種資金雄厚的智庫和自由市場機構所倡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機構是由他們「憎惡的」龐大壟斷企業(如洛克菲勒家族)資助的。
作為對這些大型商業慈善事業的回報,奧地利為右翼政治家(如柴契爾和雷根)提供了一塊方便的理論上的遮羞布作為藏身之處,因為他們粉碎了工會,剝奪工人的權利和福利,努力提高資本家的利潤。
綜上所述,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和「理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對「自由」的訴求也是如此。
實際上,現在強加給我一個出於歷史和經濟需要而無意識地產生的體系;在一個經濟及其法律不為我們服務的體系;在一個所有重要決定都不是由普通人民主做出,而是由資本獨裁政權做出,一個由老闆、銀行家和億萬富翁組成的專制和不負責任英精的體系中。在一個我們無法控制的體系中,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對海耶克來說,自由意味著沒有對個人的政治政治「脅迫」和「武力」的缺席,拒絕承認資本主義法律強加給工人階級的非常真實的經濟脅迫和力量。換句話說,對他來說,自由就是資產階級不受任何限制賺錢的自由。
正如恩格斯在與杜林的精彩論戰中,借鑒了黑格爾的辯證哲學指出的那樣,真正的自由不是通過想像自己擺脫社會、經濟和自然中的規律而獲得的,而這些規律在個人、資本家和工人的背後盲目地運作。
相反,真正的解脫恰恰來自於理解規律,並能夠運用它們來為我們帶來好處。簡而言之,自由「是對必然性的洞察」。
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
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
「因此,自由包括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的控制,這種控制建立在對自然必然性的認識之上;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26]
例如,人們可以想像自己是一只鳥,可以自由地飛走。但這並不意味著如果你從三樓的窗戶跳下來,你就能避免摔死。
然而,通過了解重力定律,運動定律,牛頓力學和空氣動力學定律,我們可以創造出可以讓我們飛行的飛機或無人機。
同樣,雖然圓柱體中每個氣體分子的運動似乎是隨機和不可預測的,但由於科學研究的歷史,我們現在知道有熱力學定律控制著整個系統的動力學,溫度,壓力,體積等之間具有非常明確的關系。
通過了解這些定律,我們可以將大量氣體中所含的熱量轉化為蒸汽,並使用它來轉動可以發電的渦輪機;也就是說,創造工業革命背後的力量,改變了社會和自然。
經濟學也是如此。然而,自由意志主義者對科學地理解資本主義體制不感興趣。他們的目標不是解釋經濟的運作,而是在矇昧工人,並為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提供理論上的辯護。
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真正了解世界,以便改變世界;有意識地認識和理解資本主義的規律,正如黑格爾所說,必然性規律「只有在不被理解的情況下才是盲目的」。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革命來推翻它們,並用一套基於社會主義計劃和工人民主的新法則取而代之。
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任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實基礎上組織工人和青年;在爭取革命的鬥爭中,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武器武裝自己。
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人類才能從資本主義混亂和危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從必然王國通往自由王國」。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注釋
[1] 馬克思致卡爾·克林格斯,1864年10月4日,《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1/219.htm
[2] 雅內克·瓦瑟曼,《邊際革命者》(耶魯大學:耶魯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1頁。
[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index.htm
[4] 雅內克·瓦瑟曼,《邊際革命者》,第28頁。
[5] Eugen-Maria Schulak & Herber tUnterköfler,《奧地利經濟學派:其思想、大使和制度的歷史》(維也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2011年),第16頁。
[6] 雅內克·瓦瑟曼,《邊際革命者》,第41頁。
[7] Eugen-Maria Schulak & Herber tUnterköfler,《奧地利經濟學派:其思想、大使和制度的歷史》,第19頁。
[8]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冊,第1篇,第1章,《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3/index.htm
[9] 雅內克·瓦瑟曼,《邊際革命者》,第103頁。
[10]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分析》(印第安納波利斯:自由基金,1981年),第5章,Econlib。
[11]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5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5.htm
[12] 托洛茨基,「蘇俄經濟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211.htm,譯者注:本文主要沿用以上鏈接的譯文,但譯者發現部分翻譯具有瑕疵,也加以修改
[13] 同上
[1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2.htm
[15] 托洛茨基,《共產國際的前五年》,第1卷和第2卷(倫敦:WellredBooks,2020年),第611頁。
[16] 托洛茨基,「蘇俄經濟危機」
[17] 同上
[18] 雷·菲利普斯和麥克·羅斯沃爾斯基,《沃爾瑪人民共和國》,(倫敦:反面,2019年),第30-31頁。
[19]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3編,《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5.htm,原文的重點
[20] 「即時經濟學:實時革命」,《經濟學人》,2021年10月23日。
[21]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2001年),第45-46頁。
[22]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3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80/03.htm,原文的重點
[23]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2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1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1.htm
[25]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關於貨幣改革的小冊子》.
[26]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1編,《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



